有时经过临潼老城,总还是觉得有点亲切。什么空疗、陆疗、铁疗、工疗,我也叫的上来的。当然后大多改制换名了。就在一片疗养院的后面,山坡上一个不知名的村子里,我曾住过半个月。
大二那年暑假,在家没事儿,寻思找个地方打工去。一来挣点钱,二来打发无聊的暑期。你知道,这大学生,上学的时候,一大群年轻人,进进出出,啸聚山林,顾盼自雄。一放假,作鸟兽散,找个人玩都没有,很无聊的。再说要串联一下,或者相约出去逛逛,不更得花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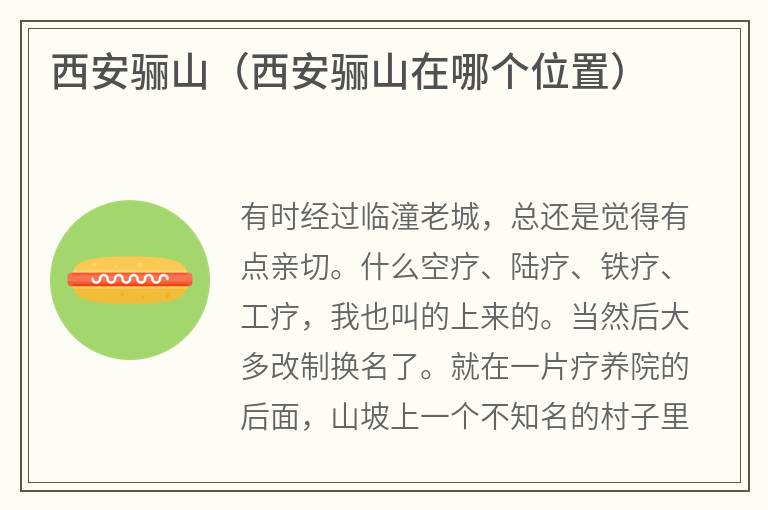
西安骊山(西安骊山在哪个位置)
建筑工地上,活儿倒不少,但是家里人觉得不太安全。后来老爸想到临潼有个朋友,也许能帮上忙。这位婶子在兵马俑附近做生意,主要给老外卖旅游商品,地图、折扇、明信片、画册、各种钥匙挂扣等,销量最好的就是那种泥娃娃——微缩版的秦俑,便宜,十块钱买十几个,用一个小网兜装着。暑期也算旺季,她想找个大学生来帮忙,好赖懂点外语。我一斗胆,就去了。
我在骊苑春酒店对面的村子,先租了一间房。那儿全是民房,很便宜,50块一个月。就是啥也没有,进去一看,光床板下面四摞砖,唯一的电器就是房顶中间,孤零零悬着的爱迪生灯泡。在我的极力要求下,上了一副新蚊帐。厕所、水房都有公用的。我到老街上去采购了几样东西,就准备开张了。一张草席、暖水瓶、热得快、蚊香,牙具、毛巾、几本小说月报,所有东西,我用一个粉色塑料盆儿装回来了。反正是夏天,也不要啥铺盖,冷了,带的有几身衣服可以盖下。年轻就是这么好活!
去了才知道,酒店还是很漂亮的。门口一溜罗马柱,大厅花岗岩铺地,擦得锃明瓦亮,冷气很足。远处的旗杆上挂着万国旗,下面是一溜大轿子车,沃尔沃、考斯特。一看环境不错,我就放心了。
呆了一天,我大概明白了这个生意。兵马俑是来西安的外籍游客必到的打卡地,但是一个县城的条件又留不住客人过夜。所以干脆留客人吃顿中饭。饭不能白吃,吃完要留你走走逛逛,最好再带点啥。所以二楼用餐,一楼店铺,出入都是流量。我要干的这个行当,行话叫“刀子”。刀子不属于哪一家店铺,整个大厅,几十家店铺的生意你都能做,你带了老外,跟他聊,帮他介绍,下了货就有提成。当然,实际上一个新人是不可能有啥大单子的,首先你得对这个场子的东西非常了解,那里边有成万块的玉雕,也有盗墓得到的明清古董衣,我真见过一对法国夫妇买了好几件,那花色非常繁复,但是笼着一层沉静的暗光。后来我才知道欧洲人玩VINTAGE,但是我至今不解,他们真的知道这些东西的来路么?不过据春田哥说,买这东西的人都是很懂行的。
都是刀子,却各有各的道。有个外院出来的大拿,很自以为是,听说是这边最厉害的刀子。一见我,便走过来,有点挑衅的说“听说你是大堡子来滴?”春田哥比较亲和,老远看见一个高个子老美走过来,他就走上去拉着别人比个子,他有意伸出手在自己头顶等了一下,又踮起脚尖,在老外头顶比了比,然后问“twometershigh?”表情和动作都很夸张,不过那个中年人像个大男孩一样笑着。我还见过一个讲日语的刀子,是个小姑娘,说话特小声,人畜无害的样子,只是把好多苏绣还是丝巾往身上披,笑得很甜美。那个日本男人也是很腼腆的笑着,似乎难为情,不断示意包起来。结完账走后,大家都咋舌,不到十分钟,四五千的货就下了。呆了几天,我有点明白“刀子”这个词的含义了——就是要“残豁”!可是,我还没开张。
春田哥是蓝田人,在新疆克拉玛依那边教过几年英语。觉得在外地教书也赚不了几个钱,家里也照应不上,就辞职来了临潼。虽然吃的是“洋饭”,但农民的朴实没有丢,再说,我也师范类,将来八成要教书,我们可聊的似乎就多些。他最爱推的是玉石的小挂件,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小柜台的玉石是他的货。也许是蓝田人吧,他很懂玉。蓝田玉、和田玉、缅甸翡翠,什么颜色,什么纹理,看水、看色,他讲起来头头是道。“咱这不是卖好玉的地方,上了千肯定卖不掉。”“就是造型漂亮,三五百块,人家就当玩了。如果有欧美的年轻情侣,那最好了。”“那边人玩饰品,看的是在哪买的,和谁一起旅行的买的,并不看重啥真金白银的材质,好看就行,这就看你会不会聊了!”“白色又不是很白,有点半透明的是缅玉,细看里面有白色的棉絮,这种东西不值钱,一般做成个玉扣买个百十块钱。”“如果是和田玉,纯白的,那可就值点钱了。”九十年代末都上千了吧。若干年后,在云南瑞丽逛玉石市场的时候,同去支教的老师都说我蛮懂行,他们不知道,这都是春田老师给我开的蒙。
在大家的鼓励下,我最后也算开了张。一个台湾大姐,在我这买了几把折扇。她说她想要送给谁,让我帮她选内容,扇子上印着不同的诗文的,这个刚好问到咱专业上,聊了一会儿,她买了三把扇子。我第一次认识到,人要是没有专业,想要赚点钱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太容易被替代了。干了十来天吧,我卖了十几套明信片,几袋子小俑,和七八把扇子,反正房租肯定够了,但是加上伙食,还真不好说。
惯例,当天谁下了大单,晚上就要请客吃饭。最受欢迎的就是麻辣鱼,有时去的人蛮多,其实吃不了两筷子,还得要盘炒米,不过年轻人在一块,很开心。吃完饭,晚上还会到街心广场去跳舞。
有天晚上突然有朋友建议上山去玩,说有个单子会。开始我不太明白,“啥,单子会?晚上山上还有人?”“漫山遍野都是人,能找个地方下脚就不错了。”去了我才明白,就是骊山老母店的庙会,带着凉席或单子上山,开心了就睡到山上。我模糊的感觉到,这种风习可能和远古野合淫奔的传统有关,老母殿本身就是以婚育送子灵验而驰名。单子会么,滚床单之意吧。先前有朋友说是因为临潼有个床单厂,所以成就了这么个“单子会”,我颇不以为然,太没有想象力了。床单厂早就倒闭了,按说单子会也该终结了,但这些年依然如火如荼,时节一到,遂复旧观。
我想起了陶庵《虎丘中秋夜》里的句子。“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鹅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去了你就知道,可能没有人江南士子那么雅,但是论规模,可以说是毫不逊色。
虽然并未带单子,我们还是在山上转了好半天。庙门前人太多了,松林里也拉了灯光照明。好多的男人赤膊上阵,光头大肚子,吆五喝六。最后我们走到骊山面向县城山坡上。一条长长的步道通向山下,哥几个就坐在台阶上。这情形如同若干年后我在太平山顶眺望维港,山下灯火辉煌,高楼上星星点点,每扇窗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不知为何我们唱起了歌。开始是山顶有人嚎叫,后来大家都唱,唱累了变成大伙点歌让我唱,真的唱了一晚上,唱的啥,一句也记不清。只记得更远处的公路上,车子在缓慢移动,车前伸展着长长的光柱。
从山上下来,没几天我就离开了。也许觉得,这活儿并不适合自己。同游的朋友,后来也再未见过,但那天晚上,大家心无芥蒂,胸无城府,倾盖如故。好几位我已经叫不上名字。其中一位小裁缝,是我同租住一个小院的房客,南方男孩,腼腆又狡黠。一位姑娘,地图摊位上的售货员,皮肤略黑,但是眼睛很有神采,待人亲和,对我很照顾。还有她的闺蜜一位。当然还有刘春田大哥。几位朋友,遥祝安好。谨以此文记载一次说走就走的打工。
本文经冷林先生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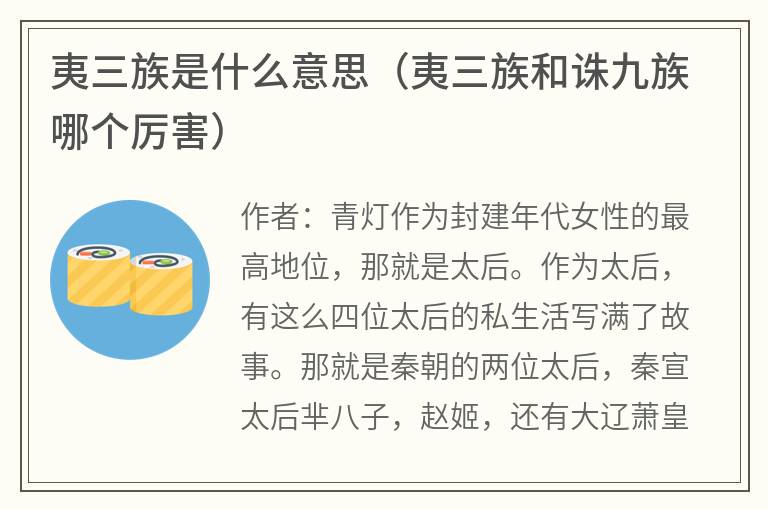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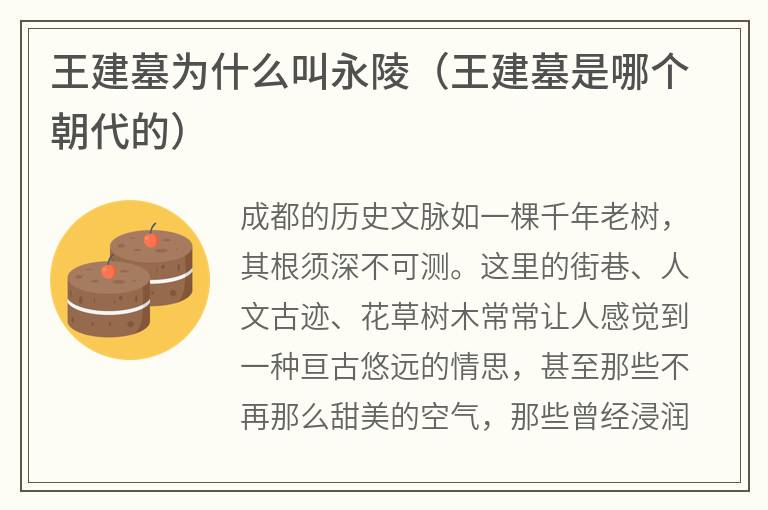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