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鸽子屈指算来也有20个小年头了,悠悠二十载,尽管无情的岁月把当年执着少年满头乌丝染成了白发;但我内心却总有一个搁不下的情结,那就是渴望得到一羽能托起整棚的种鸽。这个奢望恐怕是天下养鸽人共有的通病吧!期间,有不少上等的极品曾经与我擦肩而过,并非没有把握的机会,只是碍于面子或为家庭考虑的原因才不得不放弃。
我的养鸽经历是受本村一个出了五服的堂哥---斌子引起的。在70年代的农村,养鸽子是被看做“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玩物丧志”的行当。就凭这三个头衔,英俊、潇洒的棒小伙养鸽子找对象都难。原因很简单,谁家的父母愿意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基于这个习俗,所以六、七十年代在我们这地方农村,年轻人养鸽子的很少,再有就是当时中国还很落后,农民连饥饱问题都没解决,哪有闲余的粮食养鸽子。我养鸽子是因为父母的宠爱才误入歧途的。我的家庭中姊妹多,我是这个家庭中的唯一男丁。父母非常溺爱,有点好吃的、好喝的都是先让着我。尽管养鸽子不是什么好事,但出于对于我的喜爱,父母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事一样,所以我养鸽子根本没受到任何阻拦就顺理成章的开始了。
斌子家的条件比我家强多了。他爸在我们公社(70年代各地乡镇都叫某某人民公社)卫生所是个外科医生,端的是铁饭碗,斌子的零花钱自然就少不了。加之斌子家就他哥一个,他爸又常年不在家。斌子在家就是一个“山大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养鸽子自然不在话下。记得当时斌子鸽棚里佩戴不同地区环号的鸽子不下百羽。最为出众的是一羽红绛雄,此鸽戴的是重庆足环(70年代信鸽足环是汉字写的),绛红色的翅膀上点缀着墨黑色雨点,黄眼,短嘴,大鼻泡,红绛虽然在死棚里关着,但它丝毫不减过去驰骋疆场时的勇猛。喜欢占高处的巢穴,有时还隔三差五的偷袭同族的家园。凶悍霸气,在众鸽群中给人“鹤立鸡群”的感受。如果把它捉在手里,你就好像托着块海绵,一点感觉都没有。斌子和我都知道这是个好东西。他自然更是爱不释手。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老弟!你把那只红绛拿走出窝小崽吧!”我听了一愣,以为是斌子在逗我,当我看到他说话的表情是真的是,我一时又不知怎么回答才好,违背心思的说了句:“算了吧!我家地方小,又经常有黄鼠狼出没,别糟践了这么好的鸽子!”斌子听后也就不再提红绛的事了。每每回想起这件事,我都觉得自己当时的回绝是对的,其一:因为“君子不夺他人之爱物!”其二:如果自己真要是拿走了红绛,万一有个闪失,后果又该如何?君不见好友因借鸽子反目为仇的还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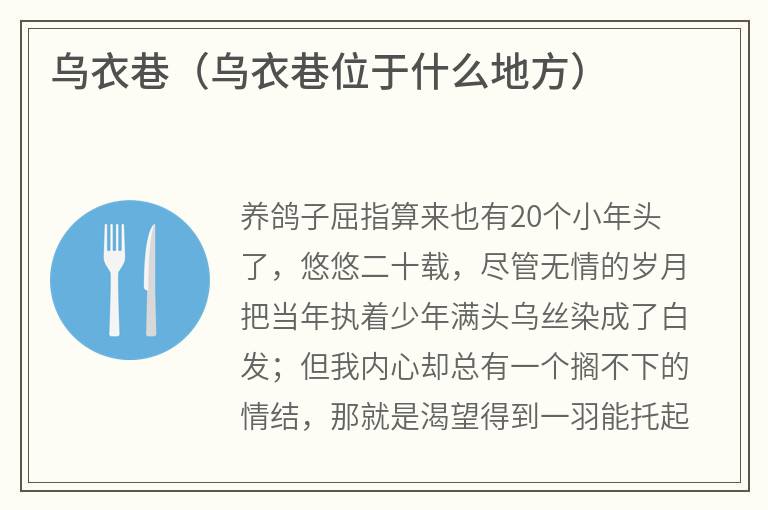
乌衣巷(乌衣巷位于什么地方)
80年代初期,斌子的腿闹骨病,他约我同他一起去北京积水潭医院看病。我知道斌子看病是借口,到北京买鸽子引种才是他真目的。我瞒着妻子偷偷把家里仅有的3000元钱掖在身上。到北京积水潭医院看病后,我俩就到积水潭医院北边一个斜街鸽市。常言道:“不到天边,不知天外有天;不到山外,不知山外有山。”北京不愧为天子脚下,卧虎藏龙。仅仅一个五、六十米的斜街鸽市,各种铭鸽应有尽有,造型奇异的鸽哨、形态多姿的观赏鸽让你目不暇接。在斜街鸽市,我第一次见到了向往已久的詹森。那是只纯正的詹森原环,不只是从它佩戴的足环上晓得,而是从它的外貌就可判断出这是只上品。鸡黄眼贼亮,不时流露出一股煞气,粗更长颈,鹰鼻,灰色的羽毛泛着黑色,站在笼子里纹丝不动,好像虎踞龙盘一般。我和斌子在詹森鸽面前顿足了好久,还是斌子挨不住性子,问鸽主:“这鸽子多少钱?”鸽主摇晃着芭蕉扇,用左手比划了个叉,说:“八千块!”“八千!”我一听差点没叫出来,要知道当时在农村,八千元能买一套崭新的12马力的拖拉机。我知道斌子带的钱多加上我带的3000元,买这只鸽子不成问题,但转念一想,自己偷拿的这3000元,是家里平时油盐柴米用的,如果买了鸽子,以后吃饭花什么!我拉了拉斌子的衣角说:“走,到前面看看,兴许还有更好的!”斌子情不自愿的离开了那只詹森鸽。打那以后,各种各样的詹森鸽我见了不少,但像我在斜街见得那只却再也没有看见过!
如今,自家鸽棚里的鸽子也不下四、五十羽,过去只能在鸽市过过眼瘾的鸽子,现在我的棚里也有了。每每想起过去的经历,我便会吟起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那首《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只有在有钱人家看到的铭鸽,如今寻常百姓家也有了!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