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标配是什么?
是琴棋书画,还是诗酒花茶?
或许都是,还有一条不可或缺,那就是藏书。
一个文人,即使身居陋室,也要有藏书,有雅致的书斋,家资丰饶者,更有几处书斋,甚至藏书楼。
他们自得于书斋。宋代文人雅士最令人向往的“诗情画意”的生活——焚香、点茶、品字、赏画、诵经、论道等,又有几个不是在书斋?
在嘉兴,历史上有很多出名的书斋或藏书楼,赵孟坚有彝斋,吴镇有梅花庵,项元汴有天籁阁,项笃寿有万卷楼,李日华有味水轩,高承埏有稽古堂,曹溶有静惕堂,吴骞有拜经楼,朱彝尊有曝书亭,蒋光煦有别下斋,沈曾植有海日楼……
溯其源,嘉兴藏书,发轫于宋,延续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清,余绪影响于民国,泽被当世,刻书亦然。



嘉兴两宋藏书、刻书知多少
非弃清明乐隐居,
特因景范面鸳湖。
观澜兴罢春风软,
濯足歌残夜月孤。
南宋淳熙五年的状元姚颖,曾在嘉兴范蠡湖畔筑圃读书,他仰慕陶朱公功成身退的淡然从容,不拘名利的高洁,便将居所取名景范庐。
这首《题景范庐》,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访景范庐时所写。
数十年后,这里又来了一位读书人。他就是岳珂,岳飞的孙子。
岳珂(1183—1243),字肃之,号亦斋、倦翁,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十月,他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相当于代理嘉兴知府,寓所也在范蠡湖畔。当时这儿属于嘉兴七十坊之一的金佗坊,所以岳珂以金佗园为居所命名。
他在这设立相台书塾,藏书、著书、刻书。
此时的嘉兴,距离升府(1195)已过去22年,正是繁荣鼎盛时。
嘉兴因1127年的建炎南渡,一跃成为京畿之地,又因南宋中兴之主宋孝宗出生于此,而成龙兴之地。
地理位置的提升,体制的升格,给嘉兴充分的发展机遇,嘉兴成为当时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发展,在宋朝推行文官治天下的时代大潮中,嘉兴文化进入第一个发展高潮。
其时,南渡的世家大族,多聚集于此,官宦云集,人才荟萃,不乏名士和名门之后。
著名诗人朱敦儒,隐居鸳鸯湖畔放鹤洲;著名学者王明清寓居嘉兴,有笔记《挥麈录》传世;赵氏宗族赵孟坚隐于广陈,书画自娱;岳飞之孙岳珂寓居金佗坊……
这里名师硕儒汇聚,文教大兴,宋代嘉兴进士463人,南宋高达381人。
“直接迁入的百官士人及其家族对藏书的大量需求,随之兴起的科举热潮对藏书日趋增长的渴求,均大大激发了藏书的发轫。”
谈及嘉兴两宋藏书、刻书发轫之缘由,著有《嘉兴藏书史》《嘉兴刻书史》的陈心蓉总结说,区域经济的长足进步、硕儒汇聚文教兴起等,为其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市场需求,雕版印刷业的精进,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为书籍的流通和收藏提供了技术支撑。
嘉兴早在北宋就已有藏书万卷的赵衮。北宋元祐年间,他以殿中丞致仕后归隐嘉兴,居三塔景德寺后。宋代嘉兴诗人张尧同曾在《嘉禾百咏》中,专门记述了他:
藏书几万卷,归老此林泉。
不为寻莼鲙,于公亦有贤。
南宋时,嘉兴辖内传于后世的藏书家明显增多,多为学者、名士,如岳珂、闻人滋、许棐、赵孟坚、卫湜等。
隐居于海盐广陈(今平湖广陈镇)的著名书画家赵孟坚以诗画藏书自娱,颇有闲情雅致。
他藏书很多,常常坐小船载着书籍琴弦和饮食餐具,迎着日出,挥毫作画,又于夕阳西下之时,于日下吟诗,有子固、彝斋等藏书印。

在两宋时期,藏书、著书、刻书常互为表里,在藏书家中,不乏藏书刻书兼具者。岳珂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岳珂藏书很多,这从他刻印、著述的书中可见一斑。
他为官之余,致力于典籍和古物收藏,曾到中原各地收集北宋文物典章,尤其是历代皇帝大臣的御笔和翰墨,编为《宝真斋法书赞》。除此,此书综合家藏的大量历代名人墨迹法书,汇集了从晋代到南宋的历代名人石刻、手迹。
《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甚高,“其间遗闻佚事,可订史传之是非;短什长篇,可补文集之讹阙”。
宋代刻书以赵、韩、陈、岳、廖、余、汪七家为最,岳就是指岳珂。《天禄琳琅书目·茶晏诗》将岳珂列为两宋私家刻书七大名刻家之一。他的刻书所就在嘉兴金佗坊家塾相台书塾内,其所刻诸书特别著名。
岳珂为保证刻本质量,严把每道流程,刻书必经广集并本、延请专家、确定校勘三步。近代版本学家叶德辉曾说宋时家塾刻本,“今所最著如岳珂之相台书塾刻《九经》《三传》”。
嘉兴籍清代文学家、藏书家钱泰吉在《曝书杂记》中对《九经》《三传》以及《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还指出岳珂刻印《九经》《三传》,以家中藏书为底本。岳珂家藏仅《九经》就有建本、江西本、越本、蜀本等。
岳珂还刻有自编《金佗粹编》《愧郯录》《桯史》等,特别是《金佗粹编》是他寓居嘉兴时利用家藏编撰,搜集前人著述、文献档案很丰富,是为其祖父岳飞辩诬之作。
岳珂自撰、辑撰刻本,后世递修、拓本等有不少传于后世,成为国家珍贵古籍,比如《桯史》《英光堂帖》等。
南宋藏书家卫湜也是藏、刻兼备。他以藏书、刻书为乐,自撰《礼记集说》刻印。两宋传世的刻书家还有卫樵、闻人耆年、张滋等。
特别是闻人耆年,他是宋代医学家,刻印的自编《备急灸法》,选入历代名医22则灸法,除孙思邈、葛洪有著作传世,仓公、华佗、徐文伯、甄权等都无著作传世,正是通过这本书,灸法经验才得以流传。在书中,他还绘制了11幅图谱,将各病症相关穴位标明。
两宋时,除了私人藏家以外,还有官府藏书,刻书更是形成了鼎足而立的官刻、家刻、坊刻等三大系统。
当时的嘉兴版刻盛行,嘉兴官府及儒学、海盐县官府、盐官县官府都有刻书传世,如南宋宝祐四年(1256)海盐县衙刻《澉水志》八卷,为宋代罗叔韶修,海盐常棠纂,周中孚题跋中称“叙述赅括,体例谨严”,《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冠以舆图”。
“刻书条件苛刻,既要有很好的刻工,又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嘉兴有这样的刻书家,这样的刻书氛围,可见当时嘉兴文化已经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了。”嘉兴市图书馆馆长沈红梅这样认为。
宋代佛寺藏书、刻书盛极一时,天宁禅寺、海会院、隆平寺、金粟寺等都以藏经著称。特别是海盐金粟寺,在北宋年间自制“金粟寺藏经纸”专供抄写佛经,名闻古今。
金粟笺用桑皮、楮皮加工而成,内外涂白蜡,又以药水濡染,这种纸精细莹滑,久存不朽,正是金粟寺享誉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叶恭绰曾在题跋中说,“相传浙中士大夫以其纸之佳,宋时即携取待尽”。
《金粟山大藏经》是以金粟纸书写,北宋熙宁元年(1068)由金粟寺广惠禅院发起编写的一部写本大藏经。目前,此经仍有不少残本流传,如国家图书馆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持世经》《阿毗达摩识身足论》《中阿含经》等都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宋代秀州惠云院刻《妙法莲华经》现藏台湾,这册梵夹装、宋刊小字本佛经,卷末有南宋秀州惠云寺僧人释德求的三则手跋,经文前,清代海宁籍金石僧六舟和尚题有,“秀州(嘉兴)惠云院宋刊妙法莲华经,道光己酉八月望前二日西湖南屏山净慈住山沙门六舟达受敬篆”。


藏书文化给城市文风以滋养
朱栏碧瓦照山隈,
竹简牙签次第开。
读破文章随意得,
学成富贵逼身来。
诗书教子真田宅,
金玉传家定粪灰。
更把遗编观得失,
君家旧物岂须猜。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曾以诗记录过那个时代轻财重书的藏书理念。藏书贵于聚财,士人把藏书当作重要的事情。这种藏书风气不仅让两宋藏书、刻书空前繁荣,也泽被后世。
嘉兴藏书、刻书之风,可说是其缩影。
嘉兴藏书家崇尚以藏书教育子孙、留传后世,希望以藏书惠及乡里,他们鼓励子孙和邑中子弟“守儒为准、守身为本”。
北宋时在嘉兴辖内有两位藏书家,一为海盐卫公佑,一为华亭卫公佐,两人都藏书很多,都有积极捐地办学的助学行为。
特别是卫公佐,个性慷慨,当时,邑中没有学堂,他和弟弟卫公亮、卫公望仗义相助。对于藏书,他有一种十分开放的态度,每次邑中有人来求书、借阅,他都慷慨以待。
陈心蓉和嘉兴南湖学院凌冬梅在研究藏书史时都注意到,两宋嘉兴藏书家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学者型藏书、刻书。特别是宋室南渡为嘉兴带来大批官宦士人,科举大兴,“嘉兴学者型藏书比较多,多是为了读书求学而藏书,真正为了收藏而藏书的不多。”

范蠡湖畔金明寺隔壁就是金佗坊旧址
发轫于两宋的嘉兴藏书、刻书对后世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南宋时,嘉兴作为京畿之地,经济文化繁荣。特别是明代,嘉兴受益于运河,水路交通发达,经济和文化事业达到高峰。
嘉兴藏书、刻书高度发达。最大的民间收藏家项元汴出现在嘉兴,他不仅收藏传世书画,也大量藏书,他的哥哥项笃寿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刻书家,他所刻《东观余论》字画精工,是清内府天禄琳琅藏书室的珍藏,他的儿子项德棻所刻《研北杂志》《避暑录语》《武夷新集》等都是精品。
谈及嘉兴藏书之盛,刻书质量之好,陈心蓉以近代版本学家叶德辉《书林清话》所列的一组“明人刻书之精品”数据说明,全国26家,浙江15家,嘉兴占4家,“1629年前后,罗马传教士利玛窦的著作《交友论》首次翻译刻印就是在嘉兴”。
对那个藏书文化繁荣的时代,沈红梅颇为感慨,这种繁荣在明清达到鼎盛,延续至后世,“我们这里一直是藏书之地,藏书、刻书家很多,比如曹溶、朱彝尊等,比如海盐藏书世家张家近代还出了出版家、藏书家张元济。清代藏书、刻书最发达的是海宁,在全国都有影响力。”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所列清代500余位万卷以上藏书家,海宁就有11人,其实,这一数据尚未完全涵盖海宁超万卷的藏书家。
明代以后,嘉兴形成很多藏书世家。凌冬梅最大的感受是这种书香延续至今,“最重要的是读书、藏书的地方文化风气及藏书世家诗书传家的家风和精神传承。”
她近几年致力于女性藏书研究,明显感受到基于丰饶的读书、藏书土壤,这里的女性也有着很好的读书风气,往往参与家族藏书行为。特别是世家之间彼此联姻,女性会把娘家的读书、藏书风气带到男方家里去,还会进行两个家族的藏书交流,明清之际,出现如柳如是这样的女藏书家。
发轫于两宋的藏书、刻书之风,影响了后世的诗书传承,对嘉兴文风和教育产生直接影响。读书气氛好了,文风盛了,科考的人就多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同时,也保留了一地的文脉传承。
他们注重保留、整理地方文献。历代嘉兴藏书家编著、刻印私藏,高承埏《稽古堂丛刊》、胡震亨《秘册汇函》等不少大部头丛书刊印。
沈红梅作为《嘉兴文献丛书》副主编,对嘉兴先贤藏书、刻书感受颇深。《嘉兴文献总目》统计的近万种嘉兴文献中,仅史部,历代嘉兴人著述2600余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可圈可点。
他们收集整理古籍,潜心校勘辑刻,补阙订讹,藏书、刻书风气传承至今,对嘉兴文化带来很大影响。
“文风鼎盛,就连小镇都有诗派,比如梅里诗派。大量地方文献得以保存,离不开嘉兴历代文人的藏书、编著、刻书之功,比如三百年数代接续的《槜李诗文合集》。我们编辑《嘉兴文献丛书》,特别幸福,有这么多地方文献可供选择。”
嘉兴有开放的藏书态度,沈红梅以为至少从项元汴就开始了。
但追溯嘉兴藏书家,你就会发现,早在两宋就初见端倪。
卫公佐常将藏书开放给邑中人,南宋时的藏书家闻人滋也有着与卫公佐类似的藏书态度。他是秀水闻湖(今王江泾)人,与陆游曾同在敕局为书籍、文书删定官,精于小学,人称老儒,陆游称他“读经义衮衮不倦,发明极多,尤邃于小学”。他曾在嘉兴南湖畔建草堂,有《南湖草堂记》。
他藏书丰富,喜欢借给别人。对此,陆游深有感触,曾在《老学庵笔记》里说,嘉兴人“闻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过蔬豆而已。郡人求馆客者多就谋之。又多蓄书,喜借人。自言作门客牙,充书籍行,开豆腐羹店”。
他们有意识地征集、辑录文献史料。朱彝尊收集大量明人诗集,编《明诗综》,曾和同时代文人联名发起《征刻唐宋秘本书启》。他们认为保存古籍,真正使其起到作用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流通。曹溶有《流通古书约》,首次提出古书流通法,朱彝尊也延续了这一观点。
嘉兴市图书馆是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嘉兴很多先贤在西学东渐中得风气之先,加之这里深厚的藏书土壤,浓厚的读书风气,为清末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打下基础。
沈红梅作为图书馆人对此非常自豪,“或许正因为嘉兴有开放的藏书态度,清末才在海宁这个私家藏书、刻书最盛的地方,出现了全国第一个县级公共图书馆。”

金佗坊旧址
面对丰厚的藏书、刻书文化,在禾城文化复兴的当下,嘉兴如何继承发扬?
嘉兴历代包括藏书家、刻书家在内有多少收藏家?他们有何收藏特色,有哪些藏书、藏品,背后有什么故事?
不少学者认为,嘉兴正在重建天籁阁这一嘉兴收藏文化的重要标识,是否可以借此梳理、挖掘、展示嘉兴的收藏文化,了解那些藏家对后世的影响,对重点的藏书家、藏书世家,如项氏等可进行重点研究,有可能的话,再收集一些流落在外的藏书、藏品。
热爱嘉兴地方文化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最直接的传承是让先贤们保存下来的古籍真正活起来,用起来,让躺在博物馆里、图书馆里的文献“数字化”。
在传播手段上,则可以采用多媒体手段,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如短视频等,不仅传播知识,也要传承精神,让它们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这个工作,嘉兴文化工作者一直在做,他们正逐步将古籍整理影印出版,还建立了地方文献数据库,正在编辑出版的《嘉兴文献丛书》就是其中的代表。
发轫于两宋的藏书、刻书为嘉兴崇文厚德、耕读传家的风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因此才会有嘉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这种精神,不仅是爱书、藏书的书香精神,更是我们的先贤代代相传,尊重文化、守护文化,自发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担当。

2022年12月9日《嘉兴日报·江南周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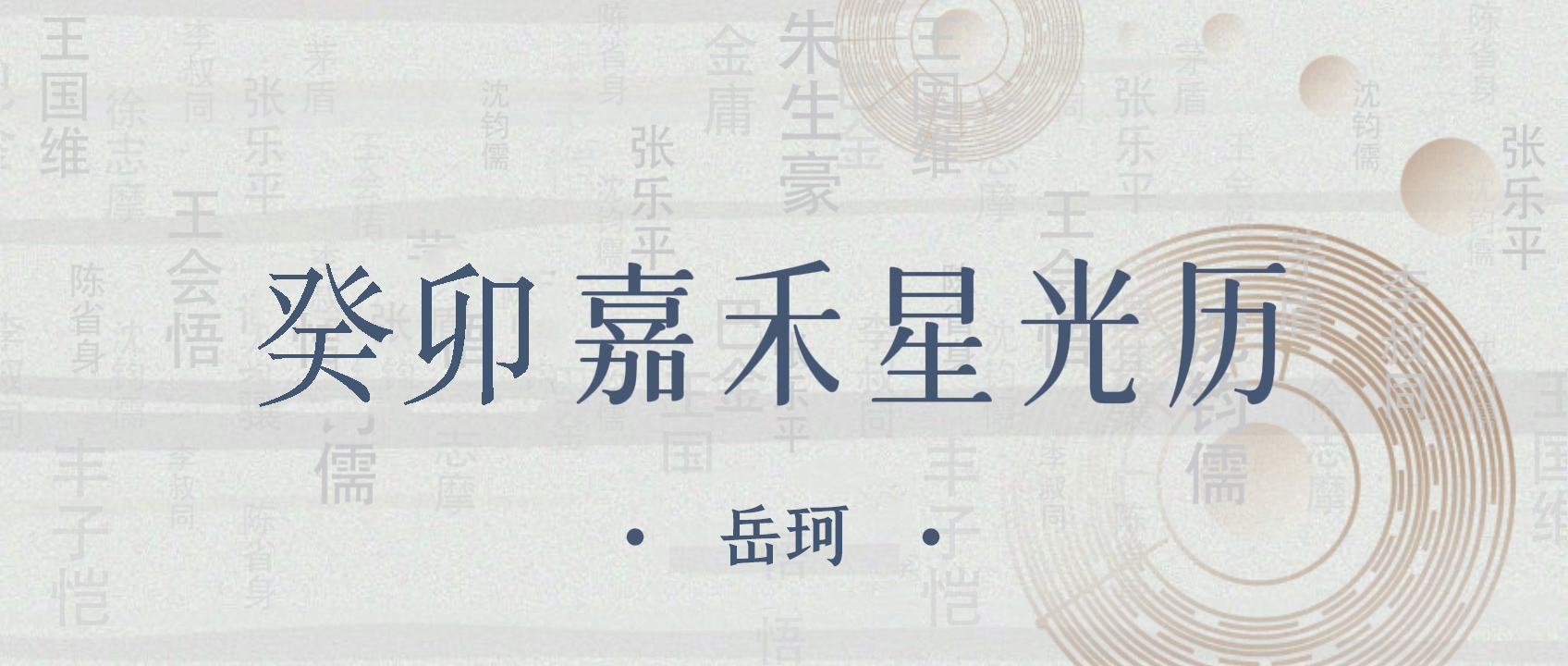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