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迟子建,1964年生于黑龙江漠河;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韩、荷兰文等海外译本。

我所看重的作家品质:朴素、慈悲

柏琳:
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你谈到自己的创作有越来越多的能量,还有很多想写的内容。从产量和写作耐力上看,你看上去像是保持了一种旺盛而匀速的前进姿态,但从你说的话看,似乎更好的作品还在路上,也许人当“不毁少作”(或曰“不悔少作”也可以?)你如何看待自己从前的作品?非要比较的话,是否存在某几个让自己满意的写作峰值?
迟子建:
在写作上,我是个不知疲惫的旅人,但我的状态又是你所形容的那样,节拍不快不慢,匀速前进,这比较符合我的性格,而这也是中年之后写作的最佳速率。初学写作时,我可以利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一夜不睡,写出个万字短篇,那时体力充沛。而现在即便是写一个短篇,至少也要花掉十天八天的时间。
关于写作能量,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矿藏,我自己的矿藏里还埋藏着哪些有待挖掘的宝贝,无须探测,自己最清楚。当然,不断挖掘,也是对自己已有成果的不满足,寄希望于下一部作品能做得更好一些。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该有的作品,所以我对过去三十多年的作品,总体是满意的。如果说长篇,我可能偏爱《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越过云层的晴朗》《白雪乌鸦》《群山之巅》,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向着白夜旅行》《踏着月光的行板》《酒鬼的鱼鹰》《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草原》《空色林澡屋》等,短篇《雾月牛栏》《逝川》《亲亲土豆》《一匹马两个人》《清水洗尘》《一坛猪油》《采浆果的人》《微风入林》《花瓣饭》《野炊图》等。
柏琳:
在写作中,你是否经历过和自己的搏斗?请和我们分享一个你和自我搏斗的例子,你如何突破自己的限度或者克服自己的障碍。
迟子建:
记忆最深的应该是1998年开始写作的《伪满洲国》,这部小说涉及到伪满时期的皇宫贵族、贩夫走卒等。这里有弹棉花的、开当铺的、做店小二的、当土匪的、做教师的、沿街乞讨的、英勇抗日的、沦为汉奸的等等,我提到的这些人,都是中国人。而那段历史,离不开日本人。
如何塑造日本人,对我是个挑战。在小说中,我刻画了几个个性复杂的日本人,羽田,一个厌战的军官;中村正保,一个随开拓团来到中国的善良的农民,以及在细菌部队做人体试验的军医北野南次郎。当侵略战争让一些人沦为机器、嗜血成性时,另一些人却在血光中看见了自己孤独的影子,以及没有未来的生活。那种被战争裹挟的失去青春和归途的感觉,是悲凉的。我在小说中,尽量克制主观情绪,客观描述这场战争中非正义一方的无辜者,写出他们复杂的人性,战争的残酷性也就凸显了。
柏琳:
对你来说,理想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在三十多年写作中,你是否失去过写作的感觉?
迟子建:
理想的写作状态,就是你在写作时,即便在黑夜,也感觉背后有光;而你在完成作品时,与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不忍告别的感觉。三十多年来,写作特别不在状态的时候极少,因为我不会在不在状态时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而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写作是没有缺憾的。即便正在写作状态中,作品也依然不是完美的。
柏琳:
那么你接下去想写的内容是什么?主题上是否会有什么新的改变?
迟子建:
可能是个人习惯吧,我轻易不会在写作前透露下一部作品要写什么。当年筹备了多年的长篇《伪满洲国》,我在两年写作期间,也只有亲人知道我在写什么。写作长篇前,我尤其不愿意让媒体知道,因为这会招来各路出版方,书没开始写而谈出版,过早“嫁女”,不是什么好事情。而静悄悄地写作,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再说了,写作跟足球一样,即便你排好了阵势,真到了场上,纸上风云和球场风云一样,也会在实战中,适时变阵。
柏琳:
你所看重的作家品质是什么?
迟子建:
朴素,慈悲。
黑土地的精神气质,像是青铜锻造的

柏琳:
新世纪近二十年来,就你观察而言,东北的社会样态发生了什么变化或断裂吗?
迟子建:
中国所经历的变化,当然也就是东北所经历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是新中国发展的铺路石,起着重要作用。这里的粮食、森林、煤炭、石油、制造业,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哪一样缺得了他们?
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真正接轨,激发了内生动力,使经济腾飞。可是东北在全国性的起跑中,却落在后面。这里原因很多,东北是老工业基地,面临的转型更为艰难,再加上关外是苦寒之地,交通相比不那么发达,以及人们还没有自觉地把自己推上市场和潮流的强烈意识,造成了如今的东北相较于南方发达省份,在漩涡中打转,人才外流严重。
柏琳:
故乡东北的黑土地是你作品灵感的源泉,当然你也有脱离这块“乡土”的作品,比如转向都市生活题材的《晚安玫瑰》,但被很多读者认为这种写作“少了迟子建的味道”,变得不从容,有了束缚和紧张感,“个人特色没有了”,你如何评价自己那些“脱离黑土地”的作品?
迟子建:
首先我得说,黑土地当然也包括了城市。其实我2000年出版的个人重要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其中一半的篇幅就是城市书写。新京、奉天、哈尔滨,是《伪满洲国》中主要的三个故事发生地。《晚安玫瑰》写的是犹太人在哈尔滨的遭遇,自然也算黑土地作品。只不过我的读者习惯了我的笔触及他们认定的“乡土”,所以对它产生了不适应感。我还有一部长篇《白雪乌鸦》,写的是清王朝末年哈尔滨的大鼠疫,我搭建了一座一百年前的哈尔滨旧城,写得很投入。
柏琳:
你曾谈过俄罗斯自然文学对你的影响,比如拉斯普京的作品。可能是东北离俄国比较近的缘故,我也能从你的作品中嗅出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清新气味。俄国文学是否影响了你的写作观念?或者,俄国文学版图中其他作家对你的精神启示是什么?
迟子建:
我最早很喜欢屠格涅夫的作品,其后接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纳博科夫、蒲宁、帕斯捷尔纳克、拉斯普京、索尔仁尼琴等等大师的作品,曾写过一篇散文《那些不死的魂灵啊》,谈的就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西伯利亚与我的生长地,隔江相望,所以俄罗斯作家笔下的森林和草原以及活动其中的人,对我有天然的吸引力。这些作家同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背负苦难,但理想之光从未泯灭,有一种不屈的气质,像是青铜锻造的。
从文学的意义上讲,没有人不是小人物

柏琳:
在小说中,你的语言总带着鲜活、生动而质朴的民间气息,我特别好奇你获取小说素材的方法,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等作品的写作,你扎根民间的方法是什么?
迟子建:
迟子建:我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对生活中的好与不好,都会拥抱,都能接受,这使得你的艺术神经,始终处于敏感状态。小说,说穿了是靠一个一个的细节来构建的,而没有生活的原声底色,细节不生动,没有立体感,作品也就失去了生机。至于我的秘诀,这个实在难谈,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观察生活的独家秘笈。
柏琳:
“底层文学”近年来十分热闹,但也存在诸多争议,你的小说其实更多都在“底层”打滚,你认为,怎样的“底层写作”才不会给人带来伪善、贩卖苦难、隔膜等负面印象?
迟子建:
如果说底层,是否有高层?从众生平等的角度来说,小说无论涉及到哪个层面,都是人间,都是生活,都是苦与乐。比如我写作《满洲国》,里面少不了溥仪,少不了抗日英雄,那么我写他们,采用的是写小人物的笔法,写他们的日常性,所以从文学意义来说,没有谁不是小人物。
柏琳:
《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群山之巅》《北极村童话》等小说,我认为其中也隐含着一种“风俗史”的民间野史的写作风骨,请谈谈你自己的“民间野史”的写作趣味。
迟子建:
风俗在小说中,很像中国画中的留白,看似虚空,没有具体指向,实则是小说意境表达的砝码之一。拿沈从文和萧红的小说做个比较,你会从风俗中发现,如果没有这样的“砝码”,小说就失去了魂魄和韵味。如果把《边城》中的风俗描写或者《呼兰河传》的风俗描写剔除掉,这两部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将失去光彩。
END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编辑推荐】
· 十年酝酿,七十万字,编年体讲述
· 伪满洲国(1932—1945)十四年间东北的沧桑苦难
· 上百位人物,三教九流群生众相,战乱时代人间悲欢
· 上千里纵横,从哈尔滨到奉天,从大兴安岭到乌苏里江
·全文修订,无删节,增补跋一篇
· 精装重量级再版,富于理念的设计,版式疏朗,适于收藏。内文采用特制轻型纸,完美实现视觉上的力量感与实物的轻盈感。
本期编辑 牧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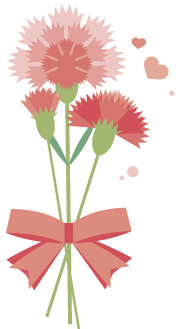
送福利
当当购书福利
48小时打折满减
春天,从读书开始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