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德华·吉本
作者一再强调罗马帝国的灭亡实即蛮族与基督教的胜利,因之在这两个问题上着墨甚多,删节本也多予保全。罗马人将帝国以外的民族统称为“蛮族”。这些居住在帝国周围的民族往往构成帝国的边患。书中最初出现的蛮族是日耳曼人,有专章叙述他们的原始生活,并指出到2世纪后期他们已拥有以铁为锋刃的武器,发动过一次各族联合对帝国的进攻,为罗马兵团所击溃。但是到3世纪时,情况有了变化。帝国面貌依旧,但雄风已消,军纪松弛,边防削弱;而蛮族人口增殖迅速,有战士百万,并从罗马学到作战艺术,因之构成对帝国边境的威胁。法兰克人、阿勒曼人、哥特人此时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然而帝国仍有相当的抵御力量。特别是奥勒良在位时整饬纪律,军威复振,威服各族,安定边境。书中对于他的祝捷活动作了详细描绘,在献俘的行列中包括了哥特、汪达尔、萨马提、阿勒曼、法兰克、高卢、叙利亚和埃及等各族战俘。但这已是强弩之末了。作者还评论了帝国在边境安置蛮族的政策。普洛布斯曾招募蛮族一万六千人当兵,分成小队,驻守边疆,并收容蛮族战俘和逃亡者在边境设置新移殖区,拨给土地、牲畜、农具,指望能够从中获得兵源以充实边防。然而事与愿违,蛮族人员不习惯务农,不愿受约束,往往流窜,成为暴乱之源。
而当民族大迁徙的波涛涌起时,内外呼应,西罗马帝国遂被淹没。东罗马帝国的边患主要来自东方。阿拉伯人的扩张吞食掉其东部领土,土耳其人的崛起摧毁了这个古老帝国。关于基督教,吉本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由于我始终相信《福音书》的传播和教会的胜利与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密切相联的,所以我着重于这一变革的原因和影响,把基督教徒自己的著述和辩解同异教徒投向这一新教派的公正或憎恨的目光加以对照。”为节编本全文保留的第十五、十六两章即是按照这一意图撰写的。此时吉本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业已形成,对基督教的传统说教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在第十五章开头的地方写道:“神学家可以……随心把宗教描绘为降自于天,披着原有的纯洁。史学家则……必须发现宗教在久居地上之时,已在一个软弱和堕落的人类中受到了不可避免的错误和腐化相混杂的污染。”他揭去神学家所加于基督教的纯洁外衣,冷静而客观地对基督教久居地上所沾染的尘俗现象作了深入的理性的考察。他的笔法是曲折、含蓄的,有时是借用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的。他介绍诺斯替派的教义时说,这个教派“对以色列上帝作了不敬的描写,把他说成一个易于冲动和犯错误的神,爱憎无常,……不能在这样的性格中看到全知、全能的宇宙之父的特征。
”这样的转述虽然冠以“不敬”字样,实际却在张扬异端,贬抑“降自于天”的基督教。书中对基督教大肆宣扬的神迹,例如驱除魔鬼,起死回生,舌割后而能言,耶稣受难后天地冥晦等一一加以否定。尽管这些神迹有教会文献可征,并经神学家、主教、教皇等先后作出见证,然而他却指出即使其中“最有力的见证”也不能“祛除不信者私下的、不可救药的怀疑”,这种怀疑之所以“不可救药”是因为它来源于理性的验证。从这里人们清楚地看到吉本的历史批判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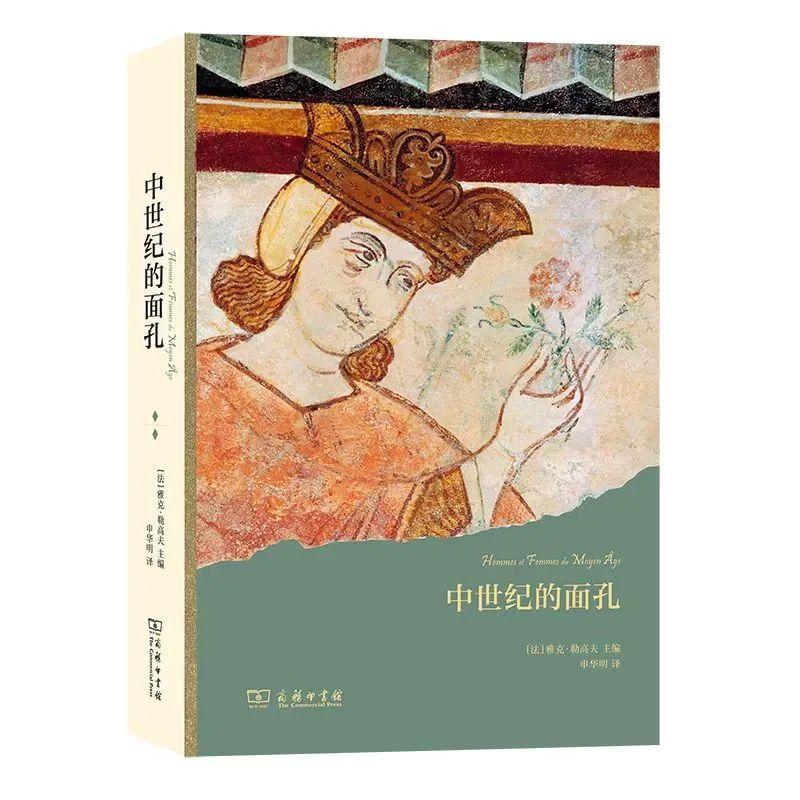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