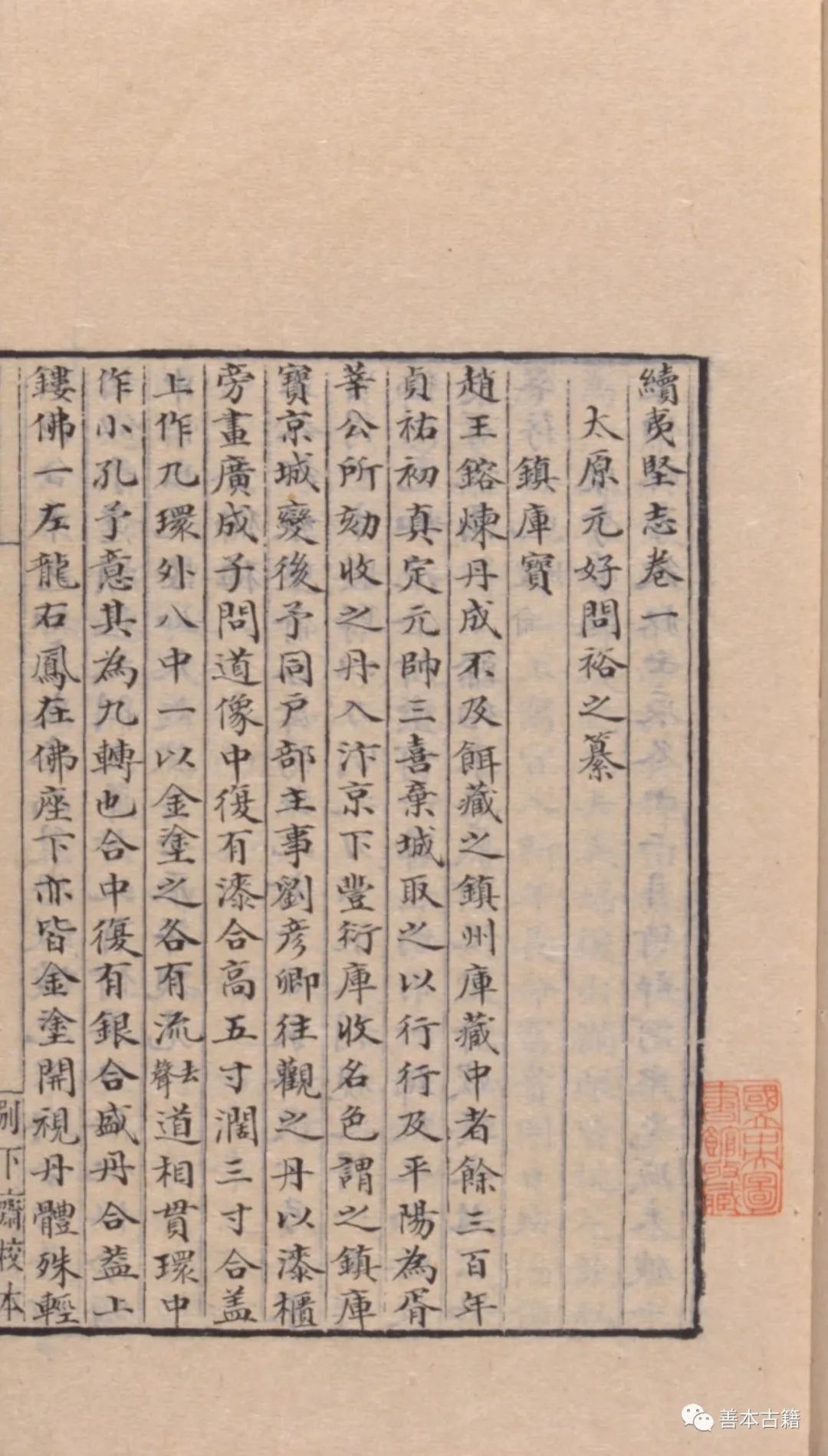
元好问在金亡前后所创作的《续夷坚志》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李正民先生就其《续夷坚志》说到:“此《夷坚志》虽续洪氏,而适当百二之会,灾变频仍,五行乖舛,有开必动,动关运会。非吊诡之卮言,实讥祥之外承。不贤识小,又何讥焉?”在肯定《续夷坚志》的文史价值的同时,也将其与《夷坚志》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但元好问之所以采用《续夷坚志》这样一个具有明显继承性的名字,可见其想法并不是要与《夷坚志》分庭抗礼,而主旨在于续写承继。因此,本文将以士人为切入点,对两者之间在内容上的联系做简单的介绍。
在展开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先对此处的“士人”做出界定。余英时在其《士与中国文化》中将“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沿用其定义,同时,为与两书中的官员形象相区分,我们在此做出更进一步的界定,将“士人”定义为以科举为重要途径,以仕宦为主要人生目的,但尚未步入仕途的知识分子。
一、重视前程
既然士人将仕途视作人生的最终目的,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重心必然是自身的前程。如《续夷坚志》中的《京娘墓》,元老在上京赶考途中“霖雨泥淖,车不能进”“车独行数里而轴折”,在这样艰难无措的情境下,却得到昔日与之相恋的女鬼京娘的帮助,“知君有难,故来相慰耳”。京娘的如此相助,得到的不是恋人重逢的喜悦,也不是雪中送炭的感激,而是仅仅一句“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夷坚志》开篇第一个故事就讲到了士人对于自身前程的关注:孙九鼎遇到已死的姐夫,当知道见到此人对自己身体无损之后,“即询前程”。此人尚知将身家性命置于官位前途之前,更有甚者将仕途看得比自身性命更为重要:在《杨证知命》中,杨证已对自己的命运做出预测——“吾必登第,正恐死不久;脱或下第,庶可少延”,但是在此情况下,他仍然不想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为功名之心所驱,卒入试”,最终“及到官,数月而卒”。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当时士人对于科举结果、自身仕途的极度重视,将其看作人生的头等大事。
二、迷信鬼神
在宋金,科举虽然越发正规化,使得每个人都有公平的竞争机会,但同时也使得参考人数激增,导致录取比例下降。每个人都有做官的机会,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官,更多的人付出一生的心血却只能是一事无成。在这种巨大的竞争压力之下,士人除了寒窗苦读之外,只能将命运交付上天,求仙问卜成为士人间“时尚”而又无奈的举措。《续夷坚志》的《北面大王》中参政梁公肃举子时“祈仙问前途”,《盗谢王君和》中王献可在待榜中“祝骰钱以卜前程”。除此之外,更有《黄真人》用一整篇的篇幅叙述士人在前途未卜之时对鬼神的依赖,在此篇中,士人之父先是询问黄真人考试题目,等到考完试之后,又询问其是否登第。在考前想通过鬼神得到提示,以求能超过他人独占鳌头,等到结束后,又迫切想知道结果,将当时士人对科举的重视、内心的忐忑刻画得入木三分。《夷坚志》中更是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士人通过占卜、祈仙求梦、相面、祝盃筊、卦影甚至靠博具等各种迷信手段询问自己的前途。如甲志卷四《孙巨源官职》中巨源“尝登州谒东海庙,密祷于神,欲知他日科第及爵位所至”,卷七《罗鞏阴遣》中“学有祠,甚灵显,鞏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祷”。
对科举的重视与对前程的惶恐,不仅使得士人主动去求仙问卜,更将生活中的一些奇异事件与科举前途相联系,认为这是上天给予的征兆,暗示着自身的前途,如甲志卷四中的《驿舍怪》中,四人同止道旁驿舍,其中三人都被一个怪物嗅“士人之面至足”,只有侯元功没有受到怪物的闻嗅,果然科举“元功擢第,而三人者遭黜”。甚至一些寻常认为不好的事情也可看作吉兆,如《续夷坚志》中《贺端中见鬼》,按照常理见鬼并非好事,但贺却“此举登科”,把鬼作为可以带来科举好运的“吉祥物”。有些士人不仅把梦境与现实联系起来,甚至把梦中的情境落实到现实中,以求让现实复制梦境,最突出的一类就是为应梦而改名。甲志卷六《李似之》文中,正路因梦中有人“出片纸,阔二寸许,上有‘弥逊二字以示之”而企图改名,即便在当时“须申礼部乃得易”的复杂情况下,依旧得偿所愿。
尽管对科举给予充分重视,既刻苦攻读又祈仙拜神,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愿,录取比例过低导致科场失利的人数总比如愿的人要少。这些落榜士人在主观上并不承认是自己学术上的欠缺导致落榜,而是尽其所能地为自己的失利寻找借口,认为科名和前程都是命定的,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也改变不了天定的结果。在《续夷坚志》的《玉儿》一篇中,鬼夫人玉儿“以手遍抚睡者云:此人及第,此人不及第”,而结果竟是“皆如其言”。在未科考之前便可预先知道科举结果,由此可见科名早已命定,与临考发挥、平素学识等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夷坚志》丙志卷十一《锦香囊》中,一妇人称仍是布衣的龚滂为“中丞”,并解释道“君明年登名乡书,即擢第,前程定矣”。
既然科举结果是前定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获得了不同的科举结果呢?时人更多地将其归结为阴德的作用,积德便可以得到好的前程,这种积德可以是自己做了善事,如《夷坚志》甲志卷五《许叔微》中,许因行医“所活不可胜记”,所以梦中有人以诗的形式告知他会做官,结果也确实如梦中所言。还可以是父辈或其他亲属做过善事,功德也可惠及子孙,如《续夷坚志》中所记的《王叟阴德》中,王叟凭良心行医,不仅身体康健,举家“夫妇皆结发,推户为县中第一”,其子孙更是官场有名:“第四子荣,以军功官宣武军鲁山尉;长孙中武举,某州巡检”,这正是一人为善,全家受益的典例。相反,如果自己做过缺德之事,就会遭到报应,哪怕本应有的科名也会落入他人囊中。《夷坚志》丁志卷五《三士问相》中,相者对前来问前途的黄崇言道:“姑以君今日论之,法当得升朝官以上,奈何作不义事,谋财杀人,阴遣已重,速归。非久当死,不必赴省试也。”其为谋家产杀死新生弟弟,因而失去本应有的官,性命不久。可见德行在科举中的重要作用。
三、“另类”士人
在官本位的宋金社会,以仕途为最要紧之事是社会的主要潮流,但是总有人能够从功名利禄中脱身而出,读书仅仅是为了实现人生理想,而非升官发财。《夷坚志》支庚卷四《碧石骰盆》中的姜潛便是这样一个读书不为功名之人:“姜好学,有隐操,崇宁间,郡以其名闻于朝。降召命再三,竟不肯起,乃赐先生之称。”《续夷坚志》中《卫文仲》一文,也为我们记述了卫文仲这样一位不图名利的士人,“性好淡泊,读书学道,故仕宦不进”。这在当时的社会可谓异类,可正是这样的异类,给当时争名逐利的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读书风气,也因此得到了作者的赞赏。
以小见大,由我们以上从《续夷坚志》与《夷坚志》在士人形象这一方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续夷坚志》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夷坚志》的传统,将研究眼光放在两者的比较上固然有其研究价值及合理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关注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发展。(刘倩倩)
参考文献:
[1]何卓点校,洪迈撰.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李正民.续夷坚志评注[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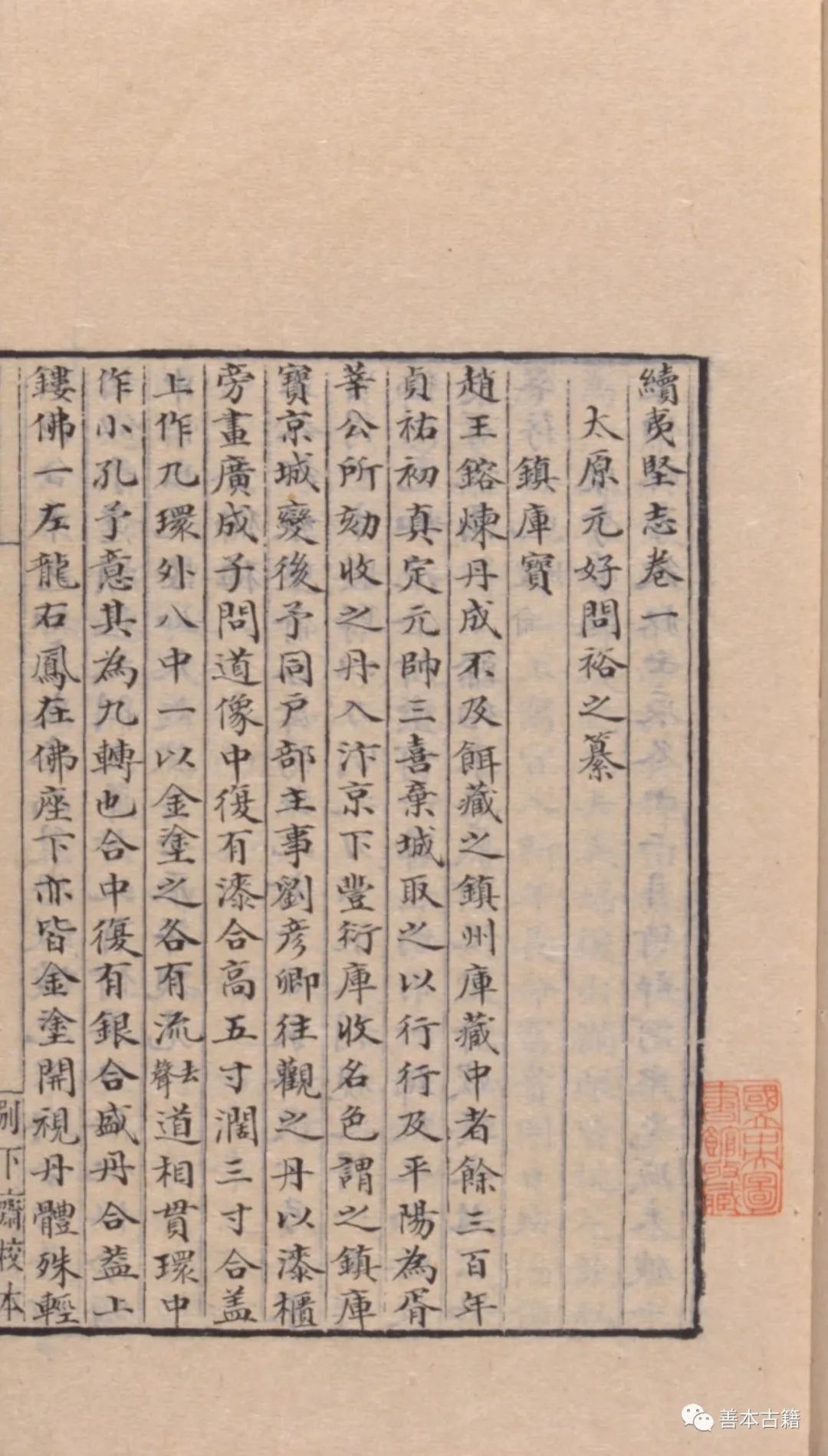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