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度规划项目“历史学元问题的研究”等。近年来致力于吕思勉遗著的整理工作,已编辑出版吕思勉文集十余种。本文原刊于《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1年第7期,经张耕华老师授权发布,特此致谢。
摘要:史料是历史认识的桥梁,但不能机械地解读为但凡史料都是桥梁,有时所谓史料其实就是历史本身。同样,史料是历史认识的依据,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史料依据,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实际的情况往往是“有证据者,未必尽是;无证据者,未必尽非。”至于史料的分类,本无严谨一以贯之的分类原则,讲解时必须注意分类的相对性而切忌绝对化。大部分史料在留存时都会掺入作者的意图,就中学历史教学而言,了解史料作者的意图较难,了解史料使用者的意图较易,后者可以通过史源的比对来辨析、讲解。
关键词:史料的作用 史料的分类 史料作者的意图
自“史料实证”列入中学历史教学的核心素养之后,我因曾在高校讲授过“史学概论”课程,便与中学界的同仁有了更多的交流与讨论。交流与讨论的话题可分为二个方面:一、集中在“史料”方面,二、集中在“实证”方面。本文就是将讨论“史料”话题时的札录,梳理、归纳为三个主题,稍加条贯,整理成文,或可供学界同仁参考,也希望能引起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研讨。
一、关于史料的桥梁作用等
关于史料是历史认识的桥梁,常见于“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一类的著述。比如,有著述认为:历史认识不是一种直接的认识,而是一种借助中介物 —— 史料进行的间接认识。这里说的“中介物”,就具有“桥梁”的含义。这样的看法,当然能获得事实上的支持。已经消逝的许许多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今人之所以还能形成对它们这样或那样的认知,全是因为这些人物、事件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史料,还有许许多多历史人物或事件之所以湮没无闻、或我们所知甚少,也是因为它们没有或者极少留存了史料。在这里,史料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之间的中介物,没有这个中介物,史家对史事的认知就无法实现。在这种意义上,把史料称之为历史认识的“桥梁”“中介”并无不当之处。《新课标》对史料的解读,也强调史料是通向历史认识的桥梁,大概也是吸取了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
但是,史料是复杂而多样的,说史料是通向历史认识的“桥梁”,主要着眼于文字史料或口述史料,如考察实物史料,情况就有所不同。一把石斧、一本古书,它们就是历史本身,如果我们研究原始先民的工具、研究古代的印刷术,它们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身。在这里,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是可以直接面对、直接观察的,其间并不需要有认知上的“桥梁”或“中介物”。所以,有些著述就特地指出,把史料视为历史认识的“中介”,主要还是针对文字史料的立论。其实,如要深查细究,文字史料也未必全是“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文本也就是研究对象本身;研究文本,也就是研究作者的思想,这里也没有什么“中介”或“桥梁”。文本就是思想的存在物。或说“思想”存在于思想家的大脑皮层,那也不是说研究思想家的思想就是要研究他大脑皮层中的东西,需要劈开大脑去直接观察他的皮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史料保存的手段、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像通过摄影、录像、录音之类的技术手段保存下来的史料,都是历史实况的存录,我们通过录像、照相、录音等史料去认识历史,实在就是一种直接的观察,其间也无什么“桥梁”或“中介物”的媒介沟通。
《新课标》对史料的解读,又强调它是认识历史的依据和基础。这一点很重要。文学可以虚构,史学必须是言之有据。历史认识能否成立,全看它是否有史料的依据。这是《新课标》与当下中学历史教学的一个亮点。然而,这一点也不能做简单或机械的解读。史学家吕思勉曾说:“有证据者,未必尽是;无证据者,未必尽非。”这里说的证据,就是以史料为依据;说“未必尽是”“未必尽非”,就是说证据与结论之间有着很复杂的关系。
何以“有证据者,未必尽是”?这可以从史料、史家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史料本身的问题。众所周知,不管是文字、口述或实物的史料,都有一个是非真伪的问题,依据有误有伪的史料,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未必尽是”。这是来自史料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史家的问题。不管是一把石斧,还是一本古书,它们本身不会开口说话,是史学家把它们用作证据来建构某些历史认识的。把石斧或古书用作证据,就包含了史学家对石斧或古书的解读。在历史学中,同样的史料而有不同的、甚至相反对立的解读,那是很常见的现象。比如《诗经》中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里的“私”字 —— 郭沫若与范文澜就有不同的解读,范氏说这是农奴的私田,用来论证西周封建说;郭氏说这是田官的私田,用来证明春秋战国封建说。
或说这是文献解读上的分歧,实物史料就不会这样。其实,实物史料也离不开史家的解读,也同样存在分歧与差异。比如,二里头的考古发现,自是研究先秦或早期国家历史的重要史料,但学界对它的解读还有很大的分歧。查阅当下通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上)》第2课说:“考古学家在河南洛阳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存。”《中国历史(七年级上)》第4课则说:“夏朝的中心地区主要在今山西南部、河南中西部一带。考古学者在洛阳平原发掘出夏王朝的一座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这里有宫殿建筑群、大型墓葬和手工业作坊,还有平民生活区和墓葬群,反映了夏王朝的阶级分化和等级界限。”二里头遗址,究竟“很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存”,还是就是夏王朝的遗存?初高中教科书的编写者就有所不同的解读。如果再去比对考古学界的解读,你就会对教科书的说法产生怀疑。二里头考古队前队长许宏曾说:“甲骨文的出现证明了自己的王朝归属,从此开始进入信史时期,在这之前,二里冈、二里头、龙山都属于史前时代。”他又说:“考古学和上古史领域不能排除任何假说及其所代表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考古研究结论的相对性,考古研究结论有相对性,能给定论的专家靠不住。希望人们从学理、材料、推导过程的角度来看考古学,而不只是期待学者给出一个结论,“中小学教科书标准答案式的思维是危险的。”[9]
至于 “无证据者,未必尽非”,那也容易理解。日常生活中,我们对家族祖辈的记忆,往往并无直接的史料,只是凭借一些间接的史料,也可以形成一些“未必尽非”的认识,只是它们不那么具体或细化。《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课有“禹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说法。这实在也没有直接的史料依据,而是凭借一些间接史料演绎推理而得出的结论。我们知道,演绎推论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必须十分小心。“演绎法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具有特别的复杂性”,不能“用简单演绎来代替具体研究,让复杂的历史事实适应一般原理和公式”。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否可靠,全看演绎所依据的理论是否可靠。理论如果不可靠,那么演绎推理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站不住脚。
总之,强调史料是历史认识的依据和基础,不能简单机械地解读为:依据了史料,我们就能获得正确的一致公认的历史结论;更不可解读为:依据了史料,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一切难题都能释然。
二、关于史料的分类
史料的类别,通常分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几大类别,每一类别之下,又可以分出许多小类别,比如实物史料,就可以分出人类的残骸、遗址、遗物等等。我们知道,史料的范围是随着历史学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因研究方法与技术的进步,许多此前未知的材料都会逐渐被发现而用为历史研究的史料,所以《新课标》在文字、口述、实物史料之外,还列有图像史料、音像史料,这都是随着摄影、录音等技术的运用而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
《新课标》要求学生“了解史料的多种类型”,又要求“能够区分史料的不同类型”。在有些学科里,“了解”“知道”了什么,也就可以依样画葫芦地学着去操作解题,但历史学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本古书,可以归入文字史料,也可以归入实物史料;竹简木牍,可以归入实物史料,也可以归入文字史料。至于究竟归入哪个类别,则要看研究者利用的是什么信息。利用古书(简牍)上的文字信息,那就视它为文字史料;利用古书(简牍)的实物信息,那就视它为实物史料。换言之,如果我们拟题设问,那么题干上一定要交代相关的解题背景,否则学生无从回答或者可以做出两可的回答。
“知道”了史料分类,并不能依样画葫芦地“区分”史料,还是因为将某个史料归入某一类别,常常也是约定成俗的,并无严格的学理和逻辑上的理由。史料分类的原则,大致是依历史信息载体的属性而定。载体是文字的,便称“文字史料”;载体是口述语言的,便称“口述史料”。《胡适口述回忆》原是胡适英文口述的录音,现在已译为中文且翻印成书,所以通常都是阅读这本口述回忆,而不是去听原始的英文录音,但习惯上都称它为“口述史料”。如果有人“抬杠”,说《胡适口述回忆》应该归入“文字史料”,似乎也不能说是错。读《史记·淮阴侯列传》,司马迁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等等,这说明他为撰写韩信的传记,曾专门到韩信的家乡去访问耆旧故老,这当属于“口述史料”。《旧唐书》的传记,大多取材于国史旧有的列传,或私家的行状、家传和谱牒等,但也采用了时人的口述,尤其在《酷吏传》里,因为“酷吏多数不得令终,史馆中不可能有此类人的行状、家传,自得多凭采访。此外,有些令终的文武官员在传末却讲点其人的短处,如生活不检点、贪污、无家教之类,这在行状、家传、碑碣上是绝对不会写的,可断定也是来自采访。”那么是否要严格地按照其实际情况,把《史记》《旧唐书》中的史料分为“文字史料”与“口述史料”两类呢?但如约定成俗地就把它们都归入“文字史料”,似乎都不能算错。
像《史记》《旧唐书》等传统典籍,有些著作称其为“文献史料”。按《文献通考》对“文献”的解释是:“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考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谓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可见古人所谓的“文献”,“文”指文字记载,“献”指时人口传言论。这与上文所述《史记》《旧唐书》等包含二类史料的实际情况很符合。所以,有些著述在论述史料分类时,并不在“文献史料”之外再立“口述史料”,而将后者以“口碑”的名目归入“文献史料”下的一个小类。当然,现在常用“文献”一词来泛指传统典籍,而不再区分“文”“献”的含义差别。不过,既然将“口述史料”单列,那么与之并列的类别名称,似不必再用“文献”而应该称为“文字”史料,这样的话,类别的区分就能更清晰些。这自然也不是吹毛求疵,而是想说明史料的区分归类、甚至类别的命名,大体上还遵循着约定成俗的做法,并无严密的学理、逻辑上的规则。
高校“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之类的课程,之所以有史料分类的介绍,目的是:一、收集史料时有大致的范围和方向。二、了解史料的特点与价值,施以相应的研究方法。《新课标》的编写也体现这样的思路。实物史料需要有考古学的方法,文字史料需要有训诂、校勘和考证的方法。中学的历史教学不以培养未来的历史学家为目标,而是希望“学生通过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进一步拓宽历史视野、发展历史思维”,“为未来的学习、工作与生活打下基础”。按这个目标,因史料分类而延伸到的方法介绍应该落在哪里?我便想到在文字、口述和实物之外的另一种史料。
吕思勉在《历史研究法》中将史料分为“记载者”(书本)与“非记载者”(非书本的)二种,“非记载者”一类又列出“法俗”小类。何谓“法俗”?吕氏说:“法系指某一社会中有强行之力的事情,俗则大家自然能率循不越之事,所以这两个字,可以包括法、令和风俗、习惯;而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在古代,亦皆包含于俗之中;所以这两个字的范围很广,几于能包括一个社会的一切情形。”这样,“法俗”二字几乎包含社会生活的一切现状。又有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状也可用作历史研究的史料依据。如法国史学家布洛赫就说,要研究法国历史上的农村地貌,就要“先得考察和分析现在的地貌状况”。
“法俗”、“地貌状况”等都可以归入“实物史料”一类,但它们的加入,改变了我们原先对“实物史料”的看法——“死人不会说话,石头不能开口”——现实生活中“法俗”“地貌”有温度、有形象,且活生生地展示在我们眼前,随时随地可供我们体验观察。这些活生生的“实物史料”的加入与运用,改变了我们的治史观念和研究方法。这就是布洛赫所说的:“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舍此别无他途。┄┄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建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吕思勉也说:“学问在于空间,不在于纸上。要读书,先得要知道书上所说的,就是社会上的什么事实。”他强调“读书与观察现社会之事实,二者交相为用,而后者之力量实远强于前者。我们对于学问的见解,大概观察现社会所得,而后以书籍证明之。断无于某项原理茫然不知,而能得之于书籍者也。”他认为“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
将社会上的现状与书籍上的记载相互参证,吕思勉称之为“活的史学研究法”。《新课标》也有“能够以实证精神对待历史与现实问题”课程目标,这是否与吕氏提倡的方法相通?不过,中学的历史教学如真以拓宽历史视野、发展历史思维,为学生“未来的学习、工作与生活打下基础”。那么,布洛赫、吕思勉的观念及其方法就很值得在教学中尝试。
三、关于史料作者的意图
《新课标》有多处强调“史料作者的意图”, 这是此前中学历史教学未有涉及的新内容,也是当下中学历史教学的创新点。
文字史料是人书写的,口述史料是人们口耳相传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书写者、口述者的“作者意图”。《新课标》还列有的图像史料(绘画、雕刻、古地图、照片等)和音像史料(录音、录像等),绘画、雕刻都是画家、雕刻家的制作品,自然就会有“作者的意图”的掺入,照片、录音与录像等虽然都是真实场景的实况实录,但它们都是由摄影师、录音师们制作的,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真实场景的实况实录而忽视它的“作者的意图”。实物史料有没有“作者意图”?这不能一概而论。如上文提及的绘画、雕刻、古地图就存在“作者的意图”,凡是制作而成的史料,难免就会程度不同地带有“作者的意图”。而实物史料中的人类化石(如几颗元谋人的牙齿、几件北京人的头盖骨),它们并不是某某人制作品,谈不上有什么“作者的意图”。近年来,学者运用分子遗传学的方法,提取现代人身上的DNA来研究人类的起源,这个DNA也就成为实物史料的新品种,它同样也没有什么“作者意图”可言。不过,现在流行给后人留下的“时间胶囊”,虽属于实物史料,但它与文字、口述史料一样带有明显而强烈的“作者意图”。
英国史学家卡尔的《历史是什么?》里,有一段就是讨论史料“作者的意图”问题。他说: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情景是有缺点的,这主要不是因为许多部分已偶尔丧失,而是因为大体说来这种叙述是由雅典一小部分人作出的。……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是为我们预先选择好、决定好了的,而且与其说是偶尔选择决定的,倒不如说是由一些人选择决定的。这些人有意无意地受一特定观点的影响,并且认为支持这一特定观点的一些事实是有保存价值的。……这些人相结这一点,而且要求别人也相信这一点。”这里所说的“为我们预先选择好”“选择决定的”“有保存价值的”等,就是史料在留存时掺入的“作者(留存者)的意图”。
如上所述,历史学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科,史料“作者的意图”问题也不能以演绎的方式去做“凡是什么,就是什么”的解读。文字、口述史料的“作者意图”是明显的,但也不能用“凡是文字、口述史料,就一定带有作者意图”去解读。如研究汉代土地买卖中的地价问题,研究者常常感慨资料的稀少,《汉书》中仅有的四五条,也是记人记事时附带叙述的,即便记录了也是语焉不详。这些地价史料,就说不上有“作者意图”了。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以“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来区分这类现象。[33]这也是考察史料的另一种角度。不过,同理,“有意”与“无意”也不能死板地用作划分文字史料与实物史料的标尺,一定要考察史料的具体留存情况而定。
《新课标》论述“史料作者的意图”,用了《资治通鉴》关于“三家分晋”的叙事为案例。论述以设问的方式提示史料“意图”的二个考察视角:一、《资治通鉴》何以“三家分晋”为开篇,这是从记事(记载什么?不记载什么?为什么这样的记载?等等)上读出“作者的意图”。二、司马光对“三家分晋”及其发生原因的评说,这是从史论、史评上读出“作者的意图”。其实,这个案例也可以用来解读史料“使用者的意图”。换言之,史料的“意图”问题,可以分为史料留存上的意图与史料使用上的意图二种。由此,《新课标》提出“能够在辨析史料作者意图的基础上利用史料”的要求,就可以分解成二个目标,即辨析史料的作者的意图与辨析史料使用者的意图。
就中学历史教学而言,辨析史料作者的意图较难,辨析史料使用者的意图较易。比如,把司马迁的《史记》当做史料,要教会学生去辨析司马迁的记事意图,非得对《史记》或史学史方面有一定的研究才能胜任,因为史家记事往往并不交代他的意图,有些甚至有意隐讳他的意图。而辨析史料使用者的意图,自也有多种思路,但其中最简便易行的,就是核对史料的原文。史学家陈垣曾在北京大学创设“史源学实习”课程,指导学生追溯史料的来源,比对原文与引文的异同,用来纠正引用上的错误。中学历史教学如引入史源学的方法,自不必在史源上有过严过高的要求,但能以常见的文献(如“廿四史”)或史学著作为源头,核对原文,比对异同,也能看出史料使用者的意图和目的。
比如,有关“二重证据法”的编写,都会引用史学家王国维的这段论述为史料: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这段文字见于王先生的《古史新证》,查找完整的原文是这样写的(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将原文分为①②③三个小段):
①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判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③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将原文与引文比对,可以辨析出史料使用意图的几种情况:如果编写者的目的是介绍“二重证据法”,那么就使用史料中的②;如果编写者的目的是介绍“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那么就应该使用史料中的①②③;如果编写者的意图是要写出一个“主旨清晰的王国维(关于二重证据法)”,那么就使用史料②;如果编写者的意图是写出一个“前后有矛盾的王国维(关于二重证据法)”,那么就使用史料的①②③。将引文与史料原文做一比对,史料作者的意图与史料使用者的意图都可以辨析清楚。
又如:《历史 选择性必修1》第5课节录《隋书·刘炫传》一段史料编写成一则“学思之窗”,所引的史料是这样写的: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核对《隋书·刘炫传》的原文,这段史料原是隋初礼部尚书牛弘与刘炫之间的对话,读者若将引文与《刘炫传》的原文做一番比对,就能读出牛弘、刘炫对话的原意、《隋书》作者的意图,以及《历史 选择性必修1》编写者的意图。借用此则材料,比较彼此的差异,或可以引导学生试写研究性的小论文。
余论
核对史料原文,不仅可以读出史料使用者的意图,还可以发现史料运用或历史结论的错误,这就落实了《新课标》所说“使用资料作为证据来检验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解答”的教学目标。其实,这里不必限定于“自己”。因思维定式的制约,“自己”的错误,往往还要靠“他人”来发现,何况一切历史认识的结论都要经过史料的检验。由学生自己动手,用核对史料原文去发现历史读物、甚至教科书上的错误,那是最实在、最有效的“实证意识”“实证精神”的教学。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学生早晚会知道你的“史料实证”只是装点门面。这不仅破坏历史学与历史教学的科学性,更会败坏人心。此也可见教书育人者的责任重大。
本文注释从略,如有引用请参考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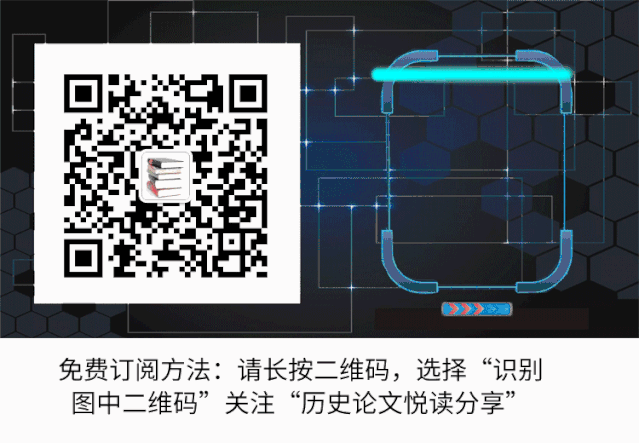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