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口的先贤们
随着“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子”papi酱在《吐槽大会2》的首秀大热,“吐槽”这个网络流行亚文化现象算是完成了登堂入室的正名过程。

papi酱名言 我不做主咖,谁还能做主咖
与大家依据字面来理解的“不吐在碗里不痛快”的意思大相径庭的是,“吐槽”其实是日本的一种搞笑艺能节目“漫才”中—的一种叫“突っ込み”的搞笑手段,有点像郭德纲的相声,由两人完成,其中一人针对另一人话语中的漏洞和错误挑刺开黑,达到搞笑的效果,这种搞笑形式传入台湾后,变成了与“突っ込み”发音相似的“吐槽”,随着动漫文化传入了大陆,逐步演化为采用调侃、戏谑的幽默方式挑毛病、指出不合理之处,抒发心中不满等情绪的一种相当流行的亚文化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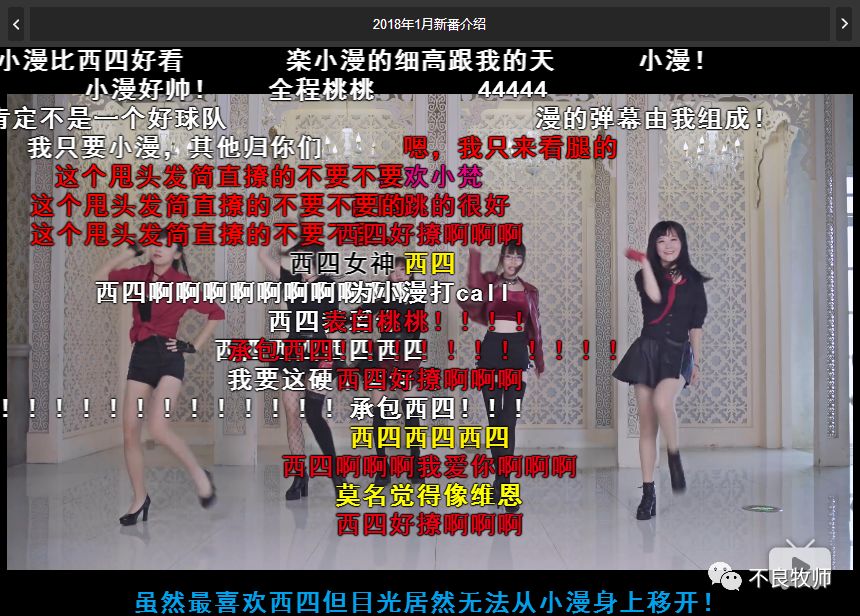
各类宅文化视频是B站大神云集之地,弹幕遮天蔽日
俗话说温饱生闲事儿,大数据显示,B站大神2017年共吐槽十亿多条,独霸全网,随着大神们在二次元世界的横行,“吐槽”迅速通过弹幕二向箔向我们所处的这个三维空间实现了全方位无死角的升维打击,迅速占领了微博、微信朋友圈等原本属于心灵鸡汤的阵地,意外达到了为民除害大快人心的效果,尤其受到饱经长辈朋友圈温情攻势凌虐的年轻人的欢迎。以papi酱为代表的网络槽神也同时开火,对网络热点事件和生活中的很多令人不爽的现象实现了精准定位和外科手术式的垂直打击,在负责搞笑的同时,还兼职了网络民意代表。

papi酱对网络键盘侠的精准定位和垂直打击说出了许多网民的心声
其实这都不算啥,因为中国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一批堪称上古槽神的打击乐爱好者,嗯你没看错,是打击乐,因为他们很早就发现,打击别人真的可以带来快乐。
俗话说,不爽就要发泄,愤懑就要吐槽,不知“突っ込み”为何物的中国古代一点也没有影响上古槽神们的发挥,《世说新语》就是一本记载两汉到魏晋时期各种神吐槽的奇书,鲁迅先生评价这本书“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简而言之,这是个典型的大V时代,士大夫和贵族阶层是吐槽的主力军,皇帝也身先士卒带头吐槽,比如书里有这个么个神段子: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晋元帝司马睿新得了一个儿子,于是遍赏群臣,马屁精殷羡赶紧上去谢恩说,皇上新得了儿子,普天同庆,我作为臣子也没有什么功劳,白得了这么多赏赐(心中很不安啊)
晋元帝笑着说:“这事能让你有功劳吗(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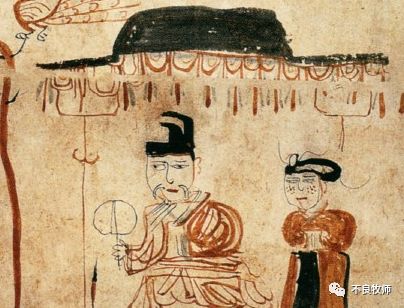
这事儿能让你有功劳么?
放在现代,这个吐槽一定会被收录进“一句话怼死马屁精系列”。
皇帝的吐槽水平如此之高,那些无所事事的士族文人更是不遑多让,因为政治上的不得意,生活中的无所事事和精神上的极度空虚,除了在五石散、酒精和共享娇妻这种事儿上感受生命的短暂和虚无之外,他们也在吐槽上倾注了大量精力,形成了一批堪称艺术的神吐槽。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 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 桓又问:“官有几马?” 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这样的参军还是早点勒令退伍,退回原籍比较好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
汉语中把“晒”引申出展示和炫耀的含义,可能就是从这个段子里来的。

狂野炫酷魏晋段子手们
不仅男性槽神辈出,女性也不甘示弱,魏国将军王凌的儿子王广娶了大将诸葛诞的女儿,洞房之夜想给老婆来个下马威,于是出言讥讽说,你这表情长得不像你爸爸一样高贵啊,妻子当即反唇相讥说,你一个大丈夫不能像你父亲王凌一样出将入相,反而要求妇人长得像英雄豪杰,要脸么?夫人毒舌堪比吐槽女王蔡明,王广自讨没趣,只好闭嘴,如果他生活在这个时代,也许还能用上张绍刚老师那句无可奈何的金句:“你这个冤孽”。

张绍刚老师的绝望金句
各位槽神完全不能满足于日常生活中的随机吐槽,干脆组织了魏晋版的吐槽大会,美名其曰为“清谈”,清谈不谈国事、不谈世事、专谈一些玄而又玄的事,最初的形式类似于哲学讲习会,大家分别演讲,再彼此以问答的形式进行探讨,著名的《兰亭序》记录的就是一次典型的清谈。但随着时间推移,清谈逐渐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类似脱口秀和辩论赛的模式,夹杂着各种神吐槽,因为服用各种丹药而长期不洗澡的文人高士横七竖八卧于一堂,一边互相吐槽,一边从身上捉出虱子来掐死,那场面只有用酸爽二字可以形容。

真正的扪虱卧谈会远不如现代人想象的那样潇洒飘逸
草根阶层的崛起
停留于历史现象的表面,把活动在历史舞台前面的少数英雄人物的作用尤其是他们的意识和言行的作用加以夸大并绝对化,而把特定时间段里默默无闻的广大人民群众及其历史活动置于视野之外,而完全忽视了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绝对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代,尽管人民群众也有不逊于贵族士大夫的智慧,但其言行却很少被认真地记录下来,从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两宋开始,以草根阶级为主体的市井吐槽开始萌芽,逐渐在吐槽届占有了一席之地。

清明上河图里的北宋段子手,一群吃瓜群众围着他听说书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士大夫阶层一员的吐槽能手苏轼功不可没,苏轼把吐槽从抒发不满情绪和玄学清谈中拉回了生活,真正实现了生活化的市井吐槽,政治上的持续倒霉不但增进了他的吐槽水平,更让他有机会深入民间,与人民群众深度接触,向人民群众传播吐槽文化。
苏轼连年遭贬,越贬越远,最远被贬到了海南岛,无奈写诗自嘲道:
人家养子爱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害到公卿
这是拿自己的儿子开涮,吐槽自己的官运,苏轼天生聪明,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然而官运不佳,连年遭贬,一直被贬到天涯海角,只好写诗借自己的儿子吐槽自己的命运,心态相当豁达。
苏轼自嘲自黑不遗余力,黑起来别人更是毫不留情,文学家秦观与他亦师亦友,因为词作《满庭芳》中有“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句”而被苏轼起了个“山抹微云君”的外号。秦观有一脸漂亮的胡子,堪称北宋关二爷,有一天一边捋着胡子一边得意的对苏轼说
“君子多乎哉?”(我这胡子多密呀)
苏轼淡定的回答说;
小人樊须也(小人胡子都密呀)
估计秦观当时脸都绿了

苏轼老师的胡子估计长得不怎么滴,不然不带这样黑人的
苏轼还成了第一个古代中医黑,欧阳修曾对苏轼说“所谓医者,意也——取其意向即可治病”,意思是缺啥吃啥,吃啥补啥,吃啥治啥。苏轼立马回以神来之笔:
如公言,今学者昏惰,当令多食笔墨灰。(像你说的这么治病,那学习不好的家伙应该多吃点笔墨烧成的灰啊)
如果苏轼活到今天,估计会号召那些试图靠食用野生动物来挽回自己男性尊严的笨蛋去吃钢筋吧。

我嗦大哥你不行关我啥事,吃啥补啥你应该去吃钢筋啊
苏轼吐槽的功力和极强的生活气息让他成为了草根阶层的市井吐槽崛起后第一个模仿的对象,巴赫金说过:“语言对语言的模拟,它包含了不甚恭维,不太严肃的成分,有开玩笑、戏谑、逗哏、调侃的性质”,不少的古代神吐槽中,尽管主角是苏轼,真正的作者却是不知名的群众或者底层文人,这种假托苏轼的吐槽一度非常流行,充分展现了人民群众的吐槽功力,比如一个民间故事里,一个土财主请苏轼去吃饭,期间为了炫耀,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小妾在酒席上跳舞,并请苏轼作诗,苏轼不假思索写下一副对联:
舞袖蹁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声撼半天风雨寒
这嘴可真是够损的,乍一看上去是称赞人家小妾舞姿美妙,仔细一看,上联是黑人家小妾有缸粗没缸高除了屁股全是腰,下联是黑人家小妾嗓门大声音高歌喉一开像公猫,可谓是损到家了。

你真不用黑我
这种假托名人式的草根市井吐槽后来越来越流行,主角不仅限于苏轼,也逐步扩大到其他名人甚至皇帝的头上,这种对名人甚至权威的艺术再创造带来了后现代主义的萌芽,比如野史中有这么个故事:
咸丰皇帝新得一民间卖艺女子,甚是宠信,连日不上朝堂,陆懋宗上书让咸丰皇帝注意影响,咸丰皇帝以为陆懋宗是大清海瑞,结果叫人一查,原来这个卖艺女子曾是陆懋宗私下包养的小三儿,于是大笔一挥,在陆懋宗的奏折上批到:
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

岂不恨哉岂不恨哉岂不恨哉
这个故事的人物、时间、细节均经不起推敲,很明显是民间吐槽手假托咸丰皇帝和陆懋宗的名号编的,带有很强的解构主义讽刺手法的味道,说明到了明清时代,民间吐槽手们已经摆脱了模仿士大夫吐槽风格的初级阶段,开始走上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解构主义吐槽之路,在明末和清末两个社会矛盾激化的时代,草根市井吐槽逐渐带有了文化对立和阶级对抗的色彩。
诸神之战
时至今日,士大夫阶层的贵族槽神和草根阶层的市井槽神之间的争斗,已经演化成占据社会主流话语权的精英槽神和试图建立流行亚文化意识形态的民间槽神之间的战争,福柯30年前说的“话语即权力”在网络时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印证,吐槽的流行和微博这种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公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话语权,使他们在在表面上可以同文化的上游进行平等的对话和接触(有时候这种对话可能不那么友好),从而使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得到“想象的解决”。
不过这种在网络上无组织的对话和接触经常失去控制,从脱口秀和互相吐槽演变成为网络暴力和互相谩骂,油腻中年男和猪精女孩这对CP从相爱相杀发展到不死不休就是一例明证。
这时候扪虱卧谈会这种复古的吐槽模式就体现出了自己的优越性,《吐槽大会》这种现代版的扪虱卧谈也就应运而生,嘉宾层次丰富,风格鲜明,伊能静、papi酱、郎朗、冯潇霆、潘粤明等,既有娱乐明星,又有体育冠军;既有文化名人,又有草根大V,还有热门网红,针对自身槽点、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一应俱全,总有一款适合你。但无论如何互相吐槽,都无伤大雅和和气,得到的只有观众的大笑和掌声。看嘉宾吐的不爽,还能发弹幕吐,真正实现了共享吐槽,不吐不快,不吐不休,欢迎观看,欢迎来吐,《吐槽大会》等你来吐。

等你来吐

不良牧师
一起听刘先生布道
微信公众号ID : Gulagisland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