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态与流变”学术讨论会在中华书局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办。在20篇报告组成的5场主题讨论中,与会学者进行了热烈交流。经授权,澎湃新闻刊发各主题讨论的文字内容。本文内容系第四场“官修唐史与《通鉴》的文献学考察”及第五场“南朝诸史的历程”主题讨论。
两场讨论分别由两个修订团队成员带来: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团队承担两《五代史》、《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的修订,中山大学景蜀慧教授团队承担《齐》《梁》《陈书》修订。修订需要以对相关史书的版本学、目录学、史学史研究为基础,而在文献整理工作中获得的一手经验,也促使学者反思如何理解、对待史书文本,形成研究思路与视角的更新。第四场讨论包括四篇报告:郭立暄(上海图书馆)《元本〈通鉴〉胡注校余述略》、夏婧(复旦大学中文系)《〈永乐大典〉引存〈旧唐书〉考述》、唐雯(复旦大学中文系)《〈顺宗实录〉详本再审视——兼论唐实录的辑佚》和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系)《隐没与改篡:〈旧唐书〉唐开国纪事表微》。第五场讨论包括三篇报告:景蜀慧(中山大学历史系)《现存六种宋刊本〈陈书〉简述》、唐星(中山大学历史系)《唐初〈五代纪传〉撰修考》和周文俊(中山大学历史系)《异文的历史——以〈宋书·孝懿萧皇后传〉一处异文的重新校读为线索》。

郭立暄
郭立暄讨论胡注《通鉴》的版本,此前《通鉴》版本研究重在宋本,但就利用胡注而言,明国子监所藏元明递修本内部的复杂变化亦极应重视。报告人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为线索,调查各地所藏元明递修本,了解其各叶的具体补板年代,发现该本在南监至少经过十次递修,加上元代初印本,目前存在十一个梯次印本。
对比不同印次,主要有三方面发现。一是初印本各卷后附胡三省识语三十四条及题诗一首,是反映胡三省著书过程的重要资料,早印本已删去绝大部分,吴勉学本、陈仁锡本、胡克家本亦无。
二是旧说此本为至元兴文署刻本,由胡克家本称其底本有王磐所撰《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王国维已考证王磐致仕时间早于胡注成书时间,不应为胡注作序。今见初印本无王磐序,弘治以下印本亦无,疑该序为明前期误入,旋即撤去。另外,四川图书馆藏本有嘉靖二十年、二十一年两任国子监祭酒邹守益、龚用卿所作序文,言及国子监补板情形,为他本所无。
三是对比南监递修造成的文本变化。嘉靖二十年以下误字叠出,嘉靖三十八年本最劣。又注文一些内容在初印本文字完足,在第三梯次的静嘉堂本中已经脱落,胡克家翻刻本或阙如,或同于后出版本填充的文字,或自行模拟填充。由此亦可推测胡本所据接近第三梯次印本。又吴勉学本、陈仁锡本所据底本,通过文本比对推测,大约为嘉靖二十年的印本。
此前中华书局的标点本《通鉴》以素称精良的胡克家本为底本,辅以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的校勘成果,但章校未涵盖对胡注的校勘。通过以上版本调查可知,初印本胡注《通鉴》依然有不少优于胡克家本翻刻所据底本之处,中华书局修订本《通鉴》改用初印本为底本,可提高胡注文本质量,是明智之选。
夏婧的报告讨论《永乐大典》所存《旧唐书》的基本性质,及它在《旧唐书》修订工作中的作用。
《大典》虽是晚期类书却能对《旧唐书》校订产生重要意义,有两个特别条件。一是《大典》的编纂成书早于《旧唐书》现存完整版本的刊行。《旧唐书》现存最早的全本是明嘉靖中闻人诠刊本,此后版本皆从此而出。宋元版本传世稀少,有南宋绍兴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但所存篇幅不及全书三分之一。近年在抄本方面有所突破,发现叶石君校钞本九十八卷和嗣雅堂钞本三十五卷,都提供了比闻人本更早的《旧唐书》文本信息,相对接近于绍兴刊本。《永乐大典》于永乐元年七月下诏编修,至六年缮写誊钞完成,尽管其今存卷帙主要是嘉靖末的录副本,但录副基本亦应保存初纂所据的典籍面貌。其中所录《旧唐书》底本应属宋元旧本,可以弥补《旧唐书》版本流传一线如缕的缺憾。除了时差因素,《大典》编纂往往将一部书整体不加别择去取地抄录在相关条目之下,恰好有利于保存所抄典籍的原有文本面貌。因此,《大典》具备校勘《旧唐书》的基本条件,值得进一步考察。
关于《永乐大典》所引《旧唐书》版本性质及其与《旧唐书》宋刻、旧钞本关系,有两方面可以证明。一是《大典》部分文字仍保存宋讳阙笔形式,可推知所据《旧唐书》文本应源出于南宋。二是对《大典》与现存《旧唐书》诸抄本、刻本及他校文献对勘。报告以《大典》保存的《旧唐书·高祖本纪》沙汰僧道诏为例,发现八则异文中《大典》有五例与嗣雅堂钞本、叶校一致,与叶校相同异文更达七例,与作为他校的三种内典文献也相对接近,而与后出的闻人本分歧显著,竟无一例相同。
此前报告人考察嗣雅堂钞本时,曾判断《旧唐书》原貌与唐宋同源史料记载具有较高一致性,《大典》引存之《旧唐书》亦可作进一步证明。报告人通过校勘实例,举出涉及的他校唐宋文献,如《太平御览》引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P.3590《故陈子昂集》、《文苑英华》、《唐大诏令集》、《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典》文字皆与之一致或接近。
上述判断的另一面折射出对《旧唐书》版本流传变化的认识。明刻闻人诠本有简单的文字讹误,也有不少超出文献整理基本原则的文字改动,尤其是因对唐人制度、语言习惯疏于了解而导致误改,致使《旧唐书》版本面貌在宋明之间出现较大的分歧和转变。在明刻本成为清代以来诸刻直接援据的祖本之后,对《旧唐书》版本体系、文献源流的认识理解更形成一定误导。

唐雯
唐雯通过对《顺宗实录》的辑佚,重新考虑该书的成书与流传问题。《顺宗实录》最初是由韩愈领衔,在韦处厚三卷本《先帝实录》的基础上增修为五卷,路随等受命刊去德宗顺宗朝禁中事,亦为五卷。《通鉴考异》称北宋时内阁有详本、略本两种《顺宗实录》。目前一般认为,详本即韩愈原本,已佚,今天所见《顺宗实录》是经过路随删改的略本,且从《通鉴考异》所引详本来看,两本差异不很大,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值得重新思考。
详本《顺宗实录》虽不传,也有迹可循。《册府元龟》、《唐会要》、《唐大诏令集》等文献虽未标出处,但实际上保存了大量唐实录内容。如果其中的顺宗朝编年条目能够在与详本有直接史源关系的《旧唐书本纪》及今本《实录》中找到对应,基本可以判断该条即《顺宗实录》佚文。利用这种办法,在《册府》中发现《顺宗实录》佚文近三十条。由这些佚文判断,详本中大量诏敕原文及不甚重要的事件不见于今传略本,且详本在史实上更为准确。这一发现打破了传统的详略两本《顺宗实录》差异不大的观点,值得重新思考详略两本的关系。
文宗诏改《实录》时,规定的删削范围仅限于禁中密事。而略本较详本佚文所少者远不止禁中事,亦多无关政治因素。考虑到当时参与《实录》工作的史官本已对改修持反对态度,应该不会在文宗已经妥协的删削范围外自行加码,则略本不应出于文宗朝诏改。很可能韩愈原本在唐代已经消亡,详本是路随修订本,而通过韩集保留至今的略本只是一种节抄本。
报告最后还通过详本《顺宗实录》的辑佚经验展望了辑佚学在电子检索时代的前景,主张跳出根据明引的书题搜罗零碎佚文的方式,通过对文献史源关系、文本特征等的整体把握,可以合理地搜集恢复出更多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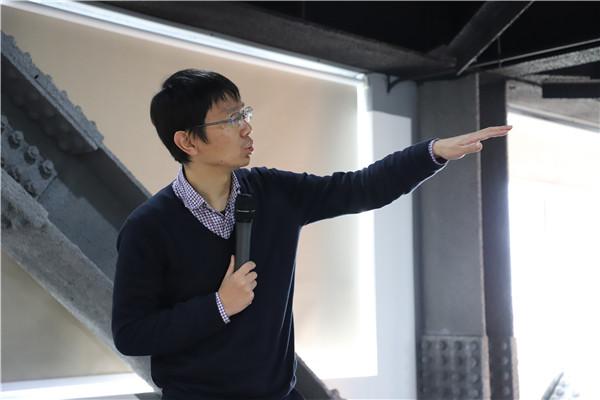
仇鹿鸣
仇鹿鸣讨论李唐开国期历史的编纂。此前学者也大致认为李世民对于唐初历史编纂有干预,虽然讨论不少,但多属“翻案式”研究,强调《大唐创业起居注》或《旧唐书》当有一误,表彰李渊个人的功绩等,未能辨析相关材料史源,障碍之一是《创业注》与《旧唐书》间的关键环节“实录”已经亡佚。目前可以从《册府》中恢复一部分高祖、太宗实录的文本。比较这三种李唐开国史文本,大体上可以判定《旧唐书》本纪基本承袭实录,而《创业注》虽然属于另一史料系统,但叙事的顺序、重点以及文字都与实录、旧纪大同小异,可以推断贞观中纂修《高祖实录》时,曾将《创业注》作为重要的取材对象。
实录与旧纪对《创业注》纪事的删减,大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创业注中连篇累牍的诏命、劝进文字等节略减省,其次则对李渊起兵时与突厥联络的细节颇有讳饰。
实录与旧纪增益改写的部分更值得注意,“增加”的部分可以说比直接了反映了太宗的意图,一方面是强化太宗本人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实录增补事迹亦处处贬低太子建成的能力与事功。因此,在高祖、太宗实录中刻意增润种种扬太宗、贬建成的细节,实际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故事格套,直到现在依然影响着我们对于唐建国史的认知。
散落于各人纪传中的李唐开国史事,不但较为零碎,而且缺乏如《创业注》可资比勘的参照物,既往学者措意较少,报告则从立传与改写两方面切入进行了讨论。由实录改编国史,只有部分人物传记能够被保留。通过《旧唐书》功臣传之首的卷五七附传前的一段文字,可以推知唐国史中功臣立传标准,是拼合武德初免死功臣与玄武门之变后封功臣食封两份名单。未能列入武德元年免死功臣名单的“太原元谋勋效”,即使在唐开国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在高祖实录中有传,若未能在太宗登基后获得封赏,也无法在国史中立传。这种做法或有便于操作的技术性考虑,但也暗符太宗一朝,推重追随李世民削平群雄之功臣,轻忽太原元从的基调。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旧唐书》高祖功臣传记中对功臣形象的描述。若干痕迹显示,唐初功臣传记中存在一些普遍性的改写,怀疑其中常见的与太宗募集参与太原起兵或由太宗引见高祖等记载,亦是一种有意的叙事格套。
最后一场主题讨论,景蜀慧报告了对《陈书》几种宋刻本的调查。南北七史传世版本中,如尾崎康所言,“《陈书》传本状态最佳”。本报告主要涉及六个藏本。
一是国图藏宋刻宋元递修九行十八字本的残卷,仅存十六叶。《旧京書影》和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皆未提及此本,据藏印、扉页内签条内容,此本为龚心钊旧藏,是建国后才入藏北京图书馆。其中宋版叶颇多,如首叶即南宋中期补版,末叶为南宋初原版,皆有刻工名及避讳字佐证。原版叶宋讳避讳严格,补板时则未如此严格。
台北故宫博物院古籍文献馆藏三种宋刻元修残本,分别存二十五卷、八卷、五卷。二十五卷本被尾崎康定为南宋中期、元前期递修。所存宋版叶颇多。其重要价值在于保留宋人校勘疏语,目前《陈书》所存疏语共七处九条,部分仅见于此本。
又有两种全本,其一为静嘉堂藏宋刻宋元(大德年间)修本,尾崎康定为南宋中期、元前期、元中后期递修。其二为国图藏宋刻宋元明初递修本,亦是再造善本底本。不过此本长期被认为是递修至元代,再造善本亦如此说明,恐不然。其一,此本各卷首尾多钤“礼部官书”朱文大长方印,明初南监修版后之新印本即钤此印藏于礼部。其二,明初补版于版心无补刊字样,民国以前学者一度普遍将明初递修都视同宋元递修。同样有“礼部官书”印的《南齐书》(再造善本影印)最初也曾被认为是宋元递修,后来始被普遍接受为是递修至明初的版本。比较《南齐书》该印本与《陈书》此本,字体、版心、刻工上都有相符处,而与其他《陈书》传本的宋元版叶有明显差异,因而应认为是明初递修本。与静嘉堂本相比,此本后补版叶中字体变动很大,俗体异体字甚至无可理喻的讹字也更多,避讳不严格。此本还有许多版叶行款字数与宋元版有明显差异。三朝本明显沿袭了此本的特征,但也对此本补板中一些明显的讹字作了改正。
唐星的报告考察唐初修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旧唐书》帝纪、《唐会要》、参加修撰者的本传等都记载“五代史”成于贞观十年,应当可信。《史通》作“十八年”,余嘉锡指出大概原本是指从贞观三年到十年共八年,后脱误。有矛盾的是《旧唐书·姚思廉传》,其中记《梁书》《陈书》的撰写时间在贞观九年之事以前。
虽然不排除《姚思廉传》打乱时间顺序叙述的可能,但该传还有另一相关问题值得注意,即所载《梁书》《陈书》卷数也较今传本少五卷。又《旧唐志》记姚氏《梁书》亦少今本五卷。又,《梁书》《陈书》中共有三处魏征结衔为“侍中、郑国公”,而魏征受封郑国公已经在贞观十年以后。由此推测,贞观十年各史奏上后,大概又经过魏征改订。而如果按照《旧唐书·姚思廉传》的史事记载顺序,姚思廉奏上《梁书》《陈书》的时间还要早于其他对五代史纪传奏上时间的笼统记载。
报告还根据新出土资料,讨论了唐初“修史学士”的具体情形。

周文俊
周文俊的报告通过对《宋书·孝懿萧皇后传》一处记载的校读案例,探讨如何理解,及如何处理史籍整理中的异文。
《萧后传》记载刘裕即位时有司上奏要求追尊其母萧氏,其中一句无法读通。点校本《宋书》据《册府》校改。然而梳理《册府》之文本来源,发现它是拼合《宋书·武帝纪》与《宋书·萧后传》相关文字而成,《武帝纪》与《萧后传》对萧氏入宋以前的位号记载,本来存在矛盾,前者称“(王)太后”,后者称“(王)太妃”,《册府》改后者从前者,存在较大误失,不宜作为《宋书》校勘依据。报告重新复原《萧后传》无法读通的文本,认为大约分属奏疏引文与史臣解释两个层次,中间有较长脱文。此类先引文书原文,再加以解释的叙述方式,在当时史书中比较常见。
通过梳理相关史事,报告认为《萧后传》和《武帝纪》看似矛盾的记载,其实都符合历史实情。当时官爵名号的任命包括两个步骤,一是通过诏书,下达任命,二是举行仪式,实际拜受。萧氏在晋末经过第一步骤获授予“(王)太后”位号,成为《武帝纪》记载的依据;但直到刘裕即位,仍未实行第二步骤,故萧氏未算正式获得“(王)太后”身份,《萧后传》所录有司奏文因此依然称萧氏为“(王)太妃”。
《宋书·萧后传》与《册府》的相关记载都经历了复杂的文本过程:前者在脱去一段文字后,原本分属两个层次的文本粘连在一起;后者则由于编者对制度不了解,强行统合了两个不同史源的文本。史籍文本流传过程中的此类现象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作为古籍整理基本方法的“四校法”的应用原则。目前古籍整理规范中,列举校勘依据时一般按版本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分层依次罗列。但若从动态的文本过程来考虑,四校法所对应的四类书证范畴未必“名实相副”,校勘证据层次如何,要立足于每一处异文自身的历史过程。
对话:正史编纂的技术性处理
叶炜(北京大学历史系):我想请教仇老师,判断技术性删削,有没有什么标准?
仇鹿鸣:其实没有特别的标准。过去史学史研究比较强调中国史学褒贬叙事的传统,暗示史书叙述中反映编者强烈的主观意图,这种情况当然存在。但历史编纂也是一种流水线作业,有层层相因的一面,只是需要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材料来确认如何具体操作,我这篇文章就是一次尝试。
实录的立传规模非常大,在这之中怎样区分谁会进入史传?而且作史传的人一般来说距离他这些历史发生的时代已经有一定距离,除了一些极特殊的情况——比如武士彟到显庆时地位变得很高,《武士彟传》经过了后来大量的增益和改动——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会有太多主动处理。那么就需要划出一个标准,把整个时段的材料都放在这个标准下处理。但执行标准的时候又会有出入,类似地位的人物,有的删了,有的保留了,并不完全划一,所以古人读史札记中,经常会批评某人该立传而未立,反映的也是这种出入,这个过程大概是无意识的。这就是我说的技术性的或者叫非主观性的处理。
唐雯:我们在做文献工作的过程中对古人的技术性处理有很强烈的感受,特别是两篇同源的东西对比,比如是本纪是根据实录删削下来的,通过现在保存的实录文字,可以看到其中一些细节的或不太重要的部分被删削,形成本纪。
古人的删削很有本事,比如我们最近也在做《十七史详节》,它完全是利用《新五代史》,把他觉得枝节的部分删掉。并没有改一个字,细节内容都删掉了,而上下文还是搭配得非常通贯。
也很难说出明确的标准,但能感到哪些文字是经过了删削处理的,有时会有一些标志。我现在在关心《旧唐书》的史源问题,就发现《册府》的很多内容,看起来像是从《旧唐书》里截取的,但其实有些许差异,可能并不是《旧唐书》本身,而是有史源关系的另一种文献。
我非常赞同仇老师讲的,很多处理并不是有意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可能百分之九十都是技术性的处理,剩下少部分是有作者深意在其中,可以去讨论其他层面的比如历史书写问题。但先要把技术性的层面区分清楚,再来讨论剩下的部分里有哪些主观性的东西。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