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
◆小山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了“儒林传”,后代正史几乎都会为儒林立传(偶有称“儒学传”者)。按照《史记正义》引姚承的说法,“儒林”不仅仅是“儒雅之林”,更应是一群“综理古文,宣明旧艺”,最后“以成王化”的人。在《史记》里,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就算一位。以今天的概念来衡量,一般的文人学士大概是入不了“儒林传”的,得是有些分量的思想者才有这个资格。明确了这个标准,再来看《儒林外史》,我们就会发现,书名本身似乎就暗含了对于“儒林”的嘲笑:“儒林”当然是要堂堂正正居于“正史”名垂千古的,怎么却和“外史”搭上了关系?至于作者,他以写稗官野史自居,以洋洋洒洒一部“外史”与“正史”颉颃,也不像是在谦虚,倒更像是对“正史”的不屑,甚至是故意唱反调的。而从内容与结构来看,这部“外史”确实体现了对于“正史”的突破。
与正史中的“儒雅之林”相反,一部《儒林外史》,几乎颠覆了文人学士的群体形象。中学课本里必选的“范进中举”,让学生们看到了“封建科举制度下士人的丑恶灵魂”,殊不知《儒林外史》里如范进般老实的已属上品了。周进、范进之流尚知进身路由举业文章,屡试不中也只是在家苦熬,闹几回疯癫最多也就是个斯文扫地,那心术不正如牛浦郎、匡超人辈,早就把坑蒙拐骗都用上了。至若严监生之吝啬,鲁编修之迂腐,权勿用之伪善……众“儒”粉墨登场,好戏连台,“真乃一时盛会”也!
《儒林外史》的结构在古典小说中也很独特。太史公草创纪传体,记一人之终始,后世因之,遂成正史不易之体。章实斋云:“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虽然在《史记》、《汉书》的列传,尤其是类传中,或因史料缺失,或为突出人物的共同点,有些传记只记载了传主一生中的几个典型事例,但多数传记是有始有终的。有始有终这一特点,在后世正史的列传中也得到了发扬。中国有尚史的传统,古典小说戏曲中人物登场往往自报家门,结尾时主要角色的结局也都会有所交代。《儒林外史》虽为诸儒立传,却突破了史传文学有始有终的模式,不以因果关系连缀事件,每个人物上场只领数回风骚,之后便牵出另外的人物,自己消失,并不交代结局。黄富民为《儒林外史》作序,云此书“人各为传,而前后联络,每以不结结之”,诚哉斯言!仔细想来,世间有多少事是真能说出个前因后果来的?就像滚动屏上一条条的新闻新的覆盖旧的,不了了之也许才更是事态真情。众多评点者(黄富民亦在其中)知晓这一点,而每每在某人最后出场时注曰“了却某某”,替作者做个了断,大约仍秉持了史传文学的思维模式。
《儒林外史》受史传文学影响至深,不仅表现在它的反其道而行之,也表现在它的突而未破之处,这其中最明显的当数善善恶恶的史传传统。《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史书具有陟黜褒贬的功能,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观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刘知几《史通·人物》),则是史官的失职。《儒林外史》表面虽以“外史”自居,极尽讽刺之能事,但作者毕竟是浸淫于传统文化的士人。诸评点者众口一词,认为作者虽以史汉之才写小说,但劝世之心良苦,并奉劝读者万勿以一般稗官野史视之,实乃事出有因。
《儒林外史》是一部讽刺小说,作者笔下假名士、假高人无不原形毕露,此可谓“破”;假名士、假高人中,三个真君子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遗世而独立,此又可谓“立”。有破也有立,《儒林外史》的讽刺并非后现代的解构,吴敬梓再愤世嫉俗,与“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也不是同道。虞博士浑雅,庄征君恬适,杜少卿豪爽,又经迟衡山牵头,一时之贤士汇聚南京,重修礼乐之事。祭泰伯祠回,详细描写了献祭始终,繁复又堂皇,是全书之高潮。卧闲草堂本评曰:“此篇古趣堂皇,竟如出自叔孙通、曹褒之手。”叔孙通为汉高祖平制礼仪,曹褒为汉肃宗改定礼制。作者愤世嫉俗至深,仍将恢复礼乐的理想寄诸笔端,善善恶恶之旨于是乎尽显。金和《跋》云,作者著书“以当木铎之振,非苟焉愤时疾俗而已”,此言得之。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以“幽榜”为全书收结,为九十余儒排列座次。虞、庄、杜三人自然高居榜首,曲终奏雅。其实第五十五回另起炉灶,轻描淡写了四个大隐隐于市的高人,以琴棋书画作结,余音袅袅,绕梁不绝,与楔子暗合。很多学者认为第五十六回并非吴敬梓所撰,第五十五回才是真正结尾。在此我们并不想讨论最后一回的真伪,但我们想问结尾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形态出现?
也许第五十六回作者坚持认为,文章有始有终才是正道,贤人君子如果埋没世间,有违著书惩恶扬善之功用。不论该回作者的初衷为何,这个结尾却符合史传文学的传统。齐省堂本评曰:“将全部所有人物总列一遍,评其贤否,着其去取,以示善善恶恶之旨。”中规中矩。
但高悬的幽榜是否果如作者所愿,为已逝者增添了哀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全书讽刺了一群假名士、假高人,可到底也竖了几个榜样。通过祭泰伯祠回,我们知道了吴敬梓的理想与寄托。转眼间第五十六回却将“真名士”也全拉上了榜———死了也得上榜,足见到头来只有举业文章才是儒林正宗!这一回没有如作者所愿“曲终奏雅”,相反,它本身成了个莫大的讽刺,把前面的文章,甚至把吴敬梓著这么一部书的行为本身,都解构掉了。卧闲草堂本评语赞叹这一回有《太史公自序》的味道,天目山樵评语却拍了一块砖:“瞎闹!”后现代文学的笔法之一,说通俗点就是“瞎闹”,通过“瞎闹”把意义解构掉。天目山樵在拍这块砖时,断不会想到自己竟暗合了“解构”的宗旨:第五十六回这个结尾,实在有点通过“瞎闹”而“解构”全书的意味,若是有意为之,全书的讽刺性无疑更力透纸背。只恐此结果断非此回作者本意。即便吴敬梓的本意也不应如此,因为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他骨子里具有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理想。在理想受阻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不出解构主义,只培养得出外儒内道的君子人格,正如楔子中的王冕,第五十五回里大隐隐于市的高人。
《儒林外史》以讽刺见长,开篇即点破“功名富贵无凭据”,最后却以曲终奏雅收官。最后一回真也好伪也好,评点者们褒也好贬也好,《儒林外史》及其评语,终究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太深。说到底,全书有再多的标新立异,也还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它的确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新任务有待新文学来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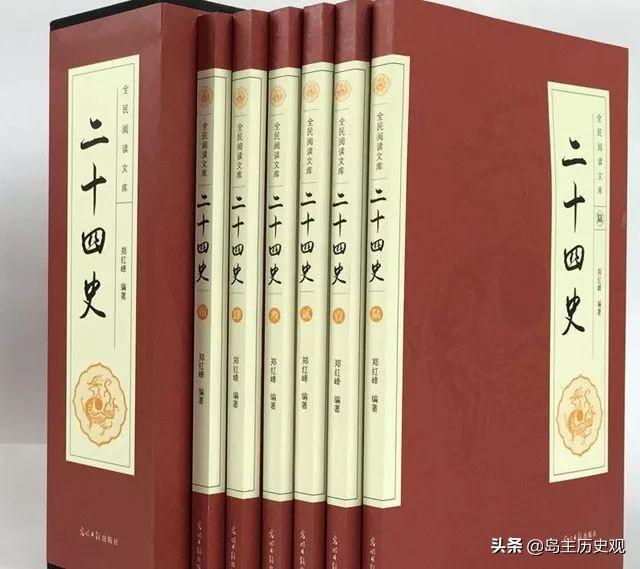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