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话本小说情节的主要模式就是戏剧性,这与其脱胎并继承“说话”艺术有很大关系。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模式有这丰富的表现方式,其中冲突、转折、表演性和巧合是最为常见的。话本小说情节之所以表现为戏剧性,其原因与其内置的“拟书场”叙述格局密不可分,在这种叙述格局中,虚拟“说话人”和虚拟“看官”之间的交流是叙述合理性的依据,根本上说,话本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即为这种交流性服务,受到这种交流性的潜在支配。
关键词:话本小说,情节,戏剧性,交流性。
The Dramatic Plot andCommunicative Model of Huaben Fictions
Abstract: Dramatic Plot is themain plot of Huaben fictions, this is because it is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oral-art" of Song dynasty or before. The dramatic plot model hasrich expression, including conflict, turning, performing and coincidence. Whydo Huaben fictions have dramatic plot? Thereason is its built-in "performance environment" in its narrationpattern. In this kind of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virtual "speaker" and "audiences" make the narrationreasonable. Ultimately, the Dramatic Plot serves the communication and iscontrolled by it.
Keywords: Huaben Fictions, dramaticplot , Communication.

话本小说的情节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模式呢?阅读话本小说会有一种强烈感受,那就是轻松的阅读心理状态,这种状态又来自哪里呢?如果这种心理状态可以从话本小说大众化的母题和与读者心理相和谐的默契的情节节奏获得某种解释的话,那么,笔者认为,读者的这种愉悦的阅读状态更来自一种宏观性的戏剧性情节模式的设置,分析这种情节模式,我们会发现它具有明确的交流性,或者,换句话说,这种情节模式是在“拟书场叙事格局”之虚拟的说话人和看官之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如果读者不进行刻意的或者研究性的区分,这种虚拟的看官与现实的读者往往会呈现重合状态,这就意味着,话本小说的戏剧性情节模式从根本上讲,是“作者——文本——读者”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众多读者相同或类似的的选择却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要求与压力,这时整体意义上的‘读者’便参与了小说发展方向的决定”[1]。话本小说戏剧性情节有多种表现形态,比如冲突、转折、表演性、巧合等等,这些表现形态从根本上讲是围绕虚拟的“说——听”交流展开,也就是说,话本小说戏剧性情节模式最根本的艺术特性就是这种交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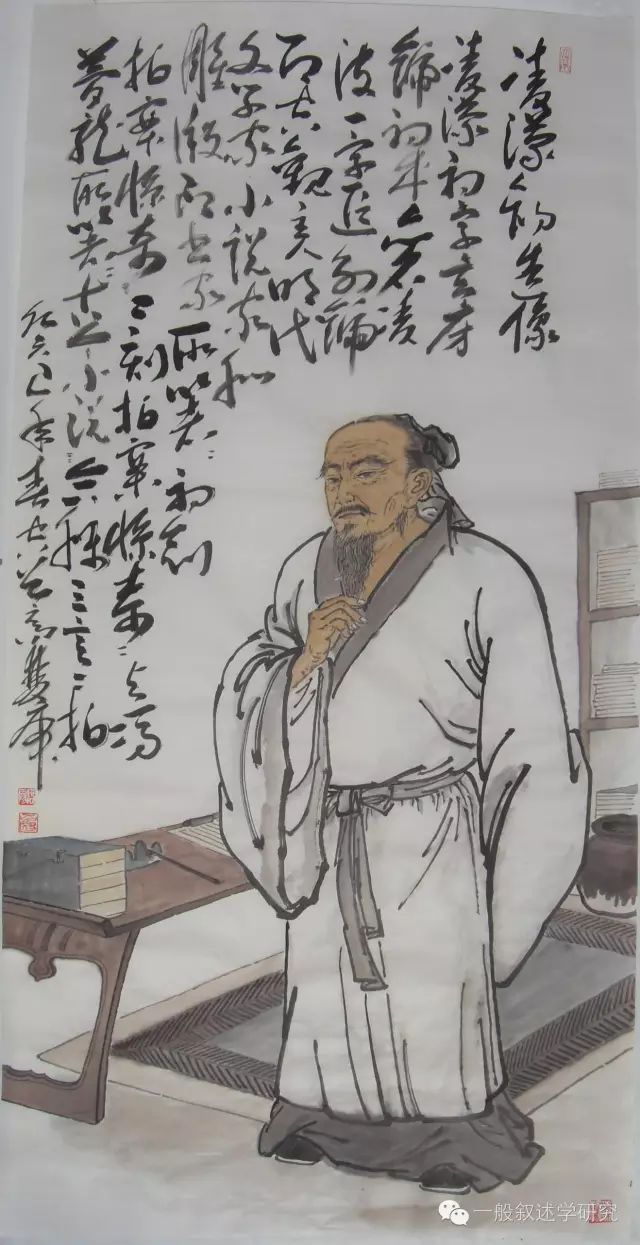
一话本小说戏剧性情节模式表现之一:冲突
冲突是戏剧艺术最为核心的艺术特征之一,可以说,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作为戏剧的艺术方法而作用于戏剧艺术文本构成方式;一是作为一种吸引观众、引起观众兴趣、共鸣的艺术手段,目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与观众达成良好的交流关系。在小说中,尤其是在通俗小说中,冲突也常常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来达到吸引读者兴趣的目的。话本小说作为来源于“说话”表演艺术的通俗小说,其情节的冲突性一方面来自“说话”艺术固有的惯性,一方面来自其作为通俗小说自身的需要,因为这不但是一种作者需要,而且也是一种出版者(坊刻者)追求经济利益的需要。冲突可以存在于人物之间,也可以来自人物内心,前者表现为人物对话或者行动,后者表现为人物内心活动带来的外部行动。因此,冲突基本上体现为人物的一种外在的行为方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这篇话本小说的经典之作成功的运用了两处人物冲突,而这些冲突又是人物内心冲突的一部分,从而构成了该小说情节戏剧性的核心。其一是杜十娘与鸨母的正面冲突,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与公子李甲“真情相好”,但当鸨母见李甲“手头愈短,心头愈热”之时,就想赶李甲出门,杜十娘便与之发生了正面冲突,致使鸨母一怒之下答应只要李甲拿出三百两银子就让杜十娘从良。杜十娘与鸨母的这一冲突其实有着很深的心理根源,首先是杜十娘的从良之志和对鸨母“贪财无义”的厌恶;其次是与公子李甲之间的感情,并认为此人可以托付终身。这两种心理根源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与鸨母的冲突,因为二者的结合之下,鸨母就成为实现自己志向的绊脚石。其二是杜十娘与李甲和孙富的冲突。杜十娘与李甲满怀对未来的憧憬买舟归乡,不料李甲受孙富挑拨,导致李甲摄于其父和金钱的压力而以千金将杜十娘卖于孙富,而此时满怀对新生活希望的杜十娘得知此情,在心里建立起来的希望之厦顷刻间崩塌,可以说此时杜十娘进退惟谷,实际上已经到了绝境,心中的美好希望与眼前的残酷现实构成极大的心理冲突与心理落差,但此时的杜十娘却表现出异常的平静,请看她得知李甲将自己卖与孙富后对李甲说的话:
为郎君画此计者,此人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资既得恢复,而妾归他姓,又不致为行李之累,发乎情,止乎礼,诚两便之策也。那千金在那里?
不但如此,杜十娘还在自己被出卖当天的四更天,早起“挑灯梳洗”,并对李甲说:“今日之妆,乃迎新送旧,非比寻常。”并且还“微窥公子,欣欣似有喜色,乃催公子快去回话,及早兑足银子。”一个心底灰冷,而又希望李甲能够回心转意的矛盾心态呼之欲出。杜十娘的这种内心冲突非常的微妙也非常深刻,波诡云谲的内心全以平静出之。尤其是当李甲与孙富交易完毕之后,彻底绝望的杜十娘积压内心的怨恨猛然迸发,她与李甲、孙富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请看杜十娘对孙富和李甲说的话:
对孙富:
十娘推开公子在一边,向孙富骂道:“我与李郎备尝艰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为谗说,一旦破人姻缘,断人恩爱,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当诉之神明,尚妄想枕席之欢乎!”
对李甲:
妾风尘数年,私有所积,本为终身之计。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前出都之际,假托众姊妹相赠,箱中韫藏百宝,不下万金。将润色郎君之装,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生死无憾。谁知郎君相信不深,惑于浮议,中道见弃,负妾一片真心。今日当众目之前,开箱出视,使郎君知区区千金,未为难事。妾椟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命之不辰,风尘困瘁,甫得脱离,又遭弃捐。今众人各有耳目,共作证明,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耳!
由内心冲突表现于行动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其之所以受到历代读者的推崇,不单单因为其思想价值,而且还因为其极高的艺术性。“外部动作或者内心活动,其本身并非‘戏剧性’的。它们能否成为戏剧性的,必须看它们能否自然地激动观众的感情,或者通过作者的处理而达到这样的效果”[2]。可以说,该篇无论是作者创作还是激动读者方面均表现了人物由内心冲突表现为外在的冲突与行为的戏剧性。“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冲突需要有力的前提和条件,性格内部的冲突(内心冲突)同样需要这样的前提和条件。构成性格内部冲突的前提,是性格内部存在着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单一的意志和品格很难构成真正的内心冲突”[3]。《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的皇甫殿直就是一例,皇甫殿直因受一僧人欺骗在官府主持下将妻子修掉,此时的皇甫殿直一心想维护的是自己的尊严和封建贞节观念,但如果是这种“单一意志”,那么就不会构成故事的进展,富有戏剧性的是,休掉妻子一年之后的正月初一,皇甫殿直“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个,双双地上本州岛岛岛大相国寺里烧香。我今年独自一个,不知我浑家那里去了?’簌地两行泪下,闷闷不已。”此时,所谓的“尊严”、所谓的“贞节”都难抵自己凄凉的生活,贞节观念与凄凉生活二者在其休妻时前者占上风,而在此时后者又占了上风,毕竟再冠冕堂皇的虚无的观念也无法弥补“自从修了浑家,在家中无好况”的凄凉。因此,皇甫殿直后来的行动无不在这种内心冲突的背景下展开。
话本小说冲突性的情节是非常常见的,比如李渔《连城璧》子集“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中,谭楚玉与刘藐姑的爱情就是在与刘藐姑母亲的冲突中发展的,而作为冲突的高潮是在演出《荆钗记》中,把男女主角殉情跳水演成了真实版的殉情跳水。李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采用戏中戏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戏里戏外融为一体,将戏里戏外的冲突进行了叠加,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双重的冲突与双重的高潮。《五色石》第一卷“假相如巧骗老王孙活云华终配真才子”中,胸无点墨的木长生与有真才实学的黄生之间的冲突是在故事的运动中逐渐发展并达到白热化程度的。话本小说中的公案小说大多是在故事的动态发展中逐渐使冲突达到高潮,比如《警世通言》卷13“三现身包龙图断案”中包龙图的机智与罪犯小孙押司的狡诈之间形成极具戏剧意味的冲突关系。等等。
冲突,不但是为了取得良好的接受效果和与读者兴味构成完美契合的交流关系,而且这种冲突的交流性还是一种内置的、已经艺术化、文本化的艺术手段。约翰·盖利肖在论述如何使小说具有戏剧性时指出,人物之间或者人物内心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交流,“因为没有冲突,就不会有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的相互交流,也就不会有不确定性。一旦在交流中加进了冲突,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加进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相互间的交流;而一旦在交流中加进了这两种因素,你也就获得了冲突。这样,戏剧性带来了故事,故事又增加了戏剧性”[4]。这里所谓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即是指冲突双方。由此我们发现,话本小说的戏剧性冲突其实含有两种交流性品质,其一是读者交流品质;其二是冲突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冲突双方的交流,有了这种交流才使小说有了戏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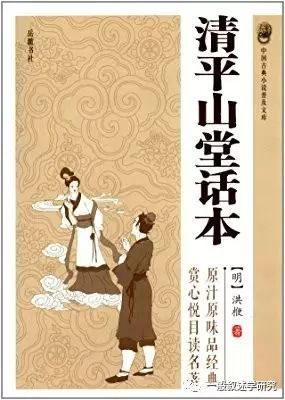
二话本小说戏剧性情节模式表现之二:转折
话本小说常常用转折性的情节使故事发生戏剧性逆转,转折性不但作为一种催化结构而且作为一种情节模式在话本小说中频频出现,话本小说情节的转折性不但因为改变并左右了线性故事的运行方向而具有结构性意义[5],而且情节的转折性对于故事本身来说也具有戏剧性意义。故事的转折性来自于一些具有使故事的运动方向、性质、速度等等发生改变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具有直接作用于人物心灵或者故事核心的品质,只有这种品质才可能使故事发生戏剧性转折。《初刻拍案惊奇》卷19“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中,谢小娥作为其家中唯一幸存的人,复仇对她来说是唯一生存的理由,但一个弱女子如何找到强盗下落,又如何实施复仇呢?于是,谢小娥梦见其父授其含有杀人者姓名的谜语就成为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它使故事的运行方向和人物的行为发生了质的变化,谢小娥的梦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也是一个极具戏剧意味的事件。李渔最善于利用故事的转折性来使小说具有戏剧性,李渔认为小说是“无声的戏剧”,因此李渔曾经把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无声戏》,后来传世的《连城璧》就是在其小说集《无声戏》被清官府查禁后改名而成。《连城璧》巳集“遭风遇盗致奇赢让本还财成巨富”中,相貌酷似的秦世良与秦世芳,前者命中富贵后者命中贫穷,二人同时向财主杨百万借钱,杨百万识人面相,认为秦世良必将富贵就借他五百两银子,而秦世芳面相贫穷却分文没有借得。
秦世芳拿着杨百万借的五百两银子做生意却遇盗,被抢个精光,不得已再次向杨百万借钱五百两,这次他多了个心眼,将三百两做生意,将二百两藏起以防不测,结果三百两却被贼人偷去。于是只好将藏起的二百两拿出继续去做贩米生意。这次他在客店遇到了秦世芳,二人结为兄弟,但好景不长,当得知米到取银子买米的时候,秦世芳发现自己的二百两银子不见了,于是就怀疑秦世良拿了他的银子,而秦世良的银子又恰恰二百两,于是被不明不白地被秦世芳拿去。秦世良没有了银子,只好回家,杨百万再借,他已心灰意冷,不再出去做生意,而“处馆过日”。秦世芳得到了银子,生意很兴隆,并赚了大量金钱回到家中,其妻甚为吃惊,怀疑丈夫何以无本而得万利。故事在此有一个戏剧性转折,原来秦世芳的银子并没有被偷,而是他出门忘到了家中,于是一切真相大白,秦世良并没有偷秦世芳的银子。这一转折性情节改变了故事的发展方向,也改变了人物的命运与行为,秦世芳于是连本带利将所有金钱还与秦世良,而秦世良将一半财物赠予秦世芳,秦世芳也因自己的义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其实我们发现,故事中这一转折性情节极富心理、道德内涵,其衡量的不仅仅是金钱,而且是人在金钱面前所采取的行动。因此,故事的转折性情节往往给人以道德启示。类似具有转折性情节的小说在李渔的小说作品中很常见,如《十二楼》、《连城璧》中很多小说都是因为情节的转折性使故事富有戏剧意味。
话本小说的转折性情节带来的戏剧性效果之一是使故事的发展方向发生改变,或者使人物的行为发生改变;效果之二是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使读者阅读成为一种娱乐、一种享受,话本小说追求“娱目醒心”,转折性情节便为这种追求提供了一种方法。因此,从根本上讲,话本小说情节的转折性与其创作的读者交流目的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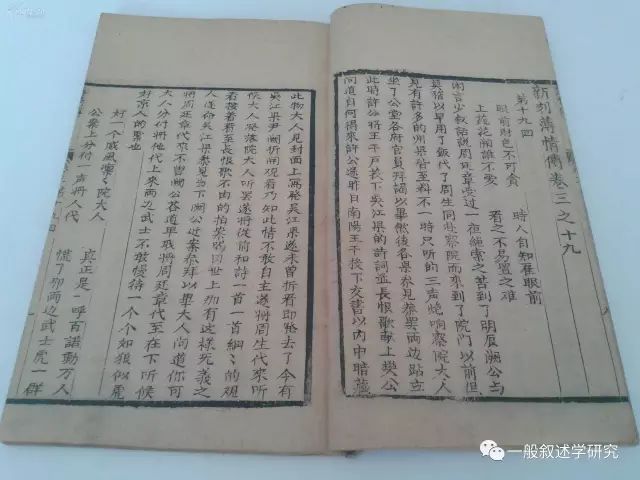
三 话本小说戏剧性情节模式表现之三:表演性
话本小说的表演性来自于情节设计的表演意识,表演不但表现为一种场面化情景,而且还表现为一种人物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是几个人物合作完成,也可以是一个人物的单独行为。但应当指出,表演性是一种叙述技巧,一种叙述行为,而非人物行为自身的特质。也就是说,话本小说中人物的表演性行为归根结底是一种叙述技巧,而不是人物必须那样。比如话本小说之公案小说往往按照顺序先叙述案发经过,然后再进入审案过程,这样官员的审案就在一种读者明了的状态下进行,于是,审案变成了案件参与者的各色人物表演的过程,他们谁是谁非、谁冤谁屈,官员是否清正,案件审理是否合理、合法等等,这些都在读者已经明了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与其是在审案,不如说是在表演。更让人注意的是话本小说中塑造的丫鬟形象,比如李渔《十二楼》之“拂云楼”中的丫鬟能红即为代表,能红形象为古代才子佳人等爱情小说和戏曲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机智、又工于心计的丫鬟角色,随即丫鬟成为一个极富灵动的叙事因子,同时,丫鬟的机灵而具有动感的行为为小说的增添了表演性特质。正因为如此,“能红现象”为有的学者所推崇[6]。那么,能红究竟如何“表演”呢?“拂云楼”首先叙述青年秀士裴七郎先与韦氏有婚约,后裴七郎之父毁约与妆奁丰厚的封家结亲,做亲之后,裴七郎见封小姐相貌丑陋,甚是反感。
在端阳佳节,封氏到钱塘江游玩遇到大风被潮头淋湿患风寒又被人耻笑其丑,郁郁而死。而恰恰韦小姐与丫鬟能红也去游玩,二人美貌使裴七郎神魂颠倒。当封氏已死,裴七郎决定续弦,韦小姐与能红自然成为其目标,经多方打听方知道韦小姐乃原来婚约又被裴父悔婚的韦氏。于是重新订立婚约,托媒人俞阿妈说和遭韦家拒绝,无计可施。裴七郎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竟然在媒人俞阿妈面前下跪说娶得丫鬟能红也情愿。不料这一跪被在拂云楼上的丫鬟能红看见,当俞阿妈再去韦家提亲,被能红一下猜中,即这次俞阿妈是为她能红而来。身份低下的丫鬟能红利用这次机会想改变自己的地位,于是设计了一出连环计,其一让裴七郎贿赂算命先生张铁嘴,利用韦小姐父母信奉命相八字来实施其计,并向韦家说明韦小姐八字带半点夫星,嫁人要嫁一个头妻已死要续弦的,而且必须有一姬妾帮助方能“白发相守”。这样,事情一步步朝能红所要的方向发展;其二,说服韦家让自己替韦小姐相亲,能红的实际意图是想从裴七郎出得到保证,即不但让她做二夫人而且要得到裴七郎的“投认状”。其三,能红替韦小姐相亲,与裴七郎“约法三章”,一是巩固自己二夫人地位,即不让再让人喊其能红名字,二是不得“偷香窃玉”,三是不得再娶小三,这样能红为自己将来在裴家的地位打基础;其四,为使自己能名正言顺成为二夫人,在裴七郎与韦小姐完婚之后,设计让裴七郎佯装有噩梦并请解梦先生解梦,说韦小姐只有半夫之分,恶鬼要把韦小姐拖走,于是韦小姐在先前有张铁嘴算命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半夫命深信不疑,并欣然答应裴七郎娶二夫人,于是能红就成为不二人选,而且是韦小姐主动提出的。由以上四处计谋均掌控于丫鬟能红之手,其行为可谓八面玲珑,表面上为别人,实际上处处为自己,能红的表演可谓精彩之至。
中国古典文学塑造丫鬟形象李渔并非第一人,《西厢记》中的红娘即是典型,而在话本小说中,如《二刻拍案惊奇》卷9“莽儿郎惊散新莺燕梅香认合玉蟾蜍”中的丫鬟龙香调皮乖巧,行为极为灵动可人,其光彩绝不亚于能红。正因为这些丫鬟代表了女性的聪明才智,甚至勇敢正义,在古典小说和古典戏剧中,丫鬟角色比其它人物更能激起读者或观众的兴趣。丫鬟的行为在小说中具有丰富的表演特质。李渔将小说称作“无声戏”,并将一些戏剧因素引入小说之中,因此,表演性在李渔的作品中极为常见,《连城璧》子集中的“戏中戏”、午集中的喧闹的治妒妇情节,《十二楼》之“夏宜楼”中的望远镜中之风景,如此等等,可以说,表演性已经内化为故事情节的核心部分,读李渔小说,读者绝不会感到累,恰如欣赏无声之戏给人愉悦。
话本小说的表演性不但是一种艺术技巧、一种叙事策略,而且已经作为故事人物的行为方式,比如《喻世明言》卷10“滕大尹鬼断家私”中滕大尹的装神弄鬼;再如卷27“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许公夫妇在对莫郎与金玉奴完婚之前对他们二人的试探,莫郎一心攀附富贵欣然答应,而金玉奴却以遵守妇节不愿再嫁,而当许夫人说明新郎就是其原来的丈夫莫郎,并设计教训一下莫郎,金玉奴才答应,整个过程人物有着自觉的表演性。因此,表演性是话本小说常见的情节方式,其直接的效果就是故事的戏剧性和读者的娱乐性,与读者建立良好、和谐、轻松愉快的交流关系不但关系到作品的命运,也关系到作者的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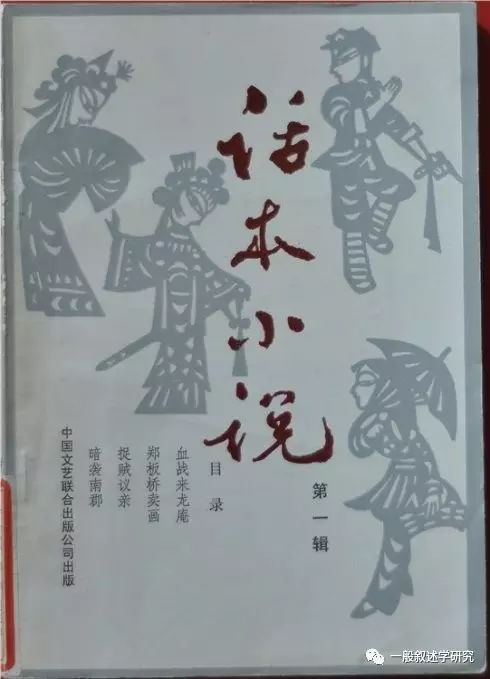
四话本小说戏剧性情节模式表现之四:巧合
巧合是话本小说常用的艺术方法,故事常因巧合而带来戏剧性。所谓“无巧不成书”,这里的“书”应该是说书曲艺,话本小说作为一种受说话艺术影响的小说类型,也把这种“巧合”叙事方法运用于故事之中。巧合就是利用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来组合故事情节的一种技巧。巧合的关键是一个“巧”字,“合”是基本要求,要“合”得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人意料之外。“合”得新颖别致,方见其“巧”。《醒世恒言》卷8“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孙寡妇怕女婿病重害了女儿,于是让儿子男扮女装顶替女儿去成亲,而男方刘家恰巧让自己的女儿代替哥哥陪刚过门的“嫂子”,阴差阳错成就了另一对新人;《醒世恒言》卷33“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陈二姐的丈夫刘贵穷困潦倒,得大娘子丈人资助十五贯钱做生意,回家后对小妾陈二姐谎称是卖她的钱,陈二姐信以为真,决定连夜回娘家,出门后没有上锁导致刘贵被静山大王杀人越货。而陈二姐在回娘家路上恰遇卖丝商贩崔宁,而崔又恰恰卖丝得十五贯钱,于是二人被告为通奸害命,崔宁被问死罪,事情竟有如此巧合。《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的“倒运汉”文若虚生意场频频倒运,而偏偏用一两银子买的名曰“洞庭红”的橘子在海外大发其财,并在回来的路上船被大风飘到一无人空岛,文若虚又巧遇鼍龙壳,而这个鼍龙壳又恰恰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于是文若虚时来运转,一下子成了富翁。在话本小说中,如此戏剧性巧合比比皆是,有些小说的题目直接体现了小说情节的“巧”,在“三言二拍”中仅题目有巧字的就有11篇之多,清人梅庵道人曾编辑一部话本小说集《四巧说》,更是以“巧”作为其选编目的,该书有四篇小说作品,其中三篇选自《八洞天》卷一、二、七,一篇选自《照世杯》卷一,四篇作品均体现了一个“巧”字,不妨把这四篇作品的题目列下面:
“补南陔”《收父骨千里遇生父,裹儿尸七年逢活儿》
“反芦花”《幻作合前妻为后妻,巧相逢继母是亲母》
“赛他山”《假传书弄假反成真,暗赎身因暗竟说明》
“劝匪躬”《忠格天幻出男人乳,义感神梦赐内官须》
从这些题目可以看出这些故事并非寻常,而是每一个故事都透露出一些奇异乖巧之处,巧合是这些故事共同的特征。而这些巧合形成一个个戏剧性的情节。有很多话本小说并非是一处巧合,而是形成一种巧合链条,正是这些巧合链条构成了话本小说戏剧性的情节模式。
由以上论述我们发现,话本小说戏剧性情节模式的表现并不是一种,而是有多种表现方式,正是这些表现的综合,形成了话本小说情节的戏剧性。也就是说,话本小说的戏剧性情节模式是上述各种表现的交叉运用形成的,而且这种交叉体现了一种高度的程序化、重复性。这种高度程序化的戏剧性情节模式具有明确的交流性,这里,“交流性”表现于两个层次,其一是存在于文本内部的交流性,即作为“拟书场叙事格局”小说特性,内置的“说——听”交流关系使小说叙事时刻带有书场演出的特性,而这种特性要求叙事的趣味性、通俗性、娱乐性,而这些性质本质上蕴含了不把故事“当真”的意思,于是,“说”、“听”双方就会在这种“约定”下进行融洽的交流;其二是存在于现实的“写——读”交流,话本小说作为通俗小说,无论在精神价值还是艺术追求都不以前卫、启蒙为核心,而是以娱乐再加一点劝惩作为创作的目的,读者的趣味与小说的销路永远是通俗小说追求的目标,因此,戏剧性带来的趣味性和娱乐性便成为话本小说的重要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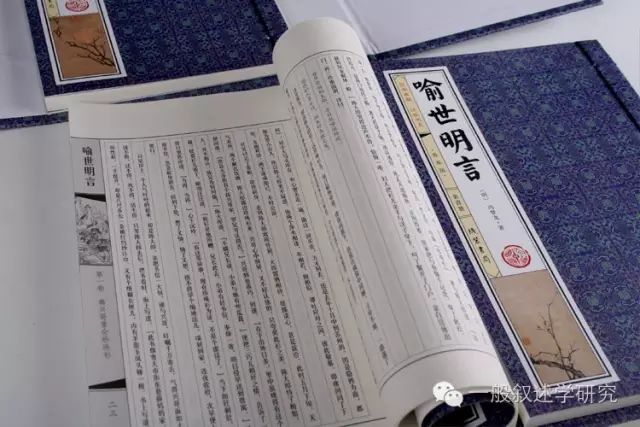
注释
[1]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21页.
[2]贝克.戏剧技巧.[M],余上沅节译,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研究室编印,1961年,第5页.转引自谭霈生.论戏剧性.[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57页.
[3]谭霈生.论戏剧性.北[M]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22页.
[4] [美]约翰·盖利肖.小说写作技巧二十讲》.梁淼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38页.
[5]王委艳.论话本小说的奇书文体、转折性结构和劝谕图式.[J].社会科学论坛.2011.2期.
[6]见王意如.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化透视.[M].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66-77页.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