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
作者:王舒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
学人小传

晁福林,1943年出生于河南杞县。先秦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1965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留校任教。著有《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夏商西周史丛考》《上博简〈诗论〉研究》等。
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先秦时期是古代中国的基石,孕育着中华文明的特质,培植出中华民族的基因。同时,又因其年湮世远,相关传说长久流传,富有浪漫神秘色彩,研究者往往需要旁收博采,廓清重重迷雾,才能求得先秦史的真相。尽管如此,古往今来,仍有无数学人为之倾倒。到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先秦史研究更加迸发出强大的学术活力。
进入80年代,时代变革,学术亦发生重大嬗递。接续和再创中国先秦史研究的辉煌成为重大学术命题。1982年,晁福林硕士毕业,登上北京师范大学讲台,至今已在先秦史领域耕耘了整整40年。他的研究横跨先秦社会形态、国家结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民俗文化、文献形成等方方面面,在继承先辈学术业绩的基础上,将先秦史研究推向新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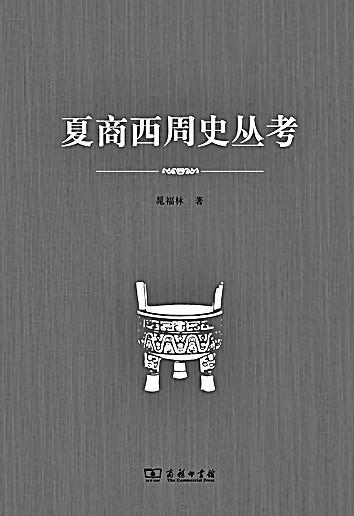


不惑之年再回校园
1943年,晁福林出生于河南杞县的一个普通人家。他自幼聪敏好学,成绩出类拔萃,17岁时,读高二时便提前参加高考,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成为历史系的一名本科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国内史学研究的重镇,新中国成立后,云集了陈垣、侯外庐、白寿彝、赵光贤、柴德赓、何兹全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北师大,晁福林聆听诸多名师教诲,受到了良好的学术熏陶,打下了深厚的治学根基。1965年,经过五年系统学习,他如期毕业,响应国家号召,远赴吉林延边汪清县一所中学做老师。此后的十余年间,他接触到的专业书籍非常有限,加之平常繁重多杂的体力劳动,对学术的渴求只能默默存放心底。唯有偶尔闲暇,他才会追忆起京城求学的时光,回味引人入胜的课堂,感念师长前辈的谆谆教导。仿佛如此这般,心绪才能稍有慰藉。

晁福林(左)与赵光贤(中)、沈长云在一起。图片由作者提供
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晁福林虽然身在山乡僻壤,但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便想抓住机会重走学术之路。他想到有两个大学同学在徐州师院工作,可能会有些便利,就把意向定在了秦汉史专业。不巧的是,该校当年只招收本省学生。晁福林无奈只能放弃,另择目标。翻查招生目录时,他惊喜地发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招收商周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竟是大名鼎鼎的赵光贤先生。本科期间,他就认真听过赵先生的课。赵先生儒雅的风范、广阔的视野、深博的学识,令他深感钦佩。于是,晁福林决心大胆一试。不久后,他如愿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大学校园。这时,他已近不惑之年。
晁福林的导师赵光贤先生是著名的先秦史专家,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古历法等领域都有很高造诣。虽是久负盛名的学者,但由于特殊的历史遭遇,赵先生开始招收先秦史研究生时,已是70岁高龄。第一届学生共有两位,一位是晁福林,另一位如今也是先秦史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河北师范大学的沈长云先生。
拜入史坛名门,晁福林受益匪浅。赵光贤先生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是陈垣先生的入室弟子。赵光贤先生受陈垣先生史源学方法的影响颇深,对陈垣先生“做考证必须遍览群书,认真核对”的教诲更是始终牢记在心。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业师身边耳濡目染,晁福林更加真切地体悟到陈垣师祖的治学精髓,为日后赓续师大的史学传统奠定了基础。
初涉先秦史,古文字成为摆在晁福林面前的一道难关。他花了大量精力自学赵先生专门编写的教材《金文选注》,并经常向赵先生请教,积累了一定的青铜铭文知识。后来,赵先生邀请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中文系王宁教授给研究生开课,晁福林趁机夯实了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功底。此外,晁福林还跟随赵先生赴河南、陕西等地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切身体会田野考古。经过历史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考古学等多学科训练,晁福林为先秦史研究做了充足的准备。
赵光贤先生在回忆自己的学术历程时曾说:“我从王国维那里学到利用古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作考证工作;从崔述和顾颉刚那里学到不轻信古书和辨伪的门径;从郭沫若的著作中开始学习甲骨文和金文;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赵先生博采众多名家之长,形成了融考证与理论于一炉的学术风格。四十余年来,晁福林始终秉持赵先生的治学理念,沿循赵先生的治学道路,史料考辨和理论建设双管齐下,既坚持历史学的求真旨趣,又不断追求理论创新。
读硕士的时候,除了循循善诱的良师,晁福林还有不少意气相投的益友。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借住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师大学生共用食堂和图书馆,彼此熟识之后,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聊天。这些经历过“文革”风雨的年轻人,个个心潮澎湃,颇有恰同学少年之感。多年后,晁先生依然清晰记得当年与同学们相处时的趣事。有位同学不仅学识过人,而且善于修理自行车。见他修车麻利,有人就说:“当年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怕也没有这般本事。”接着就有人回应:“因为王氏父子不会修车这类鄙事,才成就了两位朴学大师。”立马,又有人跟上:“咱们既会修车,又会读书,还不令王氏父子羡煞!”谈笑风生之中,透露出大家对个人命运随时代浮沉的感慨。
处在那个热情似火的年代,晁福林格外勤勉。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不免重荷在肩,为了维持日常生计,他有时也会编撰一些辞典和通俗读物,赚点零花钱。但在养家糊口之余,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书,他最向往和憧憬的,仍是做一名纯粹的学者。很快,初出茅庐的他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文。一个硕士生能够在如此高水平的期刊上崭露头角,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不多见的。
重新发现“氏族时代”
在20世纪学术史上,关于先秦社会形态的学术论辩发生过多次,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三十年代,众多学者对历史上的中国社会性质展开了激烈论战。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又掀起了一场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学术大讨论。其中,中国古史分期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时间界限问题是绽放得最为绚丽的一朵。参与论战的西周封建论者、战国封建论者和魏晋封建论者各持己见、激烈交锋,引发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当时还在读大学的晁先生就是热情的观战者之一,为了解最新进展,他经常和同学们争相翻阅论战主阵地《历史研究》刊发的宏文。同时,他心中也埋下了学术研究要观照重大理论问题的种子。

晁福林(右)课后给学生答疑。图片由作者提供
70年代末,长久的学术沉寂被打破之后,古史分期讨论问题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赵光贤先生《周代社会辨析》即为一部代表性论著,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周代的社会性质,是“西周封建论”的集大成者。晁福林甫一进入师门,恰逢赵光贤先生这部大作出版,遂将其作为治学样本,一边思索感兴趣的选题,一边仔细揣摩赵先生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得到老师的首肯和鼓励后,他将《周代“乡遂制度说”辨析》定为研究起点,正式开启了先秦社会形态研究。
那时,每当外面风雨大作而又不愿意顶风冒雨奔向图书馆借书、看书的时候,晁福林就在北京师范大学那栋编号“学12”的研究生宿舍楼里,与同学讨论先秦社会形态问题。他戏称那间小宿舍形似“鸟笼”,但他们的思想早已冲破“鸟笼”,飞向远方。他说:“过去,限于学术发展的形势,大家不可能就这个问题深入全面地进行研究,不少问题也就只能是说说而已。后来,我能够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实得益于思想解放的大形势,得益于思想禁区被逐步打破。”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中国古史学界迫切呼唤构建新学术体系,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回应的重大理论问题。继广西的黄现璠、青海的张广志两位先生之后,晁先生经过孜孜不倦的研究,提出中国古史只存在一定范围的奴隶制度的观点,力倡“夏商两代应为氏族封建制、西周则是宗法封建制、东周步入地主封建制”。这个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晁先生由此声名鹊起。紧接着,“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到底是什么”成为徘徊在晁先生脑海中的另一个疑团,他开始酝酿对整个先秦社会形态的讨论。2003年,晁先生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形态”的概念,并强调中国社会形态是中国古代历史固有的,并不是人们“研究”出来的。古代中国文明相对独立、充满活力地持续发展,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独具特色,并非正常社会发展形态的变异,而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形态。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系统。
晁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形态”的创设为科学说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断代,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相貌。若以单一化的模式来梳理纷繁的历史,犹如以简单的色调来描绘五光十色的场景,容易丧失其本相与神韵。为了化解这个症结,他吸收和借鉴了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叙事,布罗代尔着眼于探讨历史发展的多重因素。在他的笔下,历史宛若一片波澜壮阔的大海,长时段(社会结构,布罗代尔称之为“网络构造”,包括地理、社会组织、经济、社会心理等)是深不可测的潜流,中时段(社会、经济、政治)如同潜流之上汹涌而来的潮汐,短时段(人物、事件)则不过是潮汐的浪花。简言之,长时段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要素。按照布罗代尔的理论模式,晁先生发现,先秦时代尽管历经数次王朝更迭,但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氏族,不仅伴随中国古代从野蛮走向文明,而且进入文明时代后,依然持续存在。进而,他觉察到整个先秦时期的深层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变革,最终追寻出“氏族时代”是中国上古历史进程中最显著的“长时段”因素。
为了探清中国历史深海的隐秘所在,晁先生以“氏族时代”为主线,将先秦时期大体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远古至五帝时期,氏族出现和初步发展;第二阶段,夏商时期,氏族广泛发展;第三阶段,西周春秋时期,氏族发展的关键是适应新的社会局势而大量涌现宗族;第四阶段,战国时期,氏族时代向编户齐民时代过渡,走向终结。这样一来,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高层理论与繁复的中国古史实际之间,架起了一座中层理论的桥梁。社会形态理论体系的丰富使得先秦时代被多层次地梳理出来,真实的历史面貌能够更充分展现。
晁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古代社会形态,对构筑中国社会形态理论体系、释放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学术活力贡献卓著。虽然晁先生自嘲为“狼狈的探路者”,但其拓荒之功不言而喻。
跨界“第二线”
传世的先秦文献相对稀少,加之辗转传抄,不少文献不仅佶屈聱牙,而且存在错讹。如果只用这些文献来探求先秦历史的本相,往往难以得到满意的结果。因此,扎实的文献考证工作固然重要,另辟蹊径也是势所必然。
赵光贤先生曾说:“考古工作者站在第一线,古文字学家和古器物学家站在第二线,历史学者站在第三线。”受老师影响,晁先生非常重视出土文献和古文字。
20世纪80年代前期,晁先生曾专门从事甲骨卜辞研究。甲骨文是商朝后半期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直接承载着商周时期的历史记忆,是窥探商代历史的极佳史料。他先临摹《卜辞通纂》,以此来认识甲骨文,慢慢熟悉其体例,再参照郭沫若、于省吾、陈梦家、唐兰、容庚等古文字学家的文章,琢磨具体的考释方法。下了一番苦功之后,他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古文字研究法,写出了诸如《从甲骨卜辞看姬周族的国号及其相关诸问题》《殷墟卜辞中的商代名号与商代王权》等名篇。虽然后来晁先生自谦地说,因为古文字研究太难而被迫中途放弃,但事实上,问津冷门绝学、淬炼考证之功恰是其学术研究的础石。
进入21世纪,大量战国简帛文献的问世与公布,催生了一系列新的学术热点。正如史学大家陈寅恪所论“预流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面对新材料的涌现,晁先生的目光投向了先秦社会思想研究新领域。自2001年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公布,晁先生便启动了“上博简”《诗论》的研究工作。《诗经》是上古时代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诗论》则是孔子师徒研讨、评论《诗经》的汇集,反映了早期儒家的社会思想。历时逾十余年之久,晁先生在重新编联和疏证全部竹简的基础上,展开《诗论》简的系统研究,囊括作者、性质、特点、意义等方面,可以说蔚为大观、新见迭出,使得千年遗珠重新散发出先秦儒家思想的光辉,湮没已久的战国时代儒家诗学的面貌随之浮现。因《诗论》牵涉《诗经》的若干未解之谜,晁先生对上博简《诗论》的研究延展至《诗经》学史。譬如,关于《诗经》这部书的研究早已构成古代诗史研究的大宗,但《诗经》的编纂宗旨和目的却一直悬而未决。晁先生根据简文记载,推断其是为阐述和宣扬“文王受命”的周朝立国之本所作。又如,“孔子是否删诗”这桩《诗经》学史上聚讼千年的学术公案。晁先生拨开司马迁“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一语的历史迷雾,使用“二重证据法”,对照《诗论》竹简与今本《诗经》,考析和统计出孔门师徒论诗共63篇,其中56篇见于今本《诗经》,有3篇可以肯定见于今本,只是不知系于何篇。另有4篇存疑者,也不能否定其见于今本的可能性。如果孔子确曾删诗,《诗经》的文本则会与之大相径庭。一言以蔽之,上博简《诗论》为孔子未曾删诗之说提供了重要旁证。
晁先生也十分关注“清华简”。2016年,“清华简”第6辑的整理报告会揭晓了郑国早期的历史面貌,尤其是还原了郑武公曾有三年居于卫国的史实。听罢,晁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有文学家把郑国的历史改编成小说或影视剧,可能比《芈月传》还精彩。”可见,他对出土文献焕发学术价值的欣喜之情。
晁先生对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关注,始终带着历史学家的理论关怀。在竭力激活古简生命的同时,他还尝试宏大叙述思想史的新模式。在融入大量新出土简牍材料的前提下,他深化侯外庐先生倡导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理路,采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社会史理论”,以“社会思想”为体系架构起了传统精英思想史所不能反映的“思想全貌”,在近年古史学界流行的“重写”风潮中,树立起了思想史书写的“新范型”。
正如著名学者李学勤所说:“晁福林教授在先秦史领域中获有丰硕成果,恰由于他既在历史文献研究方面有深厚功力,又非常注意考古学以及古文字学的新发现、新观点,而其根本鹄的集中于富有理论意义的重要课题,这是他各种论著的读者都能感受得到的。”
培养先秦史研究的后备力量,也是晁福林先生不遗余力的事业。在栽培学生方面,晁先生有着自己的“独门秘籍”。一是要求学生深读《经义述闻》,撰写读书札记。清代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是一部从经学、小学和校勘学角度研究《周易》《尚书》《诗经》等中国古代经典的著作,解释了大量经史传记中的讹字、衍文、脱简、句读。如果能将整本贯通下来,对于筑建治学基本功大有裨益。另外就是每年专门为硕博研究生开设几次论文课。熟悉晁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很少干涉学生的具体研究方向,但这门论文课则要求提交与毕业选题不同的论文,目的是促使学生拓宽学术视野,别总围着毕业论文转。每次论文课大约持续三到四天,从清晨到深夜,晁先生对每位学生的论文都详细指导。每轮下来,不少年轻学生都感慨神劳形瘁,晁先生却倾心如注、甘之若饴,而且坚持了数十年。
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曾说:“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综观晁先生的学术历程,这样的“一二十年”何止一个?如今,年近耄耋的他依旧每日坚守在青灯黄卷之旁,神态安然,下笔有神。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4日11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