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史实言,如历史事件发生的年限看,基本可说是真实的。因为太史公的时代,文献保存是个大问题(竹简和帛书都很难保存下来),尤其还经历了秦朝李斯提议的焚书事件和挟书令事件,所以到了汉朝,史料阙如的情况下,构建历史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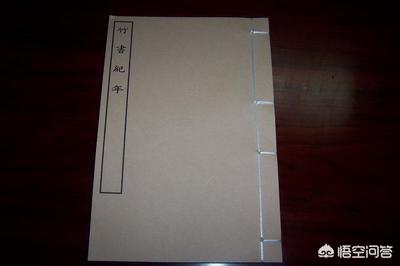
纪年在史实的基础上是否存在主观虚构?
笔者最初找到纪年时,发现其上限是从黄帝开始的,而非当时流传较广的尧舜禹始,同时,一些人也不谈这本史书对汤武革命的态度。但如果我们自己读过书就可以发现,《纪念》把所有上古帝王都喷了个遍,没有一个落下,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圣王在《竹书纪年》作者群的眼里差不多都是乱臣贼子。

记得以前有人引韩非子和曹丕来说明《纪年》涉及到主观判断的地方可靠,当时笔者尚才疏学浅,也没有走向专业化,所以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后来却发现,曹丕事件本是孤证,而孤证不立。至于《韩非子》,我怕这些人根本就没好好读书,否则,任何一个读过韩非子作品的人总会发现,韩非子对“舜囚尧……”这些人的观点之态度根本就是——乱臣贼子、党羽之言。可见,就算韩非子本人,也绝不认同这些观点。而很多人之所以会如此坚定的认为韩非子有近似的言论,那是因为把舜迫尧误作了舜囚尧。韩非子的态度其实是,大臣如果修身明德,就会把君王比下去,这就是迫君,臣子最好的做法是,暗地里做好事,明面上则把成就都归功于君主。可见,迫和囚绝不是一回事。
《竹书纪年》为何会出现这种怪异的历史观呢?不清楚,但后世的黄老学派可能跟它有关,因为二者都相信,无论君王如何混账,只要臣子反抗了,便是大逆不道。所以我们看《竹书纪年》,它从不说那些末世帝王有多坏,也不说反抗者的品德如何,而单纯只考虑一个问题——做大臣的,永远不要反抗君主,否则就是乱臣。或许正是在这个原则的驱使下,那些史实才会被做了改动——起义和革命都是大逆不道的反叛,采取禅让制度而不是家庭父子承包制,那我们就写你杀死了君主。

我们知道,孔子是否作了《春秋》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春秋笔法,这个用法大家都耳熟能详。问题在于,春秋笔法之于先秦,本是很常见的作史原则,即使说孔子确实作了春秋,却也不能把对春秋笔法的批评推给孔子。从《左传》中不难发现,当时的史官记史本身就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较大程度上以君王为准则。但孔子的《春秋》(笔者比较认同这一种观点),却是对天子和诸侯双方同时做出了批评,所谓罪我者春秋,除了孔子并非史官外,对天子和诸侯双方的批评才是后人可能批评作者的重要理由。另外,当时的史官把重心放在君王身上,不意味着他们作史就没有危险,当时本是礼坏乐崩的年代,史官所记,必然要得罪权臣诸侯,而后者要杀前者,简直易如反掌。
所以,《古本竹书纪年》虽然对我们校正《史记》有很大帮助,却未必没受到春秋笔法的影响。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它相较于早期的史书而言,是绝对的唯天子论者。
清朝学者从另一角度指出,晋人本身就有弑君的传统,所以,他们很可能像曹丕那样,把自己的行为普遍化。有点像什么呢?今日若有个大偷偷窃了不少财物,必定会想象,全天下人可能跟我一样都是偷窃犯——它们属同一个范畴。
不过,《纪年》还有一种可能,除了韩非子的批评,我们推测的史书书写原则,以及清人某些学者的推测三种情况外,公孙龙子之前的一些荒诞而不可看作信史的名家人物或也有关联。这些传说中,确实存在从反面理论批驳三皇五帝的例子,那么即便不是信史(非公孙龙子以前的情况,而是在其后),也未必能说后来没有随着辩论思潮出现过这些思想。或许,正是这些思想影响了史书作者的看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