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之“贞洁与情欲”

贞洁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性规范的核心,这种观念在话本小说中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话本小说宣扬了这种观念,而另一方面,话本小说又对人的情欲持肯定态度,这种看似矛盾的状态客观上反映了明末社会人性观念的觉醒和女性地位的微妙变化。在话本小说中,一方面小说常常以“戒色”进行劝惩教化,一方面又对男女性事大释渲染,表现出一种明知故犯的矛盾心态。贞洁与情欲往往同时出现在作品之中,但往往向后者倾斜,小说对情欲的渲染使贞洁观念作为劝惩目的边缘化。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一是因为明末社会风气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变得轻薄奢靡;二是因为读者对话本小说的反向塑形作用,即读者以购买行为来表达兴趣,坊刻者因牟利而对话本小说作者的创作行为产生影响;三是因为市民阶层崛起无论在社会风气上还是知识分子上都会受此影响,并以各种形式表达新兴阶层的声音。因此,话本小说无论写作形式还是思想表达都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学艺术活动,而是掺和了各种因素,在各方交流磨合基础上形成的通俗小说创作潮流。
话本小说中有部分小说虽表现出了对于封建贞节观念的遵从,但更多的是对之的背反,比如我们反复举的例子《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中的皇甫妻在丈夫获知她被冤枉之后,在自己努力下终于使简帖僧伏法,与妻子重归于好;《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蒋兴哥之妻王三巧因红杏出墙而被丈夫休掉,其妻欲自杀被父母劝阻,并说她还年轻貌美何愁再找个好人家,于是嫁与一个知县,后经过一些因缘巧合,最终与蒋兴哥重新团聚,王三巧的经历如果按照其身份可以有如下转变:妻子——情人——二房——妾,这种由蒋兴哥的妻子变作其妾的过程,虽说遵循了封建婚姻制度先娶为妻,后娶为妾的规范,但在王三巧的身上难以被封建贞节观念中“从一而终”思想所容,但无论蒋兴哥、王三巧的父母、甚至包括那位知县都没有觉得王三巧的再嫁有什么不妥,而王三巧本人虽曾有自杀念头,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再嫁的事实。在话本小说中,对于女性再嫁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如《警世通言》卷35“况太守断死孩儿”中,邵氏23岁丧夫守寡,于是家人等劝其改嫁:
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后日长,劝他改嫁。叔公丘大胜,也叫阿妈来委曲譬喻他几番。那邵氏心如铁石,全不转移,设誓道:“我亡夫在九泉之下,邵氏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绳上死!”众人见他主意坚执,谁敢再去强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妇。”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倒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
这里可以看出人们对寡妇再嫁是持赞成态度的,倒是邵氏决意“从一而终”,但这种泯灭人性的观念无法代替活生生的现实,邵氏终于在守节十年之后在别人引诱之下自己自投上门、自愿失身。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文中的叙述声音,即“自古云”之后的议论,这无疑代表了一种隐含作者的声音,从而体现出话本小说背反式文化叙事中迥异于封建主流价值的叙事伦理形态,这是一种凌驾于故事之上的伦理形态,故事作为一种整体的伦理表达而存在,叙事本身便是一种伦理的教化与思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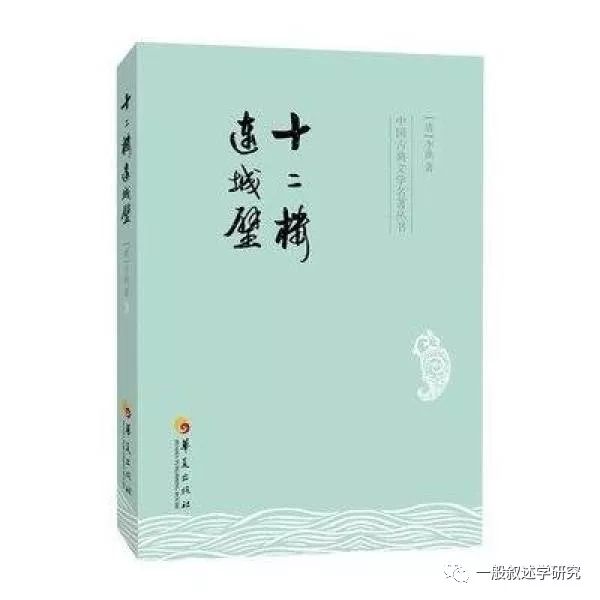
在李渔的作品中,这种背反式文化叙事更是司空见惯,比如在《连城璧》中,李渔无疑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个游离于封建主流文化之外,又千方百计向主流封建价值观念靠拢的世界,私奔、惧内、乞丐、赌徒、妒妇、同性恋等等千奇百怪,但李渔写来极为认真,无处不在的议论体现出了隐含作者声音和由这种声音传达出的、听起来头头是道、颇理直气壮的观念,这种作者的叙事伦理,无法让读者一下子判断孰是孰非,但故事的非主流性质与价值观念的主流性构成李渔小说特有的叙事张力系统,李渔小说的叙事伦理便来自这种张力所带来的小说的“游戏性”,因此,“游戏”构成李渔小说特有的叙事伦理,作者没有当真,读者何必较真呢!如《连城璧》外编卷五“婴众怒舍命殉龙阳抚孤茕全身报知己”中一开始便进行一番男女乃天地赋形、自然造化的议论,然后话锋一转,论及所谓的“南风树”(即同性相恋),接着写道:
看官,你说这个道理解得出,解不出?草木尚且如此,那人的癖好一发不足怪了。
如今且说一个秀士与一个美童,因恋此道而不舍,后来竟成了夫妻,还做出许多义夫节妇的事来。这是三纲的变体,五伦的闰位,正史可以不载,野史不可不载的异闻,说来醒一醒睡眼。
以“节妇义夫”的封建伦理来规范同性恋之间的行为,或者说同性恋者用这种主流价值规范自己的行为真是对这种用以规范男女的封建伦理一种极妙讽刺,小说写季芳和瑞郎之间轰轰烈烈的“同性”恋情,瑞郎竟用剃刀自阉来捍卫与季芳之间的恋情,难怪小说最后这样议论:
看官,你听我道:这许季芳是好南风的第一个情种,尤瑞郎是做龙阳的第一个节妇,论理就该流芳百世了;如今的人,看到这回小说,个个都掩口而笑,就像鄙薄他的一般。这是甚么原故?只因这桩事不是天造地设的道理,是那走斜路的古人穿凿出来的,所以做到极至的所在,也无当于人伦。我劝世间的人,断了这条斜路不要走,留些精神施于有用之地,为朝廷添些户口,为祖宗绵绵嗣续,岂不有益!为甚么把金汁一般的东西,流到那污秽所在去?
与小说描写极其认真的态度比起来,这种来自隐含作者的议论显得那样苍白,但又是那样认真,用贞洁观念来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方式在中国古代同性恋小说中这一篇可以说做到了极致,这种非主流的“恋爱”方式与主流的价值规范形成一种张力系统,而这种张力系统又极认真的表现在人物的行为之中,而来自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又表现出对这种行为方式的鄙薄,这就与上述张力系统的两方面形成第三方面,并与前二者形成“第三张力”系统,由此可以看出,李渔一方面述背反主流文化之事,一方面又将主流价值规范作为毫无说服力的“遮羞布”,而另一方面却以之作为“教化”的材料,尽管它是苍白无力的。李渔小说背反式文化叙事表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状态,而游戏人生永远是李渔作品叙事伦理追求的核心。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