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20年因为受疫情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变得有点儿乱,不过生活还要继续,所以新年到了,还是要盘点一下过去一年的收获。
2020年,正值笔者所供职的山东大学法学学科复办四十周年,学院欲藉此梳理这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盘点成就,作为向未来“再出发”的一个新起点。学院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认为笔者作为一名1985年入学、毕业后留校,学习、生活、工作从未离开过学校的山大人,主持编纂法学院院史是比较合适的人选。经过近一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在年终举办院庆庆典时,终于向师生及校友们呈现了一本虽不完美但相对完整的院史书稿,也算是一年的收获吧。
当我在故纸堆或发黄的老照片中,寻找和梳理学院发展的线索时,心情也会随之沉浮起落。因为每一个“事件”的背后,关联的都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人,曾经在学院学习工作过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与法学院难忘的故事。史事即人事,编纂法学院史,也就是在讲法学院人的故事。
因为我们举办的是山大法科的“复办”庆祝活动,也就是说山大历史上曾有过法科,因此,搜集整理“复办”之前法科教育的史料,就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从现有档案史料可以了解到,1926年,在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期间,在合并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等六所专门学校的基础上重建的省立山东大学中,设有文、法、工、农、医五个学院,在法学院中则设有法律系,1927年,法律本科共毕业学生约40名。只是到了1928年,在济南发生五三惨案后,由于办学经费无着,山东大学被迫停办,法科教育也因此中断。
那么,在学校及学科停办后,当时在校生们的去向几乎无人关注。在这次收集的资料中,笔者注意到,在1929年8月的一份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为恳请恩准呈请教育部保送生等原级生插入北平大学肄业事窃钧会议决国立青岛大学不续设原山东大学法医两科,所有原法医两本科生,曾代发给修业及介绍证书,以凭按年级转学有案。”只是当原山东大学法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刘升岐、彭永年等学生,拿着学校开具的介绍信申请转学时,北平大学却并未接收他们,这些学生只得回省,希望呈请“中央教育部”,保送原级生能插入国立北平大学肄业,使“生等四五年之光阴,亦不致化为泡影”。由此可以看出,在省立山东大学停办后,曾对当时在读且尚未毕业的学生提出了安置方案。只是这种“安置”未被北平大学接受,学生们的求学之路也因此而受阻。
学校停办只是校史中的一个片段,可当时那些失业教师、失学学生何去何从的故事,却未被完整地记录下来。值得欣慰的是,在另一份档案中,我们发现了彭永年的“下落”。档案记载,“案据学生彭永年呈为前在前山东大学法本科修业二年,转入北平中国学院,于民国二十年六月毕业。现拟请办律师证书,请填发在前山大修业成绩表等情”。由此我们可知,彭永年后来转学到了“北平中国学院”,毕业后,需要有在山东大学法科学习的证明以申办律师证书。这份档案材料,最终为山大法科停办后个别学生的去向有了一个交代,这多少还是令人欣慰的。
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各高校法科教育一片荒芜;在法律实务界也是专业人才奇缺。法律教育界与实务界也因此而展开了一场人才争夺战,散落在各行各业中的五十年代培养的法科毕业生,遂成为争抢对象。在这次院史收集整理过程中,对老教师的采访,使我们得窥其中端倪。比如教授我们民法的康维宁老师,他曾在燕京大学学习法律,后来并入北京大学,院系调整后又成为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康老师在毕业后选择做律师,属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律师。山大成立法律系,想调康老师来,当时的司法厅也想要他,他的母校北京政法学院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康老师最终选择了到山大法律系教书。康老师说在当时的法庭上,很少有律师打民商事官司的,而在刑事案件中那些被告也没有不认罪的。听着康老师这样的口述法律“故事”,再看看今天我们培养的学生,在法律实务界各专其业各守其责各安其分的现状,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国家和社会步入法治轨道的不易。
一些散落在校友手中的史料也颇有价值。作为山大法律系的创始人、著名的法史学者乔伟先生,就为九三届的学生题写了“以法兴邦”四个字。当笔者看到这幅字的时候,心中还是很震撼,因为它所代表的是老一辈法学者对法治的期许、对学子的希望。他们保持对法治信仰的乐观与胸怀,也正是我们纪念法科复办四十周年所要彰显的精神之一。
山大法科教育的成长,只是中华大地上法科发展的一个缩影。每个大时代下的法学者,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也会有属于各自时代的法律故事。在新年到来之际,如何讲好我们的故事,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所面临的课题。
过去的2020年因为受疫情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节奏都变得有点儿乱,不过生活还要继续,所以新年到了,还是要盘点一下过去一年的收获。
2020年,正值笔者所供职的山东大学法学学科复办四十周年,学院欲藉此梳理这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盘点成就,作为向未来“再出发”的一个新起点。学院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认为笔者作为一名1985年入学、毕业后留校,学习、生活、工作从未离开过学校的山大人,主持编纂法学院院史是比较合适的人选。经过近一年的资料收集、整理,在年终举办院庆庆典时,终于向师生及校友们呈现了一本虽不完美但相对完整的院史书稿,也算是一年的收获吧。
当我在故纸堆或发黄的老照片中,寻找和梳理学院发展的线索时,心情也会随之沉浮起落。因为每一个“事件”的背后,关联的都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人,曾经在学院学习工作过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与法学院难忘的故事。史事即人事,编纂法学院史,也就是在讲法学院人的故事。
因为我们举办的是山大法科的“复办”庆祝活动,也就是说山大历史上曾有过法科,因此,搜集整理“复办”之前法科教育的史料,就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从现有档案史料可以了解到,1926年,在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期间,在合并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等六所专门学校的基础上重建的省立山东大学中,设有文、法、工、农、医五个学院,在法学院中则设有法律系,1927年,法律本科共毕业学生约40名。只是到了1928年,在济南发生五三惨案后,由于办学经费无着,山东大学被迫停办,法科教育也因此中断。
那么,在学校及学科停办后,当时在校生们的去向几乎无人关注。在这次收集的资料中,笔者注意到,在1929年8月的一份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为恳请恩准呈请教育部保送生等原级生插入北平大学肄业事窃钧会议决国立青岛大学不续设原山东大学法医两科,所有原法医两本科生,曾代发给修业及介绍证书,以凭按年级转学有案。”只是当原山东大学法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刘升岐、彭永年等学生,拿着学校开具的介绍信申请转学时,北平大学却并未接收他们,这些学生只得回省,希望呈请“中央教育部”,保送原级生能插入国立北平大学肄业,使“生等四五年之光阴,亦不致化为泡影”。由此可以看出,在省立山东大学停办后,曾对当时在读且尚未毕业的学生提出了安置方案。只是这种“安置”未被北平大学接受,学生们的求学之路也因此而受阻。
学校停办只是校史中的一个片段,可当时那些失业教师、失学学生何去何从的故事,却未被完整地记录下来。值得欣慰的是,在另一份档案中,我们发现了彭永年的“下落”。档案记载,“案据学生彭永年呈为前在前山东大学法本科修业二年,转入北平中国学院,于民国二十年六月毕业。现拟请办律师证书,请填发在前山大修业成绩表等情”。由此我们可知,彭永年后来转学到了“北平中国学院”,毕业后,需要有在山东大学法科学习的证明以申办律师证书。这份档案材料,最终为山大法科停办后个别学生的去向有了一个交代,这多少还是令人欣慰的。
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各高校法科教育一片荒芜;在法律实务界也是专业人才奇缺。法律教育界与实务界也因此而展开了一场人才争夺战,散落在各行各业中的五十年代培养的法科毕业生,遂成为争抢对象。在这次院史收集整理过程中,对老教师的采访,使我们得窥其中端倪。比如教授我们民法的康维宁老师,他曾在燕京大学学习法律,后来并入北京大学,院系调整后又成为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康老师在毕业后选择做律师,属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律师。山大成立法律系,想调康老师来,当时的司法厅也想要他,他的母校北京政法学院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康老师最终选择了到山大法律系教书。康老师说在当时的法庭上,很少有律师打民商事官司的,而在刑事案件中那些被告也没有不认罪的。听着康老师这样的口述法律“故事”,再看看今天我们培养的学生,在法律实务界各专其业各守其责各安其分的现状,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国家和社会步入法治轨道的不易。
一些散落在校友手中的史料也颇有价值。作为山大法律系的创始人、著名的法史学者乔伟先生,就为九三届的学生题写了“以法兴邦”四个字。当笔者看到这幅字的时候,心中还是很震撼,因为它所代表的是老一辈法学者对法治的期许、对学子的希望。他们保持对法治信仰的乐观与胸怀,也正是我们纪念法科复办四十周年所要彰显的精神之一。
山大法科教育的成长,只是中华大地上法科发展的一个缩影。每个大时代下的法学者,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也会有属于各自时代的法律故事。在新年到来之际,如何讲好我们的故事,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所面临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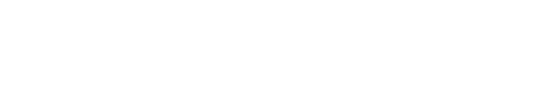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