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于《古今书录》增订本
王重民应该也觉察到了《开元四库书目》与《古今书录》的同一关系,故不采信余嘉锡的观点,而提出了一个新看法:
《新唐书·艺文志》是欧阳修在公元1054—1060年依据《古今书录》(其实际意义是依据《旧唐书·经籍志》)编成的……《新唐书·艺文志》的每个类目内,分“著录”与“未著录”两部分。“著录”是指《古今书录》原有的著录,“未著录”是指欧阳修所增入的唐代著作。《艺文志》著录了开元时代藏书53915卷,比毋煚自己所称的(也是《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的)51852卷较多一些,拿《艺文志》的著录和《经籍志》比较,所著录的图书数目也确是多些,注解说明也详细些(其中还有一些是欧阳修用自己的意见改动的),因此,疑欧阳修所据的《古今书录》是一个经过增订的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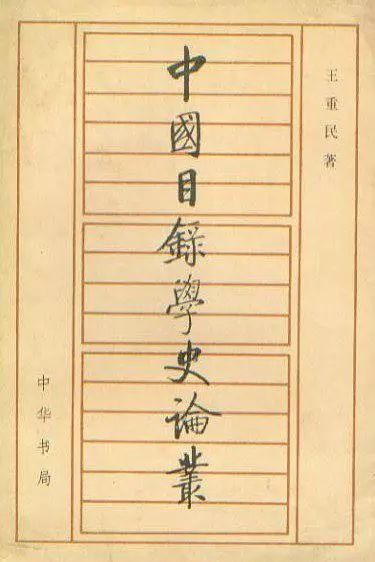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
王重民对《旧志》与《古今书录》的关系,对《新志》与《古今书录》的差异有很清楚的认识,因而提出了一个《新志》所据是“增订的本子”的设想。但唐宋文献中没有任何资料透露过《古今书录》曾有修订的信息,而且五代刘昫等撰《旧志》,其采用的《古今书录》也没有任何修订过的痕迹。因此说,虽然增订本《古今书录》可以解决《新志》差异的矛盾,但却只是一个假想,而且是不太合乎情理的假象:《古今书录》名为“古今”,实际仍是开元藏书目录,后人若非重编开元藏书总目,自不当对早已广泛流传的这部《古今书录》擅作增订,在目录学史上,也不曾出现过这类后世增订前代藏书目录的现象(作伪者除外)。
五、增损改易《古今书录》或《旧唐志》
主张此说的有台湾学者乔衍琯,其论之曰:
其实以班固删节《七略》,且又稍加增损改易而成《汉志》的例子来看,《新唐志》对《古今书录》或《旧唐志》,也会稍加增损改易,而不必照单全收。所以不仅比《古今书录》多出两千多卷,也有删减改易的地方。
此说似较合理,且有《汉志》与《七略》之关系为例,容易为人接受,但失之含糊,故亦少有影响。应该说,《新志》对《古今书录》的“增”与“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此意谓:《新志》对《古今书录》原则上是不能减省的,因为《古今书录》是开元时期的藏书目录,《新志》的“著录”部分正是要表现唐代开元时期的著录盛况,除去欧公视作偶尔的重复著录外,不应该删去任何一部图书的著录;而《新志》对《古今书录》的增补,也不是像《汉志》对《七略》那样只有区区三家的不同,而是多出二千余卷,此于《古今书录》之外的开元书目必定别有所本。

乔衍琯《中国历代艺文志考评稿》,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
六、综合《古今书录》与《群书四部录》
这是台湾学者杨果霖在他的新著《新旧唐书艺文志研究》中对《新志》“著录”来源所作的新探讨:
若《新唐志》已著录部分不全是根据《古今书录》,尤其是多出的二千余卷典籍究竟是从何而来?《群书四部录》载录“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古今书录》增新目“六千余卷”,然而《古今书录序》仅言“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其中差距“二千三百余卷”。乔好勤先生于《中国目录学史》中已经注意此一现象,他认为毋煚对于《群书四部录》必有删除,其说可从。《古今书录》删录《群书四部录》为何书,今已不得详考。《新唐志》已著录典籍达“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且云根据“开元著录”,则较接近的推测是根据《古今书录》、《群书四部录》的综合,再删去重复卷帙而来。案:《古今书录》较《群书四部录》增加六千余卷,若《古今书录》并无删录,则总卷数当为“五万四千一百六十九卷左右”,其距《新唐志》已著录典籍“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已然未远,若加上卷数的可能改变、重复等因素,则《新唐志》已载录部分当非全据《古今书录》,而可能是《古今书录》、《群书四部录》复删去重复著录之书所编成的。至于《新唐志》列于著录部分,而《旧唐志》未载其书,则可能是《古今书录》删录《群书四部录》的典籍;但由于今本《旧唐志》已有残缺,因此也可能是《旧唐志》遗漏的部分。

杨果霖《新旧唐书艺文志研究》,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
杨果霖先生探讨的思路是正确的,即《新志》在《古今书录》之外,对唐代开元书目必定别有所本。其不仅思路正确,而且也不乏证据。唐代开元时期的大型藏书目录,除了《古今书录》之外,便只有《开元群书四部录》,因此欧公采用《群书四部录》也甚合情理。但《古今书录》与《群书四部录》有特别的渊源关系,《古今书录》是以《群书四部录》为蓝本增订而成的,故一般人只关注《古今书录》而不太再考虑其所依据的底本。杨先生注意到,毋煚《古今书录》著录的图书总卷数,比《群书四部录》的总卷数再加上毋煚增补的六千余卷,少了二千三百余卷,也就是说,《古今书录》对《群书四部录》不仅有增补,而且也有删汰,而这正好是《新志》“著录”比《古今书录》多出的卷数,因此他推测《新志》可能是综合《古今书录》与《群书四部录》两部开元目录再删去重复之书编成的。但我们在考察《古今书录》的编撰与《群书四部录》的流传情况后发现,杨先生的这个推断是无法成立的。
毋煚据《群书四部录》编撰《古今书录》有删削与增补是可信的,其增删之情形毋煚自序中有明白的交代:“纰缪咸正,混杂必刊,改旧传之失者,三百余条;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增补六千余卷是毋煚在自序中明确交代过的,其删削者虽未作具体说明,但属于“纰缪”、“混杂”一类却是清楚的。这二千三百余卷既因“纰缪”、“混杂”而被毋煚删去,欧公又有何理由再摭入《新志》呢?而且从《新志》各类多出的各种文献看,丝毫也看不出毋煚当初删削它们的理由。如《旧志》史部伪史类著录十八部,小类后合计数目称“右……杂伪国史二十家”,据此伪史类应有二十部,今本存十八部,当是脱漏了两部;《新志》伪史类著录二十八部,除归类调整因素之外,有常璩《汉之书》十卷、《苻朝杂记》一卷、《二石书》十卷、段龟龙《凉记》十卷、刘炳《凉书》十卷等五部为《旧志》所不载,除了其中两种当为《旧志》传写脱漏外,其他三种皆为《新志》所增。若以为《新志》乃据《群书四部录》增入,则《古今书录》又因何要删去它们呢?既没有任何理由删去它们,则只能说明《群书四部录》原本就未著录它们,《新志》所增,必是别有来源。
若从《群书四部录》的流传来考察,更可确定《新志》的增补与《群书四部录》没有任何关系。《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元行冲等于开元九年撰成,至宋代,各种藏书目录及其他文献皆不见著录与征引,此书在北宋时当已亡佚。因为这是清代以前卷帙最大的一部藏书目录,这样一部重要书目文献,若北宋时尚存,《崇文总目》与《宋史·艺文志》绝无不著录之理。既已不传,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根本无从得见,所谓据《群书四部录》增补云云,顿成无根之谈。
结论:本于《古今书录》,兼采《集贤书目》
《新唐志》本于《古今书录》,这在学术上并无什么新意,但前人于此多未作论述,本文于“一、本于《旧唐志》”与“二、本于《古今书录》”二节中从《新志》与《旧志》的异同比较上确定:《新志》“著录”主要采用的是《古今书录》。若再从欧阳修编撰《新志》的旨意条例与唐代开元书目流传的情况看,更可见《古今书录》在《新志》编撰中的重要作用。欧阳修在《新志序》中称道:“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检《新志》实际著录之图书,其“著录”与“不著录”者之卷数与此约略相等。因此可知欧阳修《新志》由两部分组成,其“著录”之图书,即开元有“著录者”;其“不著录”者,即“唐之学者自为之书”。
“著录”部分既为开元“著录者”,则必据开元时期所编藏书目录。开元时期藏书目录,其巨者有二,一为元行冲等所撰《开元群书四部录》二百卷,一为毋煚所撰《古今书录》四十卷。前者至宋代已无人得见,欧阳修自然无法采用,即便万一偶存,因《古今书录》是在该书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群书四部录》对《新志》亦无甚参考价值,而《古今书录》自然就成了欧公编撰《新志》最主要的来源。应该说,《旧志》以《古今书录》为蓝本,对《新志》是有着启示作用的,但《新志》对《古今书录》的采用原则与《旧志》是大有区别的。《旧志》于《古今书录》是照单全录,《新志》则有意创新,故一则补录“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而成唐人一代著述之目,以补《古今书录》断于开元之不足;二则于采用《古今书录》时对其分类多有调整,并于其著录之外另觅来源,以补其遗漏,如此方可见开元藏书之盛与唐人著述之盛。
那么除《古今书录》之外,开元时期还有什么藏书目录呢?开元时参与《群书四部录》编撰的韦述曾编有《集贤书目》一卷。韦述,两《唐书》皆有传,其于开元五年由栎阳尉入秘阁,与元行冲、吴兢等一起编撰《群书四部录》。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中书令张说以集贤学士知院事,“引述为直学士”;二十七年“充集贤学士”。《集贤书目》当即韦述在集贤院时所编。但其编于何时,史文无载,又由于韦述“在书府四十年”,天宝间亦得入集贤,故其目成于开元还是天宝,仅据其身份尚不能确定。
但集贤院藏书之盛况,在韦述撰写的另一部书《集贤注记》中有精确统计。《玉海》卷五二“集贤院典籍”条引《会要》云:“(开元)十九年冬(十月丙申)车驾发京。时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九千卷(《注记》同):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注记》“五十三”),史库二万八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注记》“六十九”)。”从其来源看,《会要》亦当本于《集贤注记》。《集贤注记》中有言及天宝末事迹者,韦述自序亦题“时丙申岁”(天宝十五年,756),故其成书在天宝末无疑,而其所载开元十九年集贤院各库藏书卷数,颇有可能依据的就是《集贤书目》。张固也先生据此推测,《集贤书目》之成书“当亦在此年或稍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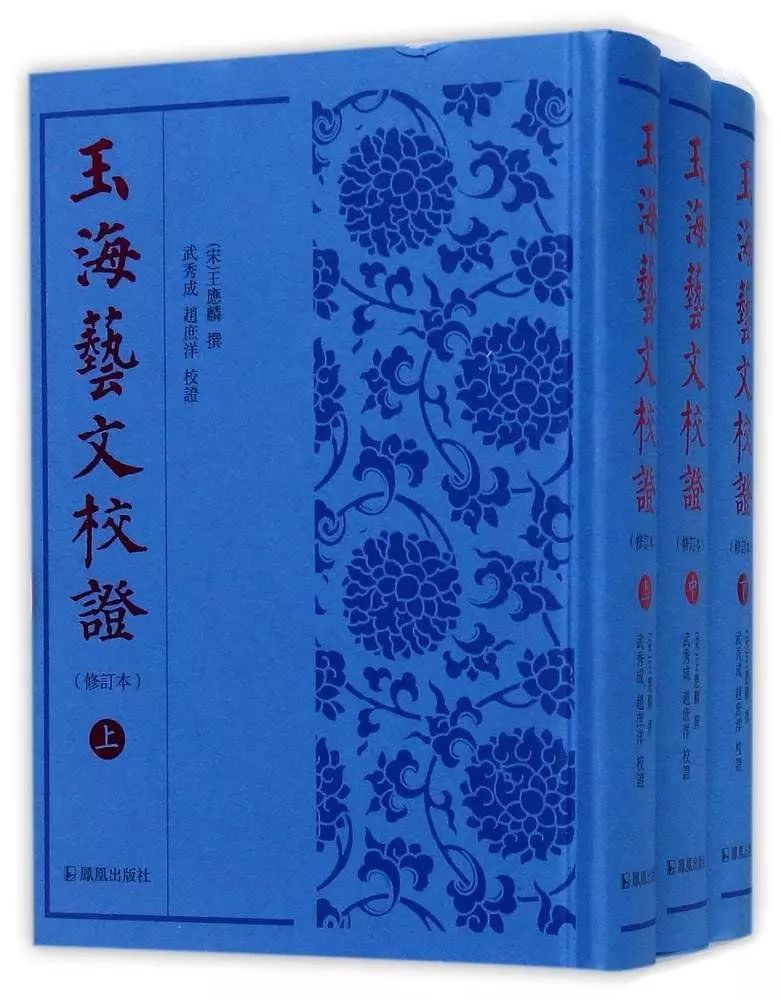
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注《玉海艺文校证》(修订版),凤凰出版社,2017年。
据文献记载,开元天宝间,集贤院确实编有书目。《唐会要》卷三五《经籍》载:“天宝三载六月,四库更造见在库书目:经库七千七百七十六卷,史库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库一万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库一万五千七百二十二卷。”总五万四千六百四十四卷。从《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及《玉海》卷五二《四库更造书目》条引《集贤注记》载此文可知,此“四库更造见在库书目”是指新编集贤院藏书目录。但在开元天宝这样的承平年代,集贤院天宝三年的藏书何以反比此前开元十九年的藏书减少了数万卷呢?其中奥秘,或是因为玄宗喜幸东都,京师集贤藏书亦有移于东都集贤院者。如开元二十四年玄宗从东都回京,即下令“集贤书籍,三分留一,贮在东都”。或是因为将集贤院所藏复本,移充秘省、史馆或其他馆院的缘故。因有此变化,故天宝三年又重编现存书目。此“更造见在库书目”,从名称看,所指当非韦述《集贤书目》,而“更造”二字也表明,此前集贤书院已经编有院藏书目,其时当在开元二十四年集贤书籍分贮之前。联系开元时期朝廷编撰藏书目录之风,以及韦述开元五年入秘阁,至开元二十四年,其居院已达二十年之久,其欲编撰《集贤书目》,宜在这一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开元十八学士”,享誉士林,几可与唐初以杜如晦、房玄龄等为代表的“文学馆十八学士”相媲美。《新志》杂艺术类著录有《开元十八学士图》,注称其为“开元人”,是开元时即有人图画其像。韦述身为开元十八学士之一,不仅荣宠当时,而后世亦想望其风采。欧阳修于此自当耳熟能详,其视韦述为开元时人亦属当然。其《集贤书目》纵不能定为开元所撰,但因其人为开元时人,故视其书目为开元著录,亦甚相宜!据此,欧阳修在编撰《新志》欲对《古今书录》有所补充时,韦述《集贤书目》无有不采录之理。此目北宋时尚有流传,见录于《崇文总目》,正是欧公唾手可得者。
此外,开元时期曾参与《群书四部录》编撰的吴兢还编有一部《吴氏西斋书目》一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宋志》皆有著录,此为欧公所亲见无疑。但《吴氏西斋书目》著录的为吴兢“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兢自撰书附于正史之末,又有续钞书列于后”,而《新志》所称唐代“著录”之图书,从前代史志目录及《新志序》下文看,当指唐代朝廷藏书,并不包括私家藏书。再者唐代及此前私家藏书的规模还比较小,其对朝廷藏书的补充作用也较为有限,故《新志》不予考虑亦在情理之中。
要之,《新唐志》直接采用的是《古今书录》而非《旧唐志》,其采用《古今书录》除删去类序、小传,调整部分图书分类外,对其著录的图书也是全部照收的。此外,《新唐志》还采用韦述《集贤书目》对开元朝廷藏书作了必要的补充。
(原文载《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微信版删去注释,略有删改,引用请据原文。)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