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山大即将迎来11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特别从“守承”和“回望”的角度,对山东大学历史学科发展过程中承载和凝结着我们“传统”的一些人和事做一点回顾。
开风气之先
山东大学在1901年将历史课程定为“中外史学”,影响了当时和后来中国几乎所有大学史学课程的设置。
是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在上奏光绪皇帝的办学奏折和办学章程中,即将中国史、外国史并列为一门“中外史学”。这也使得山大在办学之初就展现出当时的一种最先进、最阔达的知识视野。
与此同时,在教法与课时安排上,山大的办学章程还明确抵制了朝廷关于“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的“行政诏令干预”,将“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治法学”三类,平等并列为文科的三大主干。
山大能做到这一点,一是与20世纪初济南自主“对外开放”的独特氛围有关;二是与袁世凯个人的经历、见识有关;三是与袁世凯的朋友、齐鲁大学的奠基人、美国人狄考文有关;四是与狄考文的继任者、山东大学办学章程的具体设计者赫士有关;五是与首任校长周学熙有关,周学熙和他的弟弟周学渊都出任过早期山东大学的校长,而他们的父亲就是与袁世凯共同推动了济南“对外开放”的山东巡抚周馥。
总之,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山东大学的历史学科在110年前的奠基时期,就形成了今天看来仍不乏其文化厚度和思想高度,因而值得特别珍视和守护的大学传统。
《文史哲》与“五朵金花”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有五场重大学术论战,其中至少有三场是由1951年创立的《文史哲》发起和推动的,在1954年开始的《红楼梦》讨论中,高度肯定《文史哲》敢于发表“小人物”的挑战性文章。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号刊发的几篇文章。
创刊号共发11篇文章,其中历史系正副教授撰文5篇。从文章篇数和涉及的范围都可以看出彼时“文史见长”的阵容。
历史系主任、《文史哲》首任主编杨向奎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是创刊号的头条,排在校长华岗的文章之前,这也可以看出彼时的传统与风气。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实践论》,“全国学术界掀起学习宣传《实践论》的高潮”。杨向奎先生1951年5月1日发表的这篇文章,批判了胡适的考据学等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提出在历史研究中要以《实践论》中阐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为最高准则。这篇文章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研究正在从民国考据学向唯物史观史学的转变”,也反映了山大史学政治上的敏锐和政治立场的坚定,是“新意识形态在学术领域中流布和贯彻”的典范。20世纪50年代山东大学“以不守旧、趋时而著名”(季羡林语),这一特征鲜明体现在杨向奎的这篇文章中,也鲜明反映在以他为主编的《文史哲》上,《文史哲》正是合乎了时代的节拍,才多次引领学术潮流并蜚声海内外。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杨向奎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否定“考证”在历史学中的地位,也一点没有忽略史料的积累和严谨的考订对历史学的意义,他认为这都是史学研究中所必须的实践环节,都应在学习《实践论》时给予加强和坚守。
这正是山大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即:往往能敏锐地感知时代的变迁,准确切中政治与学术的最佳交叉点,并在这一交叉点上创造出学术的辉煌。
理解了山大史学的这―传统,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文史哲》创刊号上还会同时刊载了郑鹤声先生的《天王洪秀全状貌考》。该文对洪秀全的面部特征做了详尽的考证,特别是对他长没长胡子进行了追考。在后来的“史学革命”期间,该文受到批判,被当成繁琐考证的代表。但它毕竟是对农民战争领袖的细致考察,所以作者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而山大史学在整体上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学术风格:在政治与学术的交叉点上创造学术辉煌,在政治潮流中展现出学术的韧度和定力。
这一重大的学术传统,在1951年《文史哲》第二期展现得更明晰:
“1951年7月1日,童书业在《文哲史》上第二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由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中国发展规律的认知,更关系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所以吸引了几乎整个历史学界的力量来参与讨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周谷城等著名学者都是这场论战中的风云人物。而其中来自山东大学的杨向奎、吴大琨、赵俪生、童书业、王仲荦等以《文史哲》为阵地,成为这场讨论中实力最为整齐雄厚、贡献最为卓越的方面军。古史分期讨论是《文史哲》创刊后引发的首场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正是凭借此次讨论,新生的《文史哲》迅速获得了全国学人的广泛赞誉和认同。”(见郭震旦《(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商务印书馆于2011年)
但也就是在这一期《文史哲》上,还赫然刊登了历史系教授中的另一位“中坚人物”黄云眉的文章:《考证在史学上的地位》。在几乎是一边倒地把考证学推到唯物史观对面的形势下,黄文力排众说,认为考证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需要,尤其在编纂新史的资料问题上更显出它的重要性,“并呼吁在批判继承传统考证学遗产的基础上,再来一次更新的考证高潮。”
山大史学的“学术风骨”、“学术品格”,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展现出它的坚韧,显示出其作为“学术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定力与尊严。
顺便一提,1956年杨向奎调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后,接任山大历史系主任的正是黄云眉。由此也可以看出“学术共同体”在价值取向上的某种深层默契。
师生眼中的“八马同槽”
新中国成立后,山大的第一任校长华岗秉承半个世纪里形成的重贤求才传统,到处延揽高端师资。著名学者杨向奎、赵俪生、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童书业、张维华、王仲荦等齐集山大历史系,为一时之选。他们治学精神严谨,学术成果精湛。著述等身,教席入胜。这种蛊况被人戏称为“八马同槽”。其实是骐骥会驾的比喻性描述。
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师生关系、同事关系的几则回忆:
一是某校友回忆当时师生关系的,主要是讲教授之一的陈同燮:
“教授中,只有陈同燮先生的夫人不在身边。陈先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在教授中最年长,他很少写文章,一辈子只留下一本讲义,三篇文章,但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名教授’。他精通多国语言,家中却一本外文辞典也没有;他是世界史的教授,对中国古典却极精通。由于夫人不在身边,每到周日,他便约请同学们到郊区去玩。有一天,陈同燮先生同同学们去游五号炮台。面对波澜不惊的蔚蓝大海,遥望当年五百壮士英勇赴死的田横岛,他要求同学们每人赋诗一首,然后评出一二三等奖。奖品仍是他出钱,买花生给大家吃。获一等、二等的同学只管吃,只有获三等奖的同学要受罚一一跑腿去买花生。”
这样的师生关系,这种知识结构的教授,以及这样的教书育人方式,在今日山大已是不绝如缕,杳然若无。如何重续我们的传统,如何再现其中的精神风韵,这也是一个“读书人一声长叹”的大课题。
另一则回忆是教授之一赵俪生回忆“教授听京戏”的情景:
“当时有四个人是京戏迷:杨向奎、卢振华、童书业和我。大家一起去,互相请客。童听戏,也有他的怪癖。第一,他不听票价高的戏,如梅兰芳2舟元、马连良1.8元、张君秋1元等,他都不听。原因之一,怕是夫人卡得紧。(有一次,他跟我一起从合江路宿舍到大学路去上课,他花5分钱买了一包尖底纸包的花生米,倒给我一半,一面吃一面唠唠叨叨地说:连剃头加吃花生米,才给我发5块钱!)他只听东镇一家小剧院门票3角的戏。第二,他厌烦老生和旦角的唱工戏,每当慢三眼、慢四平或反二黄慢板时,我们三人都眯起眼睛听得入神的时候,童却不见了,他到吸烟室休息去了。等武打戏一上场,什么《龙潭鲍骆》,什么《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他高兴极了,神采奕奕,并且在戏散回家的路上,他一定告诉我,听了这样的戏,他的精神所得到的恢复,要比睡过一场好觉或者接受一次‘休克’治疗要强得多,明天的第一堂课一定讲得特别精彩。他甚至约请我专门去听他那一堂课。有时,联系‘龙潭鲍骆’和‘杨香武’,他能谈出一系列宋、元、明、清的社会礼俗,一直谈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他高声放肆地讲着,简直是意气风发了。”(《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赵先生的这段回忆,虽然是闲情逸笔,但这样的教授生活,这样的同事关系,这样的学术交流,恰好展示了“学术共同体”的魅力与愉悦,倒可能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大史学辉煌的真正根由。
百年山大的“世家底气”
1978年中美建交后第一批来访山大的美国学者对山大史学传统的感知:山大教授不卑不亢的“学者范儿”,倒真是凝结了百年山大的“世家底气”。
1978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年12月来访的匹兹堡大学访华团,是中美建交后第一个来山东大学访问的代表团。代表团长是该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历史学家舒尔曼。
第二年,美国俄勒冈大学周锡瑞副教授受美中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推荐,到山东大学访学一年,这是山东大学建国后第一次接受美国访问学者。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是山大在封闭数十年后的学术破冰。
舒尔曼在时任校长的吴富恒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说:“我们这次到山东大学来访问,感到十分高兴。山东大学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我过去读过你们学校历史系教师写的论文,很受启发。特别是山东大学办的《文史哲》,我很爱读,它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刊物,很有声望。我们希望你们把《文史哲》能办到过去那个高水平上去。”吴校长插话说:“这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批评。”(丁文芳:《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访华团来我校参观访问》,《山东大学报》1978年12月25日第3版)
紧随舒尔曼之后于1979年来山大的周锡瑞是俄勒刚大学的教授,他来山大是为完成义和团研究的。在后来出版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英文序言中,他回忆道:
“我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始于1979年底。那时,我在中国的山东大学和第一历史档案馆待了一年。如果没有这两个机构的支持与合作,我的这一项研究工作绝不可能完成。对我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所作的口述历史调查的原始采访记录。他们在1960年和1965-1966年深入鲁西,在这一闹过义和团运动的地区内遍访老农。……山东大学历史系向我慷慨提供的这些记录稿,比公开发表的资料选编更为完整,它对我重新探索和构建义和团的早期历史成了不可缺少的材料。正是从这些材料中,我们第一次得到从农民的角度了解这次大规模的中国农民运动。山东大学两次安排我去闹过义和团运动的乡村地区旅行。在原先的口述历史调查的基础上,我又作了进一步的采访。这些访问材料价值无量,它帮助我理解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区差异的重要性,它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一。
我尤其感谢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朋友和同行们,特别是徐绪典、路遥、李德征和陆景琪。他们是我寻找义和团运动资料的指导专家,亦总能在我的研究和看法与他们发生分歧时表示理解。”([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英文序言)
前辈学者在“乍暖还寒”的1978年,在中美关系刚刚破冰之时,能如此得体、如此自信地将不同文化置于同一学术平台,“使差异得以展示,了解得以进行”,这种不卑不亢的“学者范儿”,倒真是凝结了百年山大的“世家底气”。
直到1996年。周锡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中国老一代学者长于实证研究。过去我在中国的山东大学做研究时,深为这一优良学风所感染。”(《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和现代化进程――周锡瑞教授访谈录》,《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
舒尔曼、周锡瑞是“”后最早到山东大学访问的美国学者,他们对山大史学的认知与评说(包括他们的褒奖和批评),多少可以提示我们,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时,在融入国际学术体系时,我们应该坚守什么样的学风,应该秉持怎样的学术品格。
还应该进一步自省的是:在学术环境已经十分开放,经费也相对充足的今天,我们是否还有以往治学的“优良学风”,是否还有以往治学的精神和毅力,例如,周锡瑞再三感佩的义和团运动的田野调查,曾持续不懈地进行了60年,整整一个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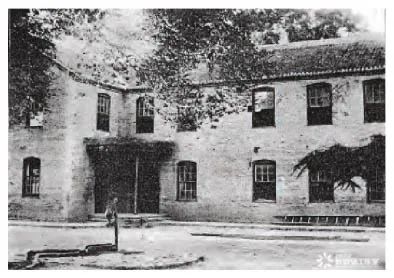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