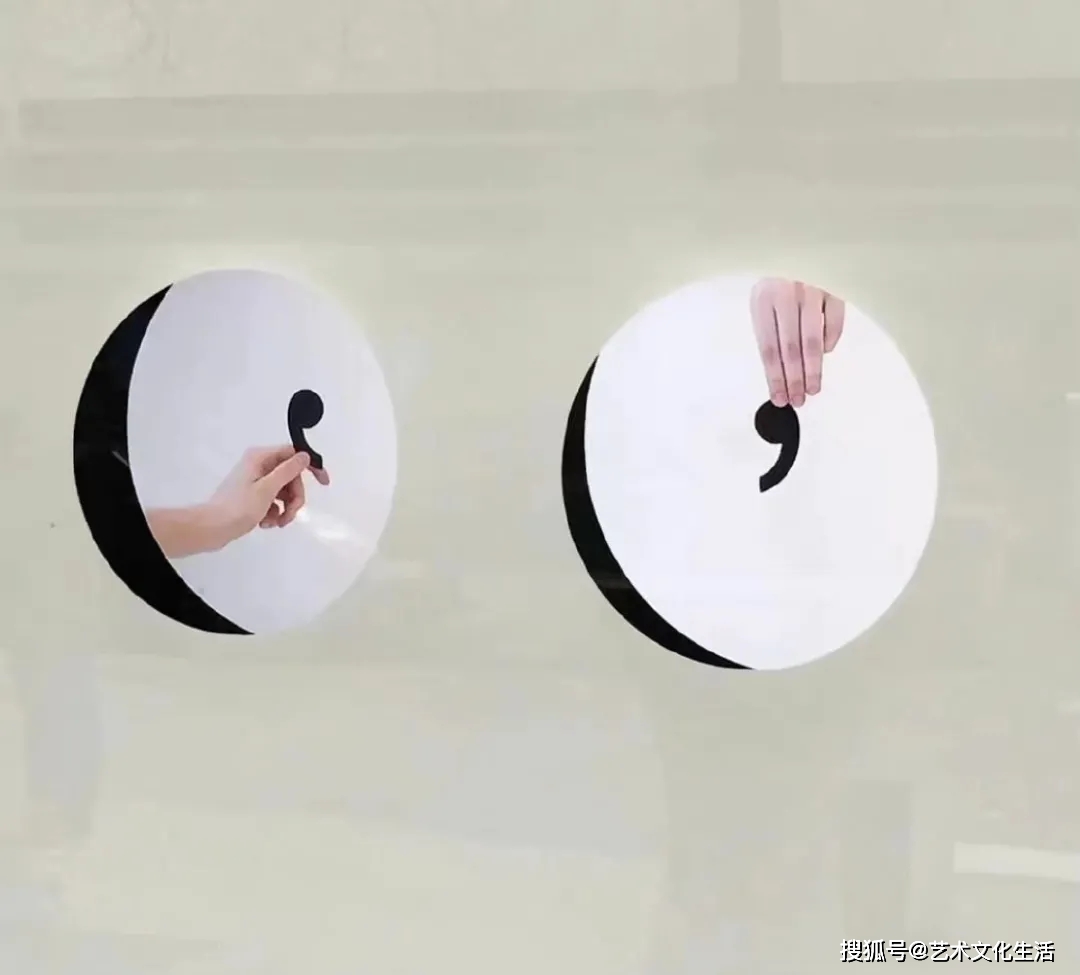
章学诚(实斋)之学,晦于当时而声光赫震于后世。自晚清以来,被尊为史学大师,北大历史系招生甚至规定考生必须读他的《文史通义》。故研究其人与其书,考证篇章、发挥大义者,不知凡几。
然“知难”之叹,在实斋生前即已有之;现在世人之所以推尊实斋者,也未必便真能知其用心。
一、史料学大师?
实斋之被推重,一是看重了他对史料的强调。
章氏“六经皆史”、“盈天地间一切著作皆史也”的说法,到了梁启超、胡适之手上,被解释为:“史部的范围很广,六经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切著作都是史料”(《章实斋年谱》嘉庆三年条)。张其昀则认为章氏之史学重在“典籍之搜罗”,“言征集史料之方法,章君所发明,远较刘君(知几)为详。……言搜罗史料之广,实为有史以来所仅见也”。此虽较梁胡所论为宽,并不仅以史料为史学。但仍是把章氏之学看成是提倡史料搜集、排比考证以获得所谓历史之真相的典型。
这个印象,显然是符合胡适所说“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见其《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及傅斯年所讲“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的科学治学方法之所需,故被拿来当了号召,距实斋学术之真相,当然也最远。故姚名达在《章实斋之史学》一文中即明确指出:
史虽不离乎史料,而史料终不可以尸史学之名。而胡适先生着《实斋年谱》,释实斋“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为“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则于史学史料之分际,尚未能深察。(《国学月报》,二卷一至二号,民国十六年)
史料不是史学。当然。但在民国初年那种狂热的材料崇拜风气下,会以史料这个角度来推崇实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姚先生责怪胡适于史料与史学之分际未能深察,其实胡适等人正是想以史料为史学的。
二、史学大师?
以史料为史学,是极狭隘极荒谬的态度,姚名达所驳甚是。然而,他虽不仅就史料搜集与考证这个角度来看实斋,但以实斋为史学,以《文史通义》为我国“史学评论第二部名著”、为“文化史学”而推崇之,是否便能掌握到实斋之学的真精神?
自北大历史系招生规定考生须读《文史通义》以来,该书正是以这种“史学要籍”的身份,为世所重。咸称实斋“为我国集大成的史学家”,视《文史通义》为“专门讨论史法史义以及一切史学问题的著作”。(见吴天任《章实斋的史学》)
但是,实斋固然曾讨论过史学,固然在《上朱大司马论文书》中说:“乙部之学,近日所见,似觉更有进步,殆于杜陵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者。”然而,就像这封信其实乃是讨论文学一样,其用心史学,至少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为了要写好古文,故以深于史学为作古文之要件。嘉庆元年三月与汪辉祖书说:“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词。而古文词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即是此意。
而且,他固然在史部自矜晚节入细,对于文学一道,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在《文史通义》之外,本有《文学》一书,编于乾隆四十七年,今虽不传,然其重文之意可见。彼《与邵二云论文书》曰:“于(文章)体裁、法度、义例,殆于杜陵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也。”
他于文学,用心显然不在史学之下。《文史通义》中,如《文德》、《文理》、《古文十弊》等皆极有关系之文字,与《史德》诸篇正相颉颃。
三、文史学
可惜世之论实斋者,对于他在文学方面的言论,往往视而不见,忘记了他的书名是《文史通义》,乃通论文史之书,本非专论史学,当时实斋且以“鄙着《通义》之书,诸知己许其可与论文”(《又与朱少白》)自喜,今若徒以史学求之,但得其半而已。
何况实斋之书又不是论文与论史各半。其所谓文史通义,自有其合言文史之旨,如《文史通义·自序》云:“余仅能议文史耳。……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原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此可见实斋是论文史的。嘉庆二年《与朱少白书》说:“平日持论,关文史者,不言则已,言出于山,便如天造地设,不可动摇”,可知其于此道之自负。又《上钱辛楣宫詹事书》云:“学诚从事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云:“惟文史校雠二事,鄙人颇涉藩篱”,皆以文史校雠之学自命。
这“文史”二字,不是指“文学和史学”。它有特殊的涵义,是实斋用来标识其学术宗旨的特殊名词,所以邵晋涵说:
“文史”字,见东方朔及司马迁传,唐宋以还,乃以论文诸家,目为文史。章君自谓引义征例出于《春秋》,而又兼礼家之辨名正物,斯为《文史通义》之宗旨尔。(《跋〈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
可见实斋所欲建立者,并非史学,而是一种文史学。这种文史学之所以成立,则依赖其校雠学的方法,故又名为“文史校雠之学”。他在《文史通义》之外,着有《校雠通义》与之并行,原因亦即在此。
四、校雠学
按:实斋之所谓校雠,与现今一般论校雠学者极为不同。通常皆以校雠为版本校勘,综合群书,比勘其文字篇籍之异同,考正其讹误,某本多一字、某本少一字、某处误夺、某处有缺衍,龂龂不已。实斋所谓校雠则不然,乃是“兼礼家辨名正物”的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之举,自以为能绍刘向、刘歆父子及郑樵之绪遗。
彼《与严冬友侍读书》自称:“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说得极为明白。其子华绂《文史通义跋》也说:“《文史通义》一书,其中倡言立议,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
这些话,都清楚地显示了《文史通义》即是运用校雠之学所得到的结果,其宗旨即在辨名正物,说明学术之源流。
其师朱筠《笥河集》卷五《怀京华及门诸子诗》第四首“章实斋副贡”有云:“欲杀吾怜总未休,甚都犹为百绸缪。冯生文史偏多恨,刘氏心裁竟莫收。燕市游来稀酒客,闽行将绝忆书楼,凭君检拂残鱼蠹,有意名山著作否?”可见在《文史通义》未出之前,朱氏已经知道他这位高足有此文史校雠之学了。实斋之书,可谓不负师门期许。
因此,以史学要籍视《文史通义》及以史家目实斋者,于此皆不能梦见。称述虽多,徒然误会其宗旨,冤杀实斋而已。更有趣的,是这些先生们往往把《校雠通义》和《文史通义》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书,不是说“其史学思想,则多表现于《文史通义》一书。至其《校雠通义》,就论甄别书籍、部次条别之道,亦即鉴别史料之法也”,就是说“《文史通义》为文化史学,《校雠通义》是学术史概论”。更甚者,则如吴天任《章实斋的史学》一书,根本不论其《校雠通义》,宣称“暂不列入本书范围”。这样论实斋,岂能得其根柢?
五、学术思想史
另一种研究章实斋的路数,是不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明实斋对史学的贡献,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把实斋之学放人当时学术发展的脉络中去看。称道他能箴砭当时崇尚经学考证的学术风气,具有思想史的意义。
最早是胡适编《实斋年谱》时,使用了新的体例,把实斋批评戴震汪中袁枚等人的话摘出抄录,认为如此,“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又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自序》)。
但胡适对于实斋攻击戴汪诸人之言辞,不甚欣赏。因为胡氏本人是拥护戴震等人的,故往往谓实斋“仍有卫道的成见,或尚含有好胜忌名的态度”。
后来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及《国学概论》则把章戴冲突的个人性格因素淡化,认为章氏之所以抨击戴震,是反对一种以戴震为代表的学风,亦即反对当时“经学即理学”,“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说法。故由章戴之异同,实斋溯而论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之异同,再溯而论朱陆之异同,提倡史学经世,谓六经皆史,排比类纂及烦琐的考证工夫,都不被承认是“著作”与“学问”。
事实上,实斋当时,已有人指他是提倡史学以对抗经学。实斋反对此说,嘉庆元年《上朱中堂世叔书》云:“议者颇讥小子攻史而强说经,以为有意争衡。此不足辩也。……小子不避狂简……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
但民国初年有一派学人,因不满于乾嘉朴学之后裔及复兴者所标榜的学风,而颇以实斋之勿同于乾嘉为借鉴,如张尔田撰《刘刻章氏遗书序》,即云实斋与汉学家相对照,有五种不同,故其书不能大显于时。
钱穆的说法,则是进一步从章戴之不同处,逆窥实斋学术的内容,说明其提出浙东学派并写《朱陆篇》的缘故。此固为思想史之研究,但也是由于钱穆对宋明理学较有好感,故能借实斋之反戴,反省到戴震所代表之学风可能存在着根本的问题。钱氏之后,余英时推阐其说,最具功力。侯外庐《乾嘉时代的汉学潮流与文化史学的抗议》一类文章,基本上也沿续了这个思路。
六、史学经世
这个思路,当然能够说明实斋提出某些说法的原因。但是,对学说之所以出现有了说明,不等于就说明了学说的内容。
而且,实斋所反对的,除了戴震之外,尚有袁枚、汪中等,嘉庆二年,《与朱少白书》论及他与洪亮吉的争辩,更是明言:“弟辨地理统部之事,为古文辞起见,不尽为辨书也。”可见批判戴震所代表之学风,能否作为他学说中的核心观点,恐怕大可商榷。他言校雠、论文章,亦非“与戴震对抗”或“以六经皆史,反对经学即理学”诸说所能涵括。
此外,把章戴对立起来看,更是容易误会实斋所谓史学经世的意义。
“史学经世”这句话,很容易令人想到致用、实用、切合当世情俗等涵义。所以钱穆便认为戴震之学是“即圣人六经而求”,“主稽古”;“实斋则称事变、称时会、称创制”,“主通今”。
这种对比是错误的,实斋所谓经世云者,绝非此义。他在《原道中》讲得非常清楚: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着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
乃是主张述而不作,据经稽古,以表章先王之道;其非通今致用、创制应时,语意甚为明显。故其云经世,乃述先王之道以训当世与后世之意。其学术型态自然也就是稽古敏求,即圣人六经而求之。
在这方面,章戴并没什么差别。他们的不同处,非一稽古一通今,而是在于实斋反对其稽古之法(如“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主张)、也反对只讲名物训诂而不探求义理的作风。从反戴震与考证学风这个角度来探论实斋之学者,在这些地方,多乏分疏,其不能知实斋也固宜!
七、洗冤录
因此,总括近百年的章实斋研究史,实斋所获者,可谓誉非其实。胡适在《章实斋年谱》出版时,曾经乐观且自豪地说:“十一年春,本书初版,国人始知章先生。”现在看来,殊不谓然:
1922年胡适《章实斋年谱》出版,到现在2021年底,国人始知章先生已被误解了一百年。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