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196窟的晚唐壁画《劳度叉斗圣变》(局部)中的《揩齿图》
牙痛是人类最常见的口腔疾病,而且远古时代就已经在折磨人类了。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遗址中,就发现了许多患有龋齿和牙周病的人骨。现代医学告诉我们,牙痛多与口腔细菌有关。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也隐约意识到牙疼是由于某种小虫子在作怪。
隋代医学家巢元方等人于7世纪初完成的《诸病源候总论》,是一部专门研究各种疾病病因及症候的中医经典著作。该书卷二九写道,牙痛的病因有两种,一种是由于“髓气不足,阳明脉虚”;另一种则是由于牙虫而引起的,“虫食于牙齿,则齿根有孔,虫居其间,又传受馀齿,亦皆疼痛”(南京中医学院校释《诸病源候总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604-605页)。书中还写道,对于第一种原因引起的牙痛,可以用针灸来治疗,但对于第二种牙痛,只能用药物把牙虫杀死,才能止住疼痛。
既然牙痛是因牙虫造成的,那么捕杀牙虫就成了治疗牙痛的关键。为此,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多种治牙虫的方法,下面略作介绍。
第一种是药物。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方》卷二二中收集了许多治牙虫的药方,其中不少药方中配有细辛。直到今天,依然可以在药店里找到含有细辛的牙痛药。不过,也有的药方显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例如书中所介绍的“鸡屎白以醋渍煮,稍稍含之瘥(chài)”(高文铸校注《外台秘要方》,华夏出版社,1993,420页)。
第二种是熏烫。《外台秘要方》卷二二收录的“杀齿虫方”是:“雄黄末,枣膏和为丸,塞牙孔中,以膏少许置齿,烧铁篦(bì)烙之,令彻热,以瘥止。”(《外台秘要方》,422页)此方想必颇为残酷,一般患者恐怕难以忍受。相比之下,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一七中所收录的方法要温和多了,“用天仙子一撮,入小口瓶内烧烟,竹筒引烟入虫孔内,熏之即死,永不发”(中国书店,1988,21页)。
第三种是针灸。元朝王国瑞在《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中写道:“风牙虫蛀夜无眠,吕细寻之痛可蠲(juān)。先用泻针然后补,方知法是至人传。”这里所说的“吕细”是穴位名,其位置“在足内踝骨肉下陷中”(李宁点校《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中医古籍出版社,1990,92页)。
第四种是巫术。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名著《千金翼方》卷一一中,推荐了几种治牙符咒,例如:“人定后,向北斗咒曰:北斗七星,三台尚书,某甲患龂,若是风龂闭门户,若是虫龂尽收取,急急如律令。再拜,三夜作。”(王勤俭等校注《千金翼方》,第二中医大学出版社,2008,254页)这个方法固然简单易行,但估计是不会有什么疗效的,最多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
第五种就是设法直接把牙虫活活捉出来,即“捉牙虫”,也有的称其为“撬牙虫”,如清末满族作家文康在《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八回中就写到,涿州的天齐庙里就有“许多撬牙虫的、卖耗子药的”。捉牙虫主要流行于民间,执业者通常为女性,被人称为“药婆”。在清朝乾隆年间王初桐所著的《奁史·术业门》中有如下文字:“药婆,今捉牙虫,卖安胎、堕胎药之类。”元末明初的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三姑六婆》中也提到了“药婆”,由此推测,捉牙虫的方法在元末就可能已经出现了。
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捉牙虫的资料很少。推测其故,大概由于此种赖以谋生的独门绝技只能私下口头传授,不能写成文字公诸于众。圈子外的人们,根本无法了解其奥妙,更无法载录。普通的学者,或许还会觉得这种司空见惯的江湖骗术根本不值得书写。倒是鸦片战争后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一些西方人,出于好奇,留下了关于捉牙虫的一些记载。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英国传教士哥伯播义(Robert Henry Cobbold)的著作。
哥伯播义是英国安立甘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名牧师,他于1848年4月到达上海后转抵浙江宁波,此后长期在此生活。1851年,哥伯播义返回英国。两年后,携夫人再次来到宁波,直到1857年才与家人一起离华返英。哥伯播义是宁波方言拼音方案的推行者之一。他除了撰写《真理摘要》等中文著作外,还出版过英文著作《中国人自画像》(Pictures of the Chinese)。此书不仅可读性极强,而且配有大量插图,形象而生动地记录了19世纪中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书中有“有效的疗法”(the Infallible Remedy)一节,专门讲述捉牙虫(图1)。

图1 哥伯播义书中的捉牙虫图
哥伯播义(图2)在书中把捉牙虫的妇女称作“女郎中”(female quacks),认为她们的特征是:小脚,发式整洁,随身携带长柄雨伞。她们不停地喊着“捉牙虫,捉牙虫”,在大街小巷中穿行。此外,如果遇到别人的暴力攻击,她们也有很强的自卫能力。哥伯播义了解到,“这些女郎中认为牙痛通常是由小小的蠕虫或蛆虫引起的;这些牙虫的巢穴就位于牙齿的根部,如果把它们从牙根赶走或劝诱出去,那么持续的疼痛就会立即停止。但如何捉拿牙虫则是其行业秘密,她们对此守口如瓶”。
当时生活在宁波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对神秘的捉牙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出现了热烈的争论。哥伯播义的一位朋友认为,这一定是骗人的把戏,因为西方医生根本没有在牙床或牙齿里发现过这样的虫子。但英国领事馆的一位外交官却对捉牙虫深信不疑,因为他曾亲眼目睹过。哥伯播义本人对此半信半疑。他说:“在宁波一带约有两千位妇女以捉牙虫为业,如果都是江湖骗术的话,她们如何谋生呢?人们会愚蠢到没病也要去找她们看病吗?如果捉牙虫没有任何疗效,人们会傻傻地掏钱给她们吗?”

图2 哥伯播义像
生活在宁波的一些西方人也曾体验过捉牙虫。有位西方女子牙痛难忍,在宁波的英国医生对此束手无策。病急乱投医,她后来请来了捉牙虫的女郎中,结果很快把牙痛治好了。在场的一位西方船长出于好奇,谎称也患了牙痛。女郎中居然从这位船长的口中捉出了大约二十条虫子。此外,为了防止女郎中们串通一气,西方人曾要求女郎中单独一人在房间里徒手捕捉牙虫。出人意料的是,女郎中还是从病人口中捉出了牙虫。这种治疗方法如此奇特而神秘,促使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特地搜集了一些牙虫标本,将它们小心翼翼地保存在酒精中,邮寄到美国的博物馆去展览。
哥伯播义最后决定自己也去试试。一天,当哥伯播义与几个西方人在中国先生指导下学习中文时,听到街上有人在喊“捉牙虫”,于是佯装牙痛,将女郎中请进屋里,并且答应付给她优厚的报酬:每一条虫子三便士。他们先请她为中国先生捉眼虫。只见“女郎中从头发上拔下一根发亮的钢针,再让人从厨房拿来一根筷子。她一手捏钢针,一手握筷子,两手交替摆弄,用钢针从中国先生的眼中挑出了一条像蛆虫那样的大肥虫。接着,那位女郎中又从哥伯播义一个朋友的口中捉出两条牙虫。最后,她从哥伯播义嘴里捉出一条牙虫。当哥伯播义等人要求继续为屋里的其他人捉牙虫时,被她婉拒了。哥伯播义等人仔细观察了捉牙虫的整个过程,但看不出任何破绽。不过,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使哥伯播义产生了怀疑。哥伯播义清楚地记得,这个女郎中总共捉出了4条虫子。可是到了算钱时,却发现杯子里有6条虫子。那个女郎中争辩说,有两次她是同时捉出了一对虫子,只是周围的人没有看清楚。
这个女郎中拿着钱离开后,无论哥伯播义他们如何邀请,再也没有一位女郎中愿意为他们行医了,可能是怕露了马脚。不久,哥伯播义等人遇上了一位双目快要失明的老妇人,而她原先竟然是从事捉牙虫的女郎中!这件事使哥伯播义彻底明白,所谓的捉牙虫原来是一种骗术。他们赶快写信到美国,让博物馆不要展出那些已经寄出的牙虫。
哥伯播义说,他在浙江省见到过不少捉牙虫的女郎中,但“不知道中国其他地方是否也有这种人”。其实,这种治牙方法在古代中国的不少地方都有。例如,至少在19世纪30年代,广州就有一位名叫关联昌(别号“庭呱”)的画师就绘过一幅题为“医牙”的线描画(黄时鉴、沙进《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59页)。画中的女子右手抓着写有“牙科”的牌子,左手扛着一柄长伞,伞顶上挂有“凤阳精捉牙虫”的招牌(图3)。据此推断,凤阳“药婆”的手艺当属一流,或者说来自凤阳的“药婆”牌。不过,宁波方言歌谣中有“阿婆箝牌捉牙虫”的句子,可见“药婆”扛着招牌是很普遍的。关联昌的这幅画属于外销画,是专门出售到西方国家去的,这说明当时一些西方人也和哥伯播义一样对捉牙虫充满了好奇。

图3 关联昌绘外销画中捉牙虫的女郎中
斗转星移,时移世易。今天的中国,再也看不到以捉牙虫为业的药婆了,但我们不应当忘却这样一群特殊的“专业妇女”。因为在她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古人为医治牙痛所做的努力,可以看到古代妇女生活的艰辛与苦涩,还可以看到中国文化阴暗面中欺骗的因素。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 2012年第8期“文化史知识”栏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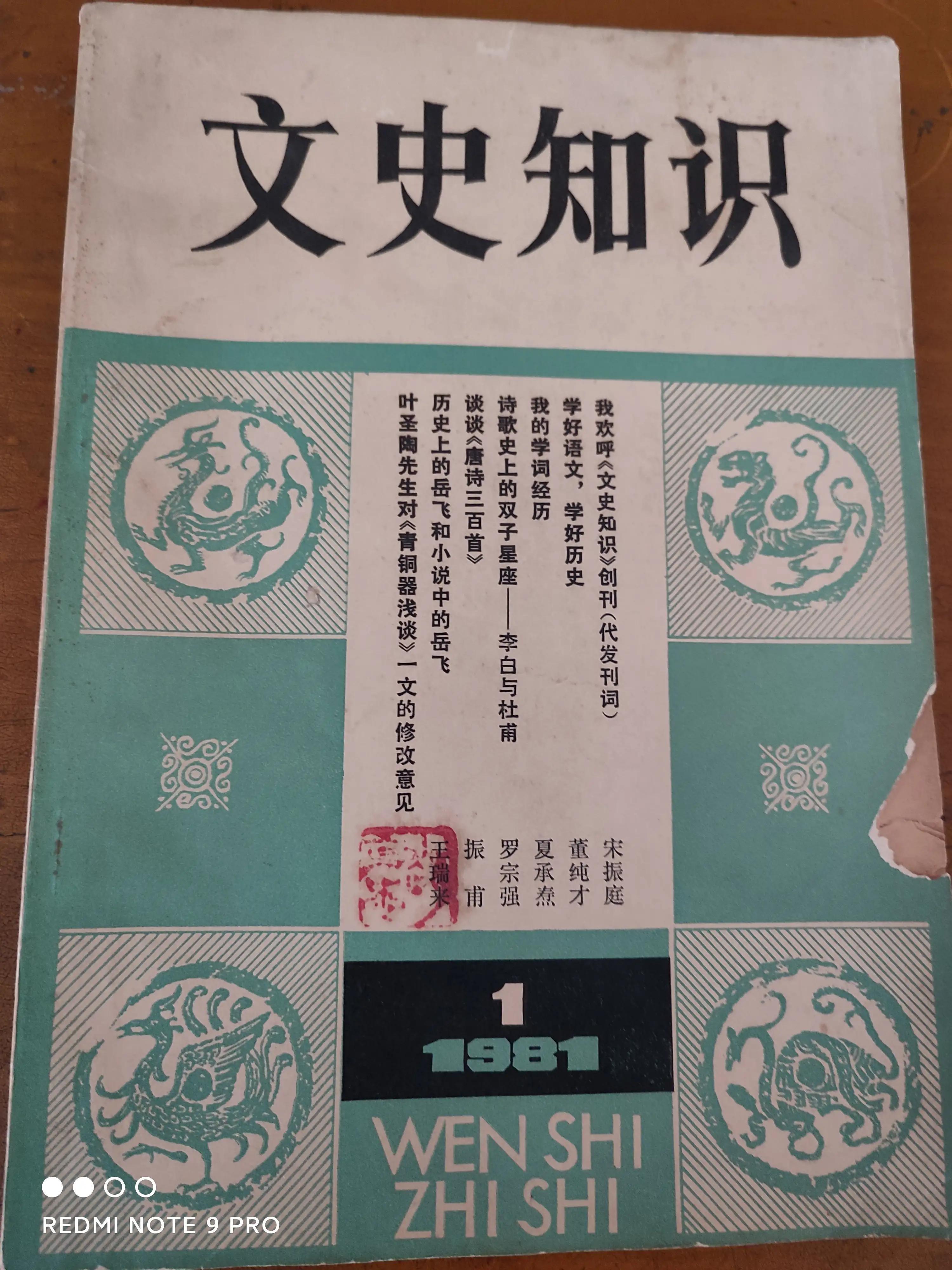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