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是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优生学家和教育家,他最早提出优生学。他与梅贻琦、叶企孙、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在二十世纪初成长起来的一代巨匠之中,潘光旦独树一帜、卓尔不群。在文人相轻的传统之下,那一代的学者们,却都非常欣赏潘光旦。徐志摩称潘光旦为潘仙,意味着他与八仙之一铁拐李的神似。梁实秋认为潘光旦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在亦师亦友的费孝通眼中,潘光旦是一部活字典,是真正的人类学家。冰心钦佩他宠辱不惊的风骨,称其为“被遮蔽的先知”,“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他和闻一多也是好朋友,连闻一多的名字都是他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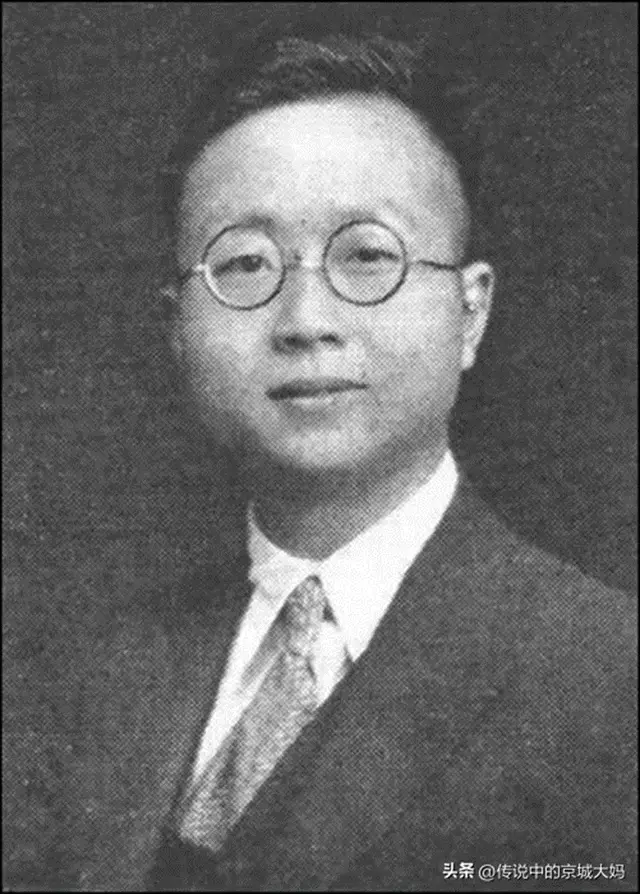
潘光旦是上海人,在清华求学时的一次体育课上,因跳高受伤导致右腿被截肢,但他依然能以自身出类拔萃的成绩赢得推荐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民学院等校任教。是老清华社会学系的灵魂人物。
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潘光旦爱书是出了名的,只要手头稍有余钱就会去买书。1926 年他从美国回来时,为了买《达尔文全集》,下船时身上仅剩一元钱。他的藏书非常丰富,朋友们常上门借书,甚至周恩来总理在研究中印边境问题时为了准确掌握边境史料,也曾借用他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潘光旦经常说的一句话:“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 潘光旦晚年眼睛极度近视,但除了吃饭睡觉,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眼睛基本是贴在书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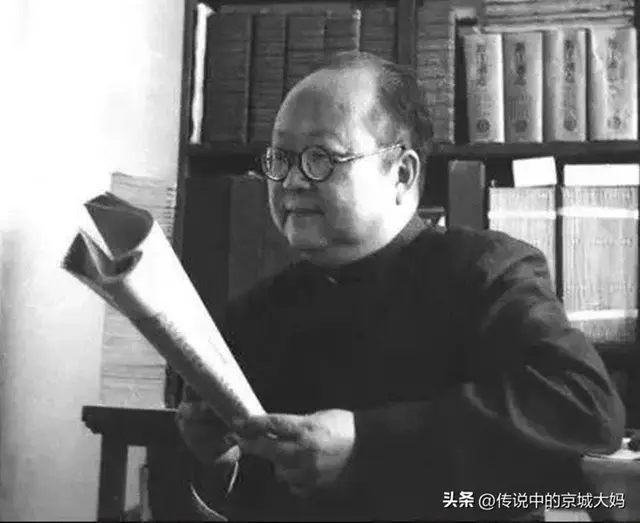
潘光旦出生于江苏宝山(现属上海)的书香世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不仅中文功底极好,英文的造诣更是深厚,可以将《英汉综合大词典》 背得滚瓜烂熟。他兴趣广泛且学有所成,在美国留学期间修过生物学,心理学、动物学、遗传学,古生物学、优生学、人类学、 单细胞生物学、内分泌学等。与此同时,他对文学和哲学也抱有浓厚的兴趣,可以真正称之为“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打通文理”。在清华读书时,他在学业上永远是第一名。梁启超是潘光旦的国学老师,在潘光旦的一篇论文后面评价道:“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能让梁大师如此称赞之人,能是普通平凡的人吗?
在教育学方面,潘光旦倡导通才教育,致力“教人做人”,强调人格、培养和通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系统教育理论。他说:“大学的宗旨不仅在教人做人、做专家,而且要做士,即承担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他兼任过清华教务长、 秘书长、图书馆长,在西南联大时担任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研究和讲授过心理学、优生学、 遗传学、进化论、家庭问题、人才学、谱牒学、 中国社会思想史、西洋社会思想史、性心理学、 教育学、民族学等(实在是令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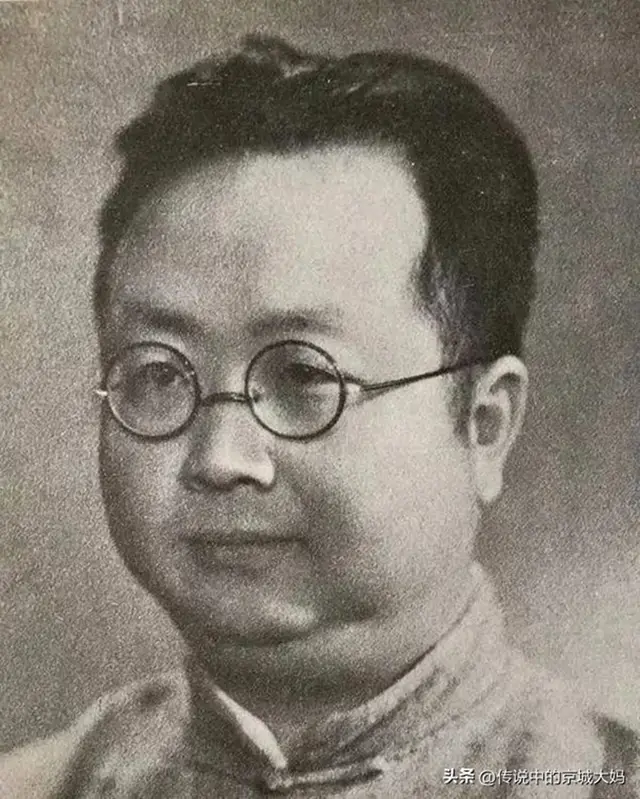
作为学者,潘光旦著述丰富,内容涉及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等。他的著作《冯小青》,译著《性的道德》、《性的教育》和《性心理学》, 树立了性心理学本土化的四块丰碑。即使在抗战期间,他也出版了《人文史观》、《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优生与挑战》、《自由之路》等著作。
1952年,他到中央民族学院后,开始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为了考证“土家族是不是单一民族”这个课题,他拄着双拐亲自到湖南、湖北西部山区进行考察研究。 一丝不苟地走完了18 个县市、14000 公里行程并写出了《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从学术角度上确认了土家族单一民族的事实。
虽然断腿,但潘光旦有一份纯真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因跳高受伤致残回乡休养时,原已订婚的女方解除了婚约。他的一位表亲赵瑞云钦慕他的人品学问,与他结成了连理。赵瑞云聪颖贤惠,夫妻情深,相濡以沫。在西南联大期间,生活困苦。为了填饱肚子,她与梅贻琦的夫人一起做糕点到集市上去卖。她们将这种糕点称作 “定胜糕”,取抗战必胜之意。

1957年潘光旦被打为“右派”,饱受折磨。赵瑞云在担忧中于1958年离他而去。 1966年潘光旦被骂“流氓教授”, 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批斗、抄家,被命令去清华园除草。他随身带一条小凳,但被红卫兵踢飞,只能坐在冰凉的地上拔草。由于长时期的缺衣少食和超强劳动,已经67岁的身体渐渐出现了问题。小便不通腹胀如鼓,却不得医治,逐渐发展为尿毒症。1967年6月10日晚,潘光旦在学生费孝通怀里离世,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费孝通送潘光旦走过了人生的最后旅途。但费孝通说:“潘先生没有抱怨”,因为“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暑期创作大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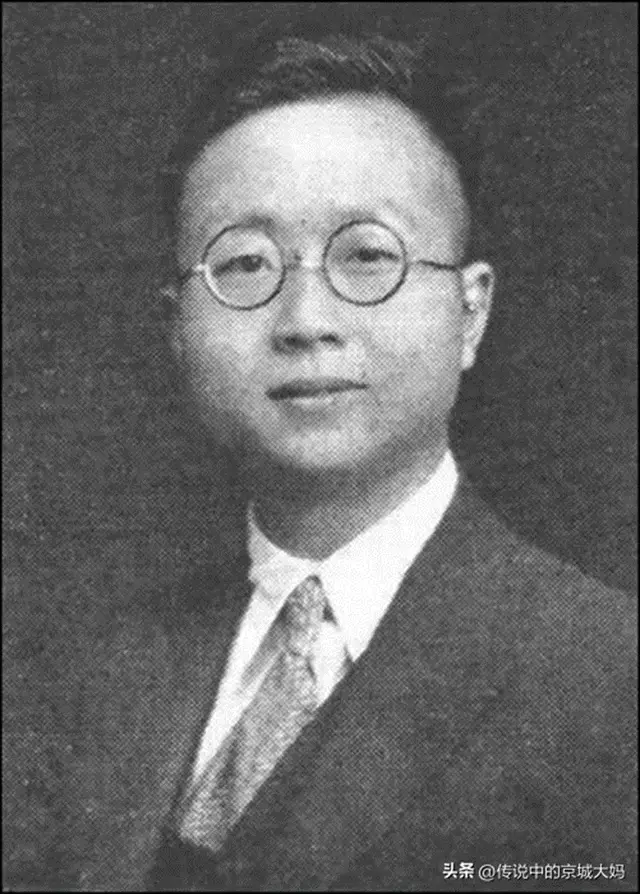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