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
作家叶兆言在散文集《群莺乱飞》中回忆了许多与作家师友的往事,夏丏尊、高晓声、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等等,他想为他们留下些文字,不惟著书立说,而是通过这些言语,完成和那个年代的对话。
今天夜读,从叶兆言的视角,谈论高晓声与汪曾祺的文学成就,一代文学之后,后来的新人们要思考的则是,如何从前辈们的树荫中走出来,另辟蹊径,披肝沥胆。

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版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出自南北朝时南朝人丘迟写给大将陈伯之的劝降信。在这篇名为《与陈伯之书》的信中,丘迟前文议理,后文动情,这四句更是以寥寥数笔,勾起了陈伯之对江南故园乡景的回忆与思念。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是叶兆言文史散文集其中两本书的书名。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叶兆言将这八个字用在这里可谓别具匠心。思绪纷飞,如同早春散飞的百鸟,扑簌着翅膀,将回忆伸向远方。
叶家是书香世家。叶兆言和他的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女儿叶子一门四代皆为作家,母亲是“锡剧皇后”,伯父伯母亦皆跻身文坛。如此家世,叶兆言在人前却鲜有提及。身为一个独立的作家,是不大愿意被人贴上背靠祖荫的标签的。在一档访谈节目中,叶兆言也曾就此笑谈,不希望总被拿来与祖父作比较。同住南京的作家苏童曾评价他,沉稳端正,儒雅温和,有谦谦君子之风。

叶兆言与祖父叶圣陶
叶兆言的父亲叶至诚是不希望他走上文学的道路的。然而事与愿违。《群莺乱飞》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叶兆言年少时在深夜偷偷翻看外国文学,忘我和动情之时,不免为其中的情节动情感怀。父亲叶至诚已有所觉,但想必是有感于叶兆言的这份热爱,曾经的禁令渐渐成了一纸空文。
眼界的开拓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阅读外国文学初时或许只是好奇,渐渐地感同身受。这对一个醉心文学的少年,实在是莫大的眷顾。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长期对外国文学的浸淫,让叶兆言对作品的品位、立意与认知更为全面。多年后已跻身作家并享有盛誉的他,重读当年读过的作品,见解与评点早已今非昔比。只是重读的意义非惟如此。如同我们重听或翻唱一首老歌,每个跳动的音符背后,都能令人忆起曾经的岁月,叶兆言的重读,是对自己走过的文学之路的一次追忆。
毕竟对作家而言,人生与阅读一旦交织,便再也无法回避。
描写现当代文人的作品不少,但这些文字中的名人学者似乎显得有些高高在上。然而《群莺乱飞》中我们见到的那些文人,更多了些烟火气。和叶家交好的文坛名人着实不少,真可以算得上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近水楼台先得月,身为在这样优渥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叶兆言耳濡目染,很难不对家中的这些客人作近距离的观察。
叶兆言看着他们从对文学充满热情的壮年,到遭逢变故,外貌到气质都与原先相去甚远,唯有内心还强留着对文学的热爱与初心。而他自己也从懵懂幼稚的少年,从一个旁观者,渐渐地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群莺乱飞》里的文人们不少是叶家的挚友与座上宾,也是叶兆言文学路上的导师与前辈。游历文字其中,仿佛听一个老先生在桌前冲着一杯热茶,神色平和的细数着家中寻常的历史掌故,偶尔为尊者讳,细节之处不免模糊。他嘴角边泛起温和的微笑,让听者不时出神,以为这确实只是午后一次再普通不过的茶话会,而忘却了对方正在谈论着的人们,是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能够留下名字的巨匠:
夏丏尊、高晓声、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等等。
他想为他们留下些文字,不惟著书立说,而是通过这些言语,完成和那个年代的对话。
——《群莺乱飞》:与过去对话,回忆里的,是半部中国文人的当代史,文 / 陈德丰
郴江幸自绕郴山
文 / 叶兆言,有删节
林斤澜是父亲的挚友,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江苏作家和浙江作家相比,现代是浙江强,当代是江苏强。现代是祖父那一辈,当代是父亲这一辈。现代作家中,浙江有鲁迅,有茅盾,有郁达夫,有艾青,都是高山仰止的顶级人物,自然无法比拟。到当代作家这一拨,按照林斤澜的看法,江苏有高晓声,有方之,有陆文夫,还有汪曾祺,情况完全不一样。
第一次见到高晓声,是考上大学那年,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高晓声和父亲是老朋友,与方之、陆文夫都是难兄难弟,一晃二十年没见过面。乡音未改,鬓毛已衰,土得让人没法形容,农民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农民形象。这是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高晓声形迹可疑地转悠了一圈,人便没有踪影,很快又出现,已拿着两篇手稿,是《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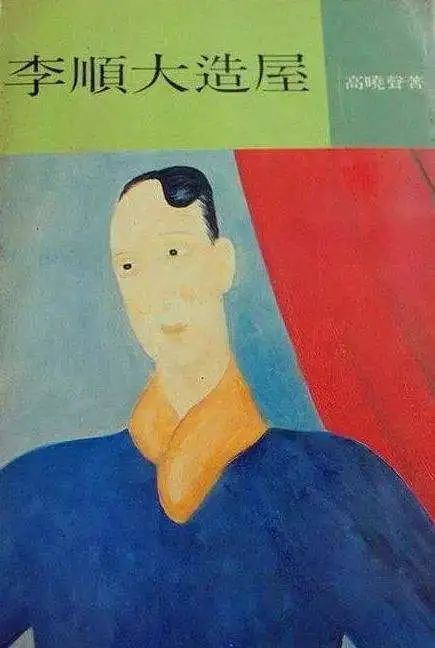
高晓声开始给人的印象并不心高气傲,他很虚心,虚心请老朋友指教,也请小辈提意见。我们当时正在忙一本民间刊物《人间》,对他的小说没太大兴趣。最叫好的是父亲,读了十分激动,津津乐道,说自己去《雨花》当副主编,手头有《李顺大造屋》和方之的《南丰二苗》,就跟揣了两颗手榴弹上战场一样。《李顺大造屋》打响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后话,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啰唆。话是在吃饭桌上说的,大家手里还端着酒杯,高晓声追着问什么地方啰唆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了。
仔细琢磨高晓声的小说,不难发现,他作品中为农民说的好话,远不如说农民的坏话多。农民的代言人开始拆自己的台,从陈奂生开始,农民成了讥笑对象。当然,这农民是打了引号的,因为农民其实就是人民,就是我们自己。中国知识阶级总处于尴尬之中,在对农民的态度上,嘴上说与实际做,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定式。换句话说,我们始终态度暧昧,一方面,农民被充分理想化了,缺点被视而不见,农民的淳朴被当作讴歌对象,另一方面,又把农民魔鬼化了,谁也不愿意去当农民。结果人生所做的一切努力,好像都是为了实现不再做农民这个理想,甚至为农民说话,也难免项庄起舞,意在沛公。
父亲一直遗憾没有以最快速度,将汪曾祺的《异秉》发表在《雨花》上。记得当时不断听到父亲和高晓声议论,说这篇小说写得如何好。未能即时发表的原因很复杂,结果汪另一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上抢了先手。从写作时间看,《异秉》在前,《受戒》在后。以发表时间而论,《受戒》在前,《异秉》在后。


和高晓声迅速走红不同,汪曾祺的小说有个明显的慢热过程。高晓声连续获得两届全国奖,而且排名很靠前,一举成名天下知。汪曾祺却是先折服了作家同行,在圈子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叫好,然后稳扎稳打,逐渐大红大紫。客观地说,在八十年代初期,高晓声名气大,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汪曾祺声望高。这两个人在八十年代不期相遇,难免棋逢对手,英雄相惜。高晓声一度对汪的评价极高,在我的印象中,绝对是汪成名之前,有一次高晓声甚至对我说,汪的小说代表了国际水平。正是因为他强烈推荐,《异秉》还是在手稿期间,我就看了好几遍。
有一次是八十年代的扬州街头,当时父亲也在场,还有上海的黄裳先生,我们一起吃早餐,站在一家小铺子前等候三丁包子。别人都坐了下来,只有我和汪曾祺站在热气腾腾的蒸笼屉子前等候。我突然谈起了自己对他小说的看法,说别人都说他的小说像沈从文,可是我读着,更能读出废名小说的味道。他听了我的话,颇有些吃惊,含糊其词地哼了一声,然后就沉默了,脸上明显有些不高兴。我当时年轻气盛,刚走出大学校门,虽然意识到他不高兴了,仍然具体地比较着废名和沈从文的异同,说沈从文的句式像《水经注》,而废名却有些像明朝的竟陵派,然后捉贼追赃,进一步地说出汪曾祺如何像废名。蒸笼屉子里的三丁包子迟迟不出来,我口无遮拦地继续说着,说着说着,汪曾祺终于开口了:“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然而——”他显然已想好该怎么对我说,偏偏这时候,三丁包子好了,他刚要长篇大论,我们交牌子的交牌子,拿三丁包的拿三丁包,话题就此再也没有继续。


沈从文(左)、废名(右)
我自己也成为作家以后,才知道汪曾祺当时为什么不高兴。一个作家未必愿意别人说他像谁,像并不是个好的赞美词,作家永远独一无二的好。汪曾祺喜欢说他与沈从文的关系,西南联大时期,汪是沈从文的学生,在写作上曾接受过指导。八十年代也是沈从文热兴起的时候,沈门嫡传是一块金字招牌,汪曾祺心气很高,显然不屑于以此作为自己的包装材料。平心而论,汪小说中努力想摆脱的,恰恰是老师沈从文的某种影响。在语言上,汪曾祺显得更精致,更峭拔,更险峻,更喜欢使才,这种趋向毫无疑问地接近了废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鲁迅先生谈起废名时,曾说他有一种“着意低徊,顾影自怜”的情结,汪曾祺也提到过废名的这种自恋,而且是以一种批评态度。废名的名声远不及沈从文,汪谈到一些文学现象,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明白,在习惯上,提到更多的还是沈从文,因为熟悉程度上来看,毕竟自己老师更近一点。事实上,说他像沈从文听了都不一定高兴,说他像不如沈从文的废名,当然更不高兴。
高晓声和汪曾祺都是我敬重的前辈,是我文学上的引路人。八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我在大学里苦读,不断地写些东西,对自己的未来一直没什么明确目的。是高晓声和汪曾祺这样的作家,活生生地影响了我,让我跃跃欲试,但是也正是他们,让我对是否应该去当作家产生怀疑。按照我的看法,高和汪能成为优秀作家,都是因为具备了特殊素质,他们都是有异秉的人,高晓声绝顶聪明,汪曾祺才华横溢,而我恰恰在这两方面都严重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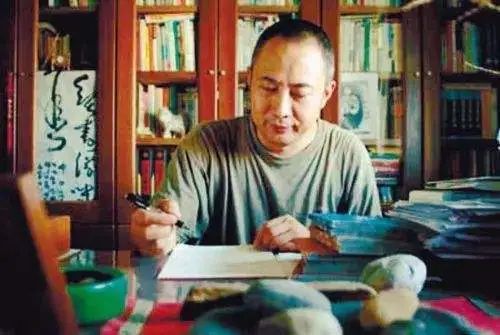
叶兆言
我忘不了高晓声告诉的一些小经验,他告诫我写文章,千万不能走气,说废话没有关系,但是不要一路走题,写文章是用气筒打气,要不停地加压,走题仿佛轮胎上戳了些小孔,这样的文章看上去永远瘪塌塌的,没有一点精神,而文章与人一样,靠的就是精神。高晓声还教会我如何面对寂寞,很长时间,我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写的小说一篇也发表不了,他却认为这是好事,说你只要能够坚持,一旦成功,抽屉里的积稿便会一抢而空。对于小说应该怎么写,高晓声对我的指导,甚至比父亲的教诲还多。同样,虽然没有接受过汪曾祺的具体辅导,但汪文字中洋溢的那种特殊才华,那种惊世骇俗的奇异之气,一度成为我刻意的学习样板。我对汪曾祺的文体走火入魔,曾经仔细揣摩,反复钻研,作为他的私淑弟子,我至今仍然认为《异秉》是汪曾祺最好的小说。

丰子恺 / 画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凡是读过《异秉》的人,都免不了去想,去思索,琢磨小说中王二的“异秉”究竟在什么地方。汪曾祺借王二之口,幽了一默,说他的奇异之处,只是“大小解分清”。什么叫大小解分清,王二进一步解释说:
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
这是王二随手扔的一块香蕉皮,顿时很多人中计,滑了一个大跟头,小说结尾时,厕所里已人满为患,大家都去抢占茅坑,研究自己是否有“异秉”。我喋喋不休提起《异秉》,喜欢这篇小说之外,更觉得可以用它说事。无论是高晓声的聪明,还是汪曾祺的才华,都十分难得,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异秉,是镜中花,是水底月,无迹可寻,可遇不可求。后人如果不明白,希望通过模仿,学些聪明和才华的皮毛,驾轻车走熟路,野心勃勃到文坛上去闯荡,去捞些什么,注定只能铩羽而归。高晓声和汪曾祺获得了应有地位,后来作家如果不能从他们的树荫中走出来,不另辟蹊径,不披肝沥胆,文学的前景就没什么乐观。换句话说,当代文学如果不够繁华,是否与太多的聪明和才华有关。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