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又称家乘、宗谱、族谱、谱牒等等。家谱记载的是本族历史沿革、世系繁衍、居地迁徙、科举仕宦、传记艺文、族规家法等等,清人章学诚曾言:“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生活于五缘文化(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人际关系下的国人似乎都很难回避家谱之事,于此可见家谱的重要性。虽则寻根问祖之心人皆有之,但吾家是否有家谱?此问题余幼时从未想过,即使到了中年,余早已步入史坛,从事学术研究,对家谱的了解似应比一般人更进了一层,但一则余诸事繁多,二则余身在都市,与生活在农村聚族而居的人不同,因周围亲戚不多,亦较少往来,故相当缺乏家族的认同感。三则家严、家慈又从未向我提起过家谱之事,甚至连家族及祖父母之事也未提及,如此一来,余脑海中的家谱意识更为淡漠,甚至丝毫不存在了。
家慈去世之后,余二兄花费不少精力纂修《忆父母亲》,家兄奔走于故旧亲戚之中,通过走访与搜集有关资料,才完成了此册。然此册以回忆先严先慈之事为主,至于祖考的源流与世系,俱呈碎片,雪泥鸿爪,渺茫难稽。此册中的《浙江归安菱湖朱氏家族简谱》弥足珍贵,是寻觅祖先最重要的线索,但《简谱》仅排列了莲庄公以降至余子姪辈的世系,至于莲庄公之上的世系,均缺而无闻,仅知思凯公为归安菱塘朱氏的始迁祖,且思凯公的名讳也不知晓。吾兄所撰的《忆父母亲》极为重要,虽称不上是家谱,但勾起了吾家对家谱之事的重视,余兄亦有意在此基础上完成修谱之事,但余家之谱牒究在何处?茫茫神州大地,何处寻觅。据悉,上海图书馆收藏家谱较为齐全(经著名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顾廷龙先生在“文革”中的抢救,目前,上图的家谱数量已达三万余种,近三十万册,约占存世的中国家谱总数的三分之一)。余兄得知这一情况后,即求助其就读上海中学时的老同学,时任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的王鹤鸣,王鹤鸣先生据称是国内较为著名的谱牒学专家,其有关家谱研究的成果甚多。但王鹤鸣告知上图并无吾族之谱牒,此事最终还是无果。所谓木本水源,若不知余家之谱牒究在何处,又何谈续修家乘之事。故之后数年间,修谱之事再也无人提及。
毫无疑问,《浮生记》的发现是吾家宗谱得以续修最关健的要素。《浮生记》佚失已久,余和家族成员素不知晓有此书,余弟子王光乾[1]于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就职于上海嘉定博物馆,他在整理湖州地方志时,发现了归安乡绅朱潼的《浮生记》,因我曾与他简单聊起过我的家世,故他知晓朱士林是吾之伯祖父,朱士元是吾大父,而《浮生记》记载朱潼有子曰士林、士元,故朱潼为吾曾祖父则毋庸置疑也。
王光乾发现《浮生记》后立即告知,余欣喜至极。然此书仅藏于杭州市图书馆,为朱潼手稿本。按规定,孤本古籍不得外借及复印,故余十分焦急。余本打算亲自赴杭州图书馆,然余同该馆素无联系,众所周知,当今社会办事难,若无熟人暗通款曲,很难成功。所以,余改变主意,与在学术会议上结识的朋友——杭州师范大学黄婉峰教授联系。此事得到黄婉峰先生的大力襄助,她遣弟子去杭图古籍部,将《浮生记》全文用手机拍摄下来,拍摄的图文非常清晰,然后又用电脑传送给我。《浮生记》失而复得,重返吾家,是余家族史上的一件大事。
《浮生记》到手后,余立即仔细拜读,发现《浮生记》內容极为丰富,其中的史料价值相当高。它不仅是朱潼个人的年谱,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了解清代地方的幕宾(俗称师爷)制度,了解幕宾是如何襄助清代府县守令等地方官员掌管钱谷、刑名等政事。朱潼后来又得到东阁大学士、恭亲王奕岳父桂良的举荐,由幕宾而入仕途,担任江西、湖南等多地的知县,他以亲身的经历,叙述了自己在任知县时是如何了解当地的民风习俗,以及如何处理案件、催交赋税、劝课农桑,整治河道、平息教案、续修县志、修葺文武庙等事。总之,《浮生记》相当充分地反映了清王朝最基层的官员——县令如何治理地方的状况。故此书不仅是归安朱氏家族的重要资料,且可窥斑见豹,对清代地方政府幕宾制度、家族封貤制度、府县级行政及司法、赋税役法制度等作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余对《浮生记》充分了解之后,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即认为《浮生记》的作用应该扩大,它不应仅仅局限于在余之家族中传播,而应作为第一手史料,在学术期刊上正式发表,以供清代地方史研究者使用。于是余即对《浮生记》作整理与校点。这次校点即以杭州市图书馆馆藏朱潼手稿本为底本,谨按年谱的格式,依年、月、四季的时间顺序划分段落,并于年号后用括号附上公元纪年。文中的异体字,考虑到今人阅读的方便,作了更改。
校点之后,余即考虑在何种期刊上发表。《历史档案》是国内享有盛誉的中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而且主要刊载有关档案史料和论文,并以明清时期内容为主。这完全符合《浮生记》的投稿方向,于是我即将《浮生记》投往《历史档案》。果不出吾之所料,不久之后,余即收到《历史档案》编辑部的回复,告之《浮生记》已被录用,但因该手稿为杭州市图书馆所收藏,因涉及版权问题,故须杭州市图书馆出示证明,才能在《历史档案》上刊用。余意识到,由杭图出证明难度颇大,当初借阅,都是用了非常手段,如今公开发表,他们定会从中作梗。然而我并不死心,我想若有人情关系疏通杭图,出证明抑或有可能。故而余通过熟人,托了浙江省社科院与地方志办公室的有关领导,试图和杭州图书馆疏通关系。但杭图的负责人要我先拿出吾家与朱潼关系的证明,[2]然而朱潼的时代哪里有身份证或户口簿之类的物件,即使有,他是清代道光朝人,与今相隔将近二百年,许多事情早已是物是人非。何况余还是因发现了《浮生记》,方知朱潼是余曾祖父,这才认祖归宗的。
为了避免口舌之争,余决定不再与杭图打交道,如此一来,《浮生记》已不可能在《历史档案》上刊发。《历史档案》这条路走不通,余必须将《浮生记》另投他刊。起初,余打算放下身段,将《浮生记》投往地方办的低端刊物,因莲庄公为湖州归安人,故余欲将《浮生记》投往《湖州文史资料》,但因此刊似不定期,亦不知交给何人?故此事也无结果。余又托人将此稿投往《明清档案》,不久,此人告之,此稿拟将刊用,但后来编辑部迟迟不见回复,估计,事不偕矣!
因祸得福,《浮生记》最后投往《近代史资料》,并被刊用。《近代史资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54年创办,专门刊载中国近代史文献资料的学术刊物。近五十年来,该刊所载史料深受国内外史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为国内外史学研究者所经常引用。其实,我对该刊还是比较熟悉的,只是顾虑该刊是近代史研究的核心期刊,门坎较高,而《浮生记》的作者知名度较低,其内容也仅是清代基层官员的个人年谱,担心享有史学界盛誉的高端刊物《近代史资料》看不上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自订年谱。倒是王光乾兄颇有勇气,一再鼓动我向此刊投稿。出乎意料的是,余投稿不久,即得到《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立即刊用的通知,因我事先向编辑说明,《浮生记》原件为吾家之所藏,故避开了杭州图书馆的羁绊。令人欣慰是余的投稿过程虽然比较曲折,但最终的结果却十分圆满。
《浮生记》刊于2018年四月出版的《近代史资料》总第137期,而且是该刊的首篇,置于第二篇《锡良函稿》之前。需要说明的是:锡良是晚清名臣,官居四川总督,钦差大臣,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的事务,兼任热河都统,是晚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结果他的文稿却排在莲庄公的《浮生记》之后。于此可见,《浮生记》确是极富史料价值的历史文献,余之前的担心顾虑是多余的。《近代史资料》的编辑不论历史人物地位之高低,而以所撰之文学术价值之高低来排列次序,其史识卓越,令余钦佩不已!
《浮生记》虽然发现并公开发表,但并不等于找到了家谱。根据《浮生记》的记载,仅知晓朱潼是吾辈之曾祖父,吾族之先祖思凯公自明洪武时迁至菱湖镇,自此吾族遂世居于此,思凯公则是归安菱塘的始迁祖也。我满心希望《浮生记》能提到族谱之事,但其中只字未提,故吾宗是否有谱牒,其谱在哪里?仍然是个谜。
去秋吾腰部做了大手术,术后,医嘱须静卧数月。余卧床时,首先忍着腰部的疼痛在病榻上撰写了《晋武帝传》跋。之后,又再次校对《晋武帝传》的清样稿。书稿之事完成后,我不甘寂寞,在病床上反复思考家谱之事。忽然闪过一念,根据菱湖朱氏以及思凯公的线索,何不在百度上搜寻,结果发现湖州菱湖朱氏有一支的始迁祖为元人朱震寰,修谱人朱绍基,堂号:澹远堂,清嘉庆年修谱。朱震寰与朱思凯并非一人,可见此非余族之谱也。
余心有不甘,继续在网上搜寻,偶然发现了有菱湖始迁祖:(明)朱思凯的族谱图片。
然而吾于网上搜索的水平有限,已无法再深入下去,探究族谱源流。余只得求助于王光乾兄,在他的同事林介宇的帮助下,很快得到了确切的信息。《菱湖朱氏族谱》为刻本,共分四册,堂号:诚敬堂。茶院公朱环为婺源始迁祖;思凯公朱永嘉为菱塘始迁祖。菱湖朱氏大概在历史上有二次修谱,第一次是清道光二年(1822),由朱希孔纂修。第二次为清光绪二年(1876),由朱士纯等编修。《菱湖朱氏族谱》现为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收藏。《菱湖朱氏族谱》有插图数十幅,朱氏为菱塘望族,在菱塘现仍存有朱氏族祠、墓田、书院、故宅等遗址。菱塘朱氏在明清二代有若干人中进士、举人、秀才、副贡、拔贡等。有清一代任地方官多人,计有道台、知府、知县、教授等。朱氏婚配之女,有多人称太君、夫人、宜人、孺人、安人。菱湖朱氏世代耕读,为书香门第,吾祖辈多人为循吏而兼醇儒也。且朱氏族中也有赐进士出身,如同左文襄公,宗棠也。(清)孙志熊所纂修《光绪菱湖镇志》(上海书店1992年版)亦有菱湖朱氏的记载。
余虽然获悉了吾家有族谱的信息,但必须拿到原件,至少是复印件,此事才算真正落实。但族谱现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如何才能获得,看来难度也不小。幸亏有林介宇兄出手大力相助,由于当今社会科技的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化时代。林介宇又是电脑高手,故他从有关的网站上下载了《菱塘朱氏族谱》。当我前往嘉定拿到吾家族谱时,不由心中感慨万千,寻寻觅觅数十年,苍天有眼,终于不负余之苦心孤诣,散佚百余年的族谱失而复得,于大洋彼岸重返吾族,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如今余与兄长等及子孙辈复祖归宗,诚一大喜事矣!吾有意以余生之力赓续菱塘朱氏谱牒,此可为朱氏门第传承香火血脉。谱若成,虽谈不上是什么不朽之事功,但至少亦可吿慰于祖考,名垂于菱湖朱氏后裔,树功立德也。
吾虽欲续谱,但如何续?心中并无章法。众所周知,凡宗族历经数十代之后,分房散支,人口繁衍,若要修谱,则必举全族之力而为之,难道仅凭蝼蚁之力、一己之身修谱吗?余岂不是太自不量力了。所以余打算在修谱之前,回旧籍祭扫祖坟,认祖归宗,并顺便调研走访,了解一下菱湖镇上究竟还有多少思凯公之后裔?若有,他们手中有族谱,抑或残卷吗?如果能找到同族之人,一则可叙同宗同族之情,二则可商量联手赓续朱氏族谱之事。然而菱湖虽为祖籍,于余而言,人地生疏,从未去过,所以故里的情况吾一无所知。因此余打算在去菱湖之前,先寻觅一位熟稔当地乡风习俗与历史掌故之人,请他接待陪同并协助寻找思凯公之后裔,但要办成此事决不容易。
慈溪图书馆馆长余巨平先生是余之旧友,为人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他闻听此事后,先是联系了湖州图书馆的费俊康先生,然后又通过费先生找到了菱湖本土历史文化资深学者李恵民。[3]余从网上获悉,李惠民是土生土长的菱湖人,他对当地的乡风民俗,历史掌故、地理环境、名门望族、方志谱牒等旧事了如指掌,而且他还是最新版的《菱湖镇志》(昆仑出版社2009年版)的主编。可见,李先生对菱湖镇古往今来的历史了如指掌,是菱湖镇的一部活辞典。他正是余期待已久、努力寻找的人物!余欣喜万分,随即与李惠民通了电话,并在手机上与他建立了微信关系。李惠民在电话中告知了诸多菱湖朱氏的信息,并允诺陪余下乡走访一些朱氏族人,又问是否让湖州图书馆的费俊康先生参与?余自然乐成其事,并期待早日赴菱塘,与李先生当面叙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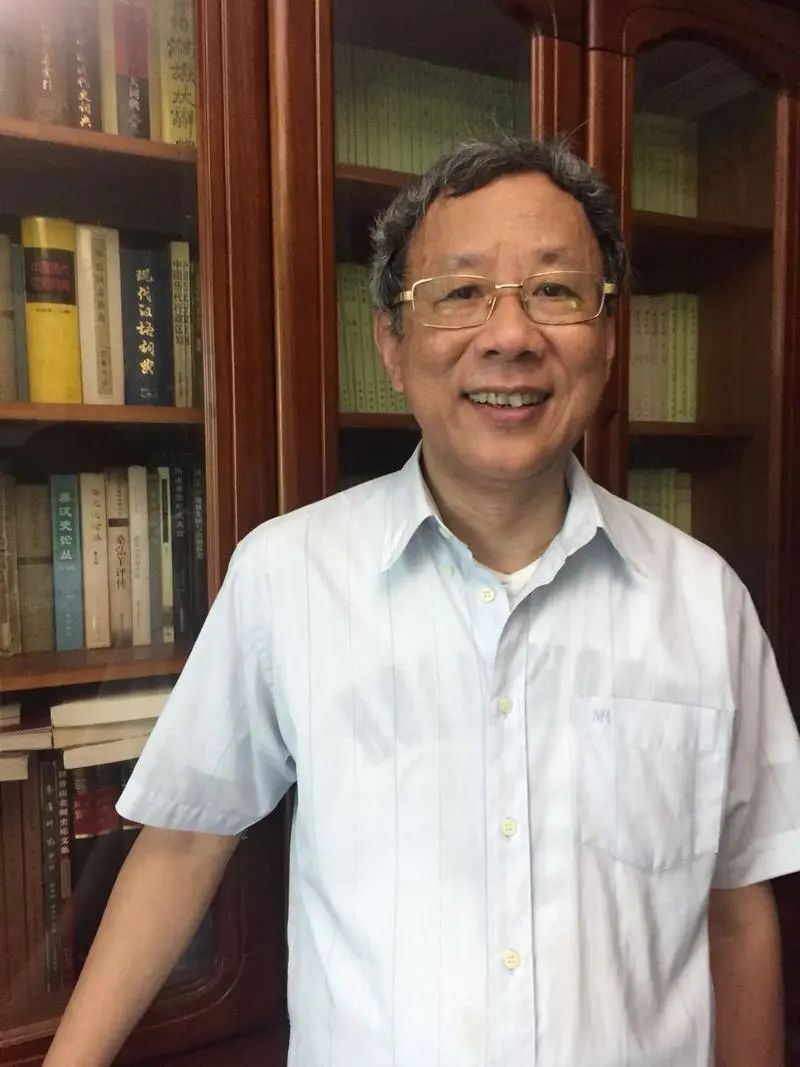
谁知好事者多磨矣!正当余翘首以盼,期待早日与李惠民晤面之时,李先生却告知,他因患疫病而久不愈,故不能陪伴。如此一来,余只能耐心等待,期盼他早日康复。但从今年二月等到现在的七月,时间已过去了差不多半年,一直杳无他康复的消息,这使余颇为失望。李先生已是八十四岁高龄的耄耋老人,加之身体抱恙而久不愈,余怎能为家中的族谱之事去打扰他呢?所以考虑再三,余决定放弃与李惠民晤面的计划。另外,余以为若不与李见面,菱湖也就不必去了,因为吾族之事,皆为明清掌故旧闻,菱湖镇上的年轻一代又怎么可能知晓。所以若无菱湖耆老或乡贤的陪伴,前往菱湖已毫无意义,至多只能发思古之幽情,祭奠先祖列宗罢了,何况若无李先生的发踪指示,余又怎能知晓祖宗的茔墓在哪里?
既然余之湖州之行作罢,那接下来又该如何办呢?余的续谱计划还要不要实施?若要实施,又该作怎样的调整?为此,余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按旧的修族谱程序和方略,须要依恃整个宗族的力量,有宗族中的德高望重者(旧时为乡绅)牵线或全面规划,组织一个修谱小组,其成员须宗族耆老或乡贤,续谱首先要统计宗族中不同时期的出生及死亡人口,包括每房的男丁或女口的盈缩,娶嫁配偶等事项。然后再统计这些人口的职业、学历等等。然而自清代同光以降,菱湖朱氏不少人已离开家乡,有的甚至远赴重洋,在异国他乡开支散叶。数百年过去了,他们已不再同菱湖镇的朱氏有任何联系,这又如何统计?按目前状况而言,菱湖镇上当然有朱姓家族,然而他们的祖先从何地而来?天下朱姓多矣,唯有茶院公朱环、思凱公朱永嘉之后裔才是吾之一族。而且即使是思凯公的后裔,除了极少一部分世代居住在菱塘镇上,余者恐怕都分散在全国、甚至是世界各地,如此的状况,谁来统计?谁来造册?所以当今之世,族谱若要能世代相传,至少二十年内得修谱一次。吾族宗谱自光绪二年(1876)以降再也无人续谱,至今已断层近一百五十年了,即使太史公在世,恐怕也徒唤奈何了。
余与弟子光乾与吾女隽颖商量后决定,必须大幅度地调整修谱计划。最关健地是基于现状,应将修谱的范畴缩的越小越好。原先设想的续修族谱已绝无可能,且完全是不切实际,甚至是异想天开。光乾兄提出纂修《菱塘朱氏支谱》的计划比较务实,甚得吾心。但在具体落实中还得要切实可行。余思考后拟出这样一个方案:
由于有《浮生记》的发现,故整个支谱以莲庄公朱潼为支点,向上可以一代一代地溯源到明初洪武年间迁徙到菱塘的始迁祖朱永嘉。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房支太多的枝蔓衍生,使人对支谱的世系一目了然。拟制作的《归安菱湖朱氏支谱》世系表都是单线上溯,举例而言,即只列莲庄公之父母,而不列莲庄公之父的兄弟姊妹。按照此例,依次类推,一直上溯到思凯公。
《菱塘朱氏族谱》的世系虽然可以追溯到茶院公朱环。但窃以为支谱还是以思凯公为始迁祖为宜,因为余这一支就是从菱塘朱氏传承下来的,而思凯公作为菱塘始迁祖是毋庸置疑的。支谱和族谱的眀显区别是体系和容量都比较小,否则何以称支谱。当然,族谱以朱环为婺源始迁祖也足以自信,因为族谱中有婺源朱氏从茶院公开始代代相因、族脉相承的记载,这是非常过硬的证据。何况朱环也并非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大人物,祖先也没有必要攀附于他。
余在支谱的序言中提到了吾族远祖朱敬则。敬则公贵为唐武周时代的宰相,在新旧两唐书中与武则天时期的名相狄仁杰载于同一列传中,可谓唐代重臣、名臣也。出自沛国朱氏的敬则公究竟是否是吾族之远祖,余很难回答这一问题。余在拙著《司马懿传》中考证司马氏世系时,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但凡治史者皆知,无论是帝王将相者的本纪列传,抑或私家所修的家乘谱牒,都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假托始祖、攀附名人,抑或司马懿家世亦不例外,故很难断定司马卬就是其先祖。三国时期,不仅司马懿祖先难考其实,即使曹操、刘备也是如此。元人胡三省曰:‘《蜀书》云:(刘)备中山靖王胜子陆城亭侯贞之后,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胡氏有此言,乃是因为刘胜的中山靖王是西汉早期所封,至东汉末年,已历数百年,又胜子刘贞为陆城亭侯,据考西汉并未有“亭侯”的封号,故他认为刘备与汉家皇室是否有血缘关系颇值得怀疑。”有鉴于此,我对朱敬则是否是余族之远祖亦持怀疑之态度,支谱虽将敬则公称之为菱塘朱氏之远祖,亦仅供世人参考而已,并不足以全信。
吾虽将修族谱计划调整为修支谱,但支谱如何纂修心中仍是没底。记得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傅斯年说过:历史研究应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傅先生此语,不仅研究国史、地方史应该遵循,即使修家谱也应铭记于心。谱牒也是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虽是家族的历史,但也来不得半点虚构。追远冒籍,过誉其祖,篡改源流,攀附名门与权贵,藉以提高自己的社会身份,这就导致私人所撰家谱多有失实之处。此类小人之所为,素为吾之不屑也。元人陈高尝言:“近世家乘族谱之作,往往夤缘攀附,忘其先而冒其祖,吾其敢尽信乎?”[4]清人章学诚则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谱系之法,不掌于官,则家为书,人自为学。子孙或过誉其祖父,是非或颇谬于国史。其不肖者流,或谬托贤哲,或私鬻宗谱,以伪乱真,悠谬恍惚,不可胜言。其清门华胄,则门阀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谢诸家,但有官勋,即标列传,史臣含毫,莫能裁断。以至李必陇西,刘必沛国,但求资望,不问从来。则有谱之弊,不如无谱。”[5]历史上的有识之士,皆指出历代谱牒中出现的造假溢美祖先之况,当为吾侪在修谱之时敲响了警钟。
当然也有因害怕造假而被后人耻笑者。吴晗在其所撰《朱元璋传》中对此状况有生动的描述:“朱元璋和文臣们商量修玉牒(家谱)的时候,原来打算拉宋朝著名的学者朱熹作祖先的。恰好一个徽州人姓朱的典史来朝见,他打算拉本家,就问:‘你是朱文公的后人吗?’这小官不明底细,怕撒谎闯祸,只好直说不是。他一想区区的典史小官尚且不肯冒认别人作祖宗,而且几代以来,也从没听说和徽州朱家有过瓜葛,万一硬认上,白给人做子孙倒也罢了,被识破落人笑话,如何使得?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6]
有宋以降,《百家姓》以赵氏为国姓,而定钱氏为天下第二大姓,于是诸多钱氏家族皆谓己族出自吴越国主钱镠,然清代大儒钱大昕却否认自己出自钱镠一族,此为后世修谱之人树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
虽然菱塘始迁祖思凯公后裔甚多,自有明洪武以降,代代相传,宗谱记载甚详,各房各支之人员名讳俱全。但清光绪二年(1876)之后已无人再续修宗谱。莲庄公朱潼一房虽仅是思凯公朱氏的一支,但他是余之曾祖父,与余有最直接最密切的血缘关系,以余一人之力,至多只能纂修莲庄公朱潼这一脉。据《浮生记》与《菱塘朱氏宗谱》记载,莲庄公有二子,即小庄公朱士林、幼庄公朱士元。小庄公为余伯祖父,他仕途通达,官至清光绪朝广东道台,又为清末著名的篆刻书法家,在文坛上享有一定的声望。然在余幼时模糊的印象中,仅认识他的女儿,我称呼她为二妈,她住在当时的南市区老西门一带,到我家来时常乘黄包车,一副阔太太的模样,称我母亲为小五婶婶。二妈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至于小庄公之子,我更无从得知。因此余就无法为小庄公这一支续家谱了。
十余年前,吾二兄主编了《忆父母亲》一册,其中附有浙江归安菱湖《朱氏家族简谱》,在当时并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编成《简谱》,也实属不易。《简谱》中仅列思凯公以降数代,每代仅以一人为代表,房中成员皆无。其中幼庄公一脉虽较详细,但其后裔名单仍残缺不全。幼庄公为吾侪祖父也,他与两恭人共育有五子、五女。《简谱》中云幼庄公长子曰问沧、三子曰建新,余以为其名讳俱不可信,既然幼庄公四子曰君厚、五子曰君肃,则其五个儿子必然俱以“君”字辈排列,此乃古人为子取名习惯之法也。
余反复思量之后,确立了这样一个修支谱法则:即修谱一定要力求完整,即使支谱也不例外,绝不能遗漏房中的一个成员。吾二兄寻觅幼庄公后裔已经做到了极致,几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绝无可能再补充幼庄公后裔的名单。因此余决定撇开幼庄公四个儿子、五个女儿(案旧谱惯例女儿原本就不上谱牒)的谱系,而以菱湖朱氏十八世雍熙公朱君肃为轴心,单线上溯到归安菱湖一世祖思凯公朱永嘉。雍熙公后裔的统计则绝不遗漏,列出包括其子媳、孙女、孙婿等所有人。此方案获得了余女朱隽颖的大力支持,她按谱索骥,仔细查阅《菱塘朱氏族谱》,将归安菱湖一世祖思凯公朱永嘉至十六世莲庄公朱潼脉系(案代与代之间只列有父子关系的,其余兄弟子侄辈一概不纳)的名讳及配偶全部寻觅出来。经余女整理后,支谱传承脉络清晰,自思凯公以降至今共传二十世,这就为支谱的纂修奠定了基础。因弟子诸文进工于书法,遂请他书写《思凯公至雍熙公及其子孙一脉世系表》,文进兄亦慨然允诺,并克日完成。
至于《支谱》的内容如何安排,亦颇费思量。若仅有一张《思凯公至雍熙公及其子孙一脉世系表》,则内容未免太单薄了,因此我在《菱塘朱氏支谱序》中综述了先祖的事功与宗族迁徙的历程,建构了纂修支谱的理路和问题意识。莲庄、小庄、幼庄、雍熙四公的行状是我手中现有的他们毕生事功最为翔实的材料。四公皆为近世之人,离吾侪之世不甚久远,莲庄公辞世之时才是清光绪年间,小庄公、幼庄公、雍熙公身处清末民初与国朝,皆是当代人较为熟稔的时代。四公的行状为《菱塘朱氏宗谱》所未有,录之可弥补旧宗谱之不足,亦可使吾申江之族人永远铭记四公之事,四公之德。《浮生记》不仅反映了菱塘朱氏家族的历史,还从一个侧面、一个视角来了解清代的地方吏治和近代师爷的业绩与功能,关于《浮生记》的学术价值,前文已作了充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最后再谈一下支谱的定名,诸文进初拟之谱名为《补足浙江归安朱氏一族朱君肃一脉家乘》,余以为太为冗长,故予以否决。再与王光乾商量,改为《菱塘朱氏支谱》。最近余去宁波、慈溪等地讲学,在参观宁波、绍兴博物馆时,看到馆中展出的一些地方上的谱牒,其中有《慈溪罗氏宗谱——清水湖罗家支谱》,使我深受启发,在与隽颖女商量后,最终定名为《菱塘朱氏宗谱——申江支谱》。申江即上海也,幼庄公晚年来到上海,雍熙公大半辈子居于沪上,吾侪生于斯,长于斯,故吾家之谱当以沪上为根,余赓续菱塘朱氏宗谱,以《申江支谱》定名,最为确切妥贴也。
《申江支谱》的纂修,梦想数十年,动笔达半年之久,其间迭遭挫折,几经反覆,终于成稿,余甚感欣慰。《申江支谱》的纂修虽然由余一人独力完成,但也少不了弟子与友人的鼎力相助,必须鸣谢的弟子是王光乾兄、诸文进兄、林介宇兄以及余巨平先生,若无他们的襄助与支持,余是不可能完成此项工程的。
朱子彦
癸卯六月初八写于新梅寓所
[1]王光乾主要从事嘉定区域文史研究,涉猎嘉定文学史、书画史、竹刻史、家族史等方面,同时致力于文物建筑保护、嘉定地方文献搜集整理、馆藏文物研究。先后在《中国史研究》《上海大学学报》《中国图书评论》《文物天地》《上海文博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50余篇,著有嘉定家族史研究专著1部——《嘉定望族》,整理并出版(发表)《嘉定李流芳全集》《梦盦居士(程庭鹭)年谱》等古籍4部。
[2]按这好比已是夫妻,或父子、母女关系,但仍要出具这方面的证明。
[3]李惠民原是菱湖中学教师,退休后,与他人合编出版《菱湖镇志》,编写菱湖镇12个农村文化礼堂、以及竹墩村名人馆、诗文碑廊和家风乡贤馆等文字展稿。
[4]陈高:《不系舟渔集》卷10。
[5]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 1985年版。.
[6]吴晗.《朱元璋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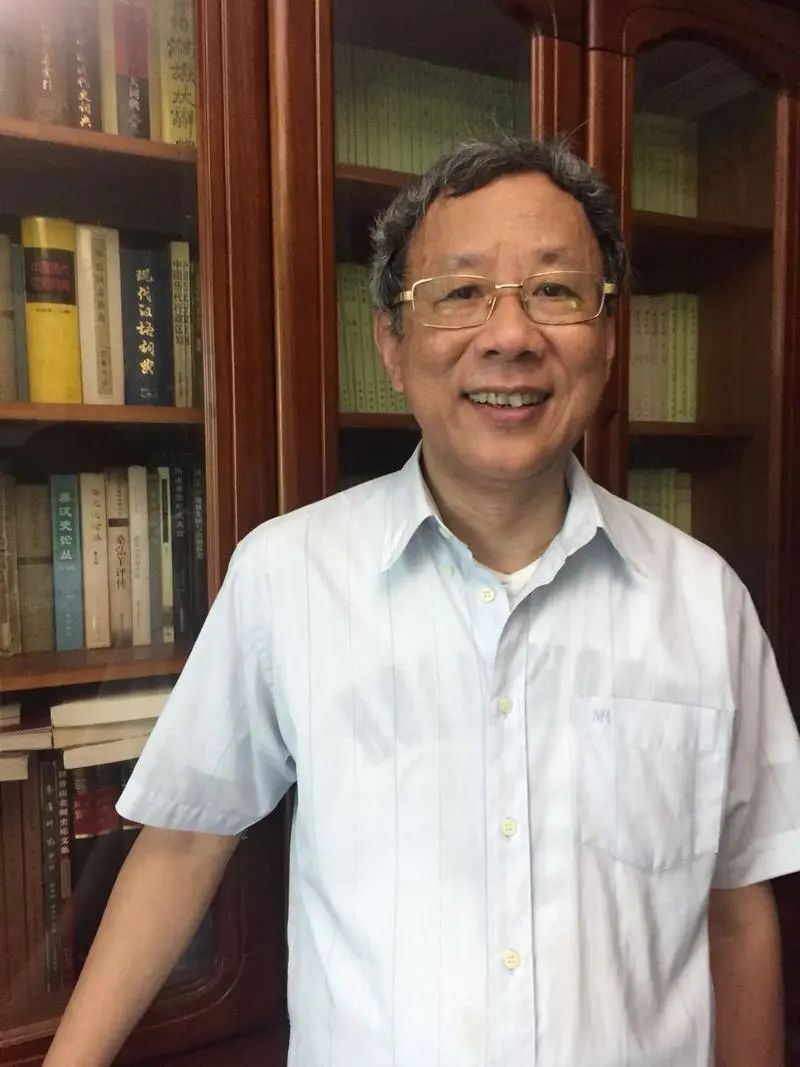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