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方盛良,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古籍研究》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明清诗文与批评研究。
摘 要
经史之思一以贯之于桐城派文论中,衍至晚清民国时期,姚永朴面对历史丕变,始终予以坚守,其《文学研究法》在系统梳理、阐释和建构“文法”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史识”,并融通在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和批评史、学术史等多个层面,它见证了姚永朴对传统文化的坚定守护和应对策略,体现出晚清桐城派挽救传统道统和文统的最后努力,也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中国近代文论转型的复杂和艰难,可谓是姚氏构建“文法”的一个灵魂。
关键词
姚永朴;文法;史识;桐城派
无论是在桐城派发展史上,还是在近代传统文化新变时期,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都堪称一部杰出的文学研究著作。该著凝结着作者的经史之思,自成一统,“经”与“史”可谓是建构该著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学界至今对此多有忽略,其意义未有彰显。本文拟专从“史”的角度,对该著所涉的几个层面加以清理和研讨,以期最大程度上接近其本真面目,发掘其价值所在。这里的“史识”特指姚氏注重文学史演变,文史会通,论从史出的识见。
一、学制变革与教材撰写:以“史”贯“文”的动因
《文学研究法》是姚永朴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课堂讲义,撰写于1913年年底,成书于1914年年初,前有其弟子张玮的序言。《序》云:“先生论文大旨,本之姜坞、惜抱两先哲。然自周秦以迄近代,通人之论,莫不考其全而撷其精。故虽谨守家法,而无门户之见存。”可见,该著既有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历时性的总结,采撷其精,并融之于桐城派的文论话语体系中,赋予晚期桐城文论更为融通开放的格局。
晚清民国之际,学制改革,新旧转型。1913年民国教育部大学规程规定,依照《大学令》,“国文学”类将“文学研究法”与“中国文学史”并列,强调它们的差异性不言而喻。姚永朴在北京大学担任“文学研究法”课的讲习,著作亦以“文学研究法”命名,侧重于“文学研究”、与文学史保持一定的距离,本该是情理中的事,但实际上通篇表现出强烈的“史识”,其背后的历史境况耐人寻味。光绪二十八年(1902)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颁行,“今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分列如下:政治课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文学科”之目别为“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中国文学”并未与“史学”同时出现,而以“词章学”名之。光绪二十九年(1903),奏定大学堂章程颁行,规定“文学科大学”分为九门,其中“中国史学”与“中国文学”并置,“中国文学”取代了“词章学”。1913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规定大学之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这是现代学制改革的重要突破,文学科与历史学科的界限划分清晰,传统教育从文史哲不分逐渐走向文史哲三分,这是桐城派传衍二百多年从未遭遇而又不得不面临的大变局。《文学研究法》正是这一学制改革直接催生的后果。该著虽言“文学”,但作者反复征引敷衍经典,于“经”“史”没有片刻的割离,可谓经史之思贯穿“文学”。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晚期桐城派对新学制下的文史之分的态度,可视为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回望与眷恋。

姚永朴像
如果结合姚永朴执教和所撰课堂讲义来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文学研究法》著作的历史。1901 年,姚永朴任起凤书院山长,嗣后又回山东高等学堂任教。其间,他著有《起凤书院答问》,自序言:“光绪辛丑(1901),予以同邑叶玉书大令之招,主讲信宜起凤书院。诸生肆业者时质所疑,辄据鄙见答之,积久成秩。壬寅(1902),襄教事于山东高等学堂,讲授之暇,复取旧稿,稍加删改,以类钞之,为五卷,将就有道而正焉。”该著体例秉承传统教学模式,详细地记录了 80 条师生问答,并依照目录学分类,分为经、史、子、集、杂五卷。史部与集部即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与“文学”。在书院教学,姚永朴践行的是文史不分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必然有着较强的惯性,对其后的教学和著作产生影响。1909 年,姚永朴受聘国文教习,执教于京师法政学堂,期间著有《蜕私轩读经记》《国文学》《史学研究法》等。《史学研究法》成书的时间大约在 1909 年至 1912 年之间。该著收于姚永朴《素园丛稿》中,姚永概序言:“《经学举要》一卷、《国文学》二卷、《史学研究法》一卷……客安庆、京师教诸生所作。”显然,《史学研究法》撰写先于《文学研究法》。从现有的文献比较来看,两个版本《国文学》是《文学研究法》直接材料来源;从撰写的体例与方法来看,《史学研究法》可谓是《文学研究法》的范本。《史学研究法》别为《史原》《史义》《史法》《史文》《史料》《史评》《史翼》与《结论》8 篇,从这些题目不难见出学制改革的痕迹。其中,《史文》一篇值得参详,“史文”语出《孟子》:“《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此文首引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开篇,接着论述“况史也者,尤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使无文以张之,何以广见闻而新耳目乎”。很明显,姚永朴有将史学凌驾于文学之上的意味, 因为此论源于曹丕《典论·论文》中申述文学的重要作用,姚永朴将“文”转易为“史”,其意图也昭然若揭。《史文》篇从“古与今”“奇与偶”“繁与简”“曲与直”四个方面进行阐发,从文学的角度对史学进行观照,凸显了史文不分的情况,似有刻意强调文学与史学的关联,回归文史不分的传统。
《文学研究法》的撰写是以《文心雕龙》为范本的。癸卯学制章程中,中国文学科目“历代论文要言”规定“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蒐集编为讲义”。这直接为教材编著提供了参照。张玮序言:“其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自上古有书契以来,论文要旨,略备于是,后有作者,蔑有尚之矣。”《文心雕龙》体大思周,是中国文论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不难发现,《文心雕龙》本身也有其“史”的考察,如《时序》《事类》《史传》等篇,就是从“史”的角度来阐释的,其“史”之痕迹在文本中比比皆是。发展到晚清民国初年,在学制变革、“文学”学科单列中,《文心雕龙》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研究著作兴盛,名著如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等。与黄侃对《文心雕龙》深刻细致的剖析有所不同,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则是直接从《文心雕龙》那里寻找资源与方法,它是《文心雕龙》接受史上,有别于黄侃的异声别调,令人深思。
二、以史系文:构建文学发展史的谱系
阐释文学是《文学研究法》的核心所在,涉及文学发展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三个层面, 姚永朴是从文学发展史入手的。以下从这三个层面梳理其中“文”与“史”的关联,探讨姚永朴构建文学发展史的谱系。
《文学研究法》卷一包括《起原》《根本》《范围》《纲领》《门类》《功效》六目,具有文学总说的性质,可以视为文学本质论。在文学本质论中,姚永朴对文学的考量,是从文学的起源开始论述的,他在《起原》中追溯文学的源头,对文学衍生的过程进行详细阐发,得出“文字之原,其基于言语乎,言语其发于声音乎,声音其根植于知觉乎”的结论,这就勾连起文学与语言的关系,为论述文字为文学之源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姚永朴还关注到文字载体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在历数由书契、竹简至活字印刷的历史后,认为“文籍流布,其术古拙而今巧”,文学的发展与文学载体紧密相关。姚永朴历时性地推演文字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史识”鲜明。在《范围》篇中,姚永朴对历代文学的概念进行了阐发。他指出:“文学之范围,有广义焉,有狭义焉。”关于广义文学的内涵,他援引《论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与“焕乎其有文章”等文献,并佐证“先儒谓凡言语、威仪、事业之著于外者皆是,盖所包括众矣”的结论。就专以文字之成为书者而论,他认为《汉书·艺文志》标举“七略”,并认为“七者之文,莫不炳然可观,垂声千载,虽尤著者莫如诗赋”,也即认为“诗赋”与其他六略相比,文学性更强。又,论及专集与总集,以为专集之名,由后人追录起于西汉之末,迄于东京,“自制名者,始于张融《玉海集》”“总集莫古于《楚辞》”。姚永朴论述专集与总集之间的关系,目的是为了验证随目录学的发展,经、史、子、集四类逐渐定型,集部作为历代文章之总汇也最终完成。文学的含义由广而狭,既是时势使然,又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自然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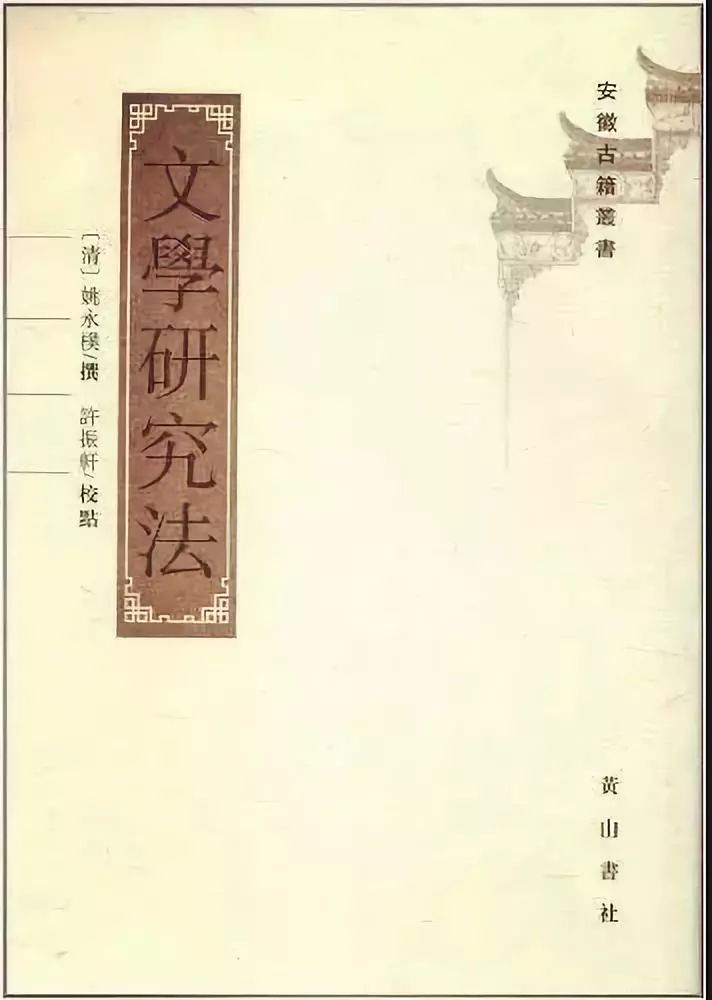
姚永朴撰《文学研究法》
《运会》篇开首照录《文心雕龙·时序》,赞同刘勰对晋宋以前文学理论的总结。刘勰在《时序》篇中,充分表达了他的文学发展观,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等论断影响深远。在考察文学的真实状态时,不能避开时事对文学的影响与推动,但文学生态复杂,发展漫长。姚永朴言刘勰《时序》篇“所论于晋宋以前文学兴废,已得其概;惟末于齐语焉不详”,并推测其原因为“岂有所讳而然欤”。所以,姚永朴《运会》后半部分,多撮钞诸史之中《文苑传》相关文学的论述来接续刘勰。《文苑传》与文学史联系密切,章学诚言:“东京以还,文胜篇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则汇次为《文苑》之篇。文人行业无多,但著官阶贯系,略如《文选》人名之注,试榜履历之书,本为丽藻篇名,转觉风华消索;则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尽也。”虽然着重论述《文苑传》的起源,认为其不能尽显文学史的全貌,但毕竟关注到《文苑传》与文学史的关系。实际上,《文苑传》往往不限于对优秀作家作品评介而且论及整个文坛状况,隐含着文学史的内容。姚永朴敏锐地观察到这点并援引《文苑传序》作为其阐发“文学史观” 的史料,从《后汉书·文苑传》到《明史·文苑传序》,他几乎网罗了所有《文苑传序》中对文学的点评,以为“此皆前史所载之可考而知者”。对于清代文学状况,姚永朴从古文、骈文、诗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列举了清代文坛重要的代表性的作家。比如诗歌方面,他以为:“诗则有龚鼎孳、吴伟业、王士祯、施闰章、宋琬、朱彝尊、赵执信、査慎行,而大櫆及鼐之诗亦最胜,其末造有莫友芝、郑珍。”清代诗歌发展流变的情况也大致能从这一名单中得到勾勒, 尽管以刘大櫆与姚鼐的诗歌“最胜”有些夸张。姚永朴为桐城诗派张目,但并不墨守成规:“今综而观之,虽历代英才,应运而出,然元、明、清文学逊于宋,宋逊于唐,唐逊于周、秦、两汉,岂不能不为时代所限欤!”这就再次回到了“时序”的论点上了。姚永朴在文史观的阐发上,继承了刘勰“时序”“通变”等文学思想,同时他又对晋宋以后文学情形进行了梳理,以“运会”来统筹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是符合文学发展史实际的,体现出他的文学整体史观。
在《诗歌》篇中,姚永朴评论了王士祯与姚鼐两家诗论,对诗史的流变进行了相关考察。王士祯在《古诗选》中选评了五七言古体诗,所言精当,桐城派对其以“神韵”论诗多有会心,褒中有贬,姚永朴继承桐城诗学传统,予王士祯以极大的关注。姚鼐《五七言今体诗钞》专选唐五七言今体诗,王士祯未及律诗,二者正可互补,姚永朴对此明察。姚鼐论涉及唐宋五言律体、七言律体,尤重杜甫与苏轼两家,兼及陆游,谓陆游“其七律固为南渡后一人”。姚永朴在对比分析中以为“惜翁论诗语与阮亭参观,各体略备”,但“阮亭未选明诗,惜翁则止于南宋”。姚永朴还援引钟嵘的《诗品》、叶少蕴《石林诗话》、姚范《援鹑堂笔记》、张英《聪训斋语》、方东树《昭昧詹言》等诗话,与王、姚诗评进行相互参读,持论公允。正是在这种多种参照补正中,诗体流变史面貌清晰可见。
综上所述,姚永朴从文学发展史的视角考察了文学起源、文学的内涵、文学的流变等,使得文学的一些概念和范畴得到较为准确的揭示。他对文学规律的探讨,建立在文学史的梳理之上,在点与面的结合中,牢牢抓住文学演进的主线,并以之将文学的现象串联起来,显示其间网状脉络,较为完整的文学谱系因此得以建构。
三、以史论文:建构文学理论史、批评史之框架
如果将《文学研究法》置于文学理论史、批评史的维度加以考察,也颇有启发。作为桐城派晚期重要的古文家,姚永朴站在桐城派的立场上,对传统文论进行重新的审视并加以论述,这既有对传统文论的总结又能见出桐城派的新变。
《文学研究法》对文学范畴的探讨主要见于卷三与卷四。杨福生认为,卷三是文学作品构成论,卷四是风格论。许结除了赞成卷四为文学风格论外,进一步将卷三视为文学作品论与文学批评论。卷三篇目别为《性情》《状态》《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后四篇是姚永朴对姚鼐“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八字箴言进行的分组探讨。
“神理”作为一个古代文论概念,在桐城派文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姚鼐视为“文之精”,与“文之粗”相对。姚鼐而下,桐城派对此多有思考,并奉之为古文至镜,对此,王达敏和蒋寅先生曾先后予以申论,无需赘言。值得继续论说的是,姚永朴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化阐释。
关于“神”,姚永朴溯源“神妙”“神化”之说的由来,援引《易·说卦传》“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孟子·尽心》“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并认为“文章亦有此境,必神足,辞乃无不达”。姚永朴还采择《说文》中对“神”的释义“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并引杜甫“文章有神交有道”“书贵瘦硬方通神”来进一步佐证。关于如何达到神妙神化之境,姚永朴认为其“是有本原”“有工力”的。姚永朴依经立义,首引《易·系辞传》《礼记·孔子闲居》里关于“神”的论述,对“穷神知化”的传统道德修养与文学所追求的意境相联系,阐发“人品”与“文品”的古老命题。他指出“此虽不专就文章言,而文章本原所在,固如是矣”,也即意味着“崇德”是达到文学入神的要求,“人品”影响着“文品”。姚永朴对《庄子》一书也特别嗜好,其“夫真超然于生死者不言生死,言生死者非超然于生死者也;真忘机者不言机,言机者非忘机者也”之论,也即重视“形神”“言意”之间辨正的探讨,间接也提及对“神”的观照。《庄子》一书,对“神”的阐发尤多,姚永朴引《养生主》里寓言“庖丁解牛”的故事,借以说文事,赞扬“去形达神”之神遇神境;引《达生》里寓言“痀偻承蜩”的故事,表明“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境界。姚永朴从《庄子》对“神”的界说,顺流而下,引后代文人对“神”的描述进一步补充说明其论。他引韩愈《送高闲上人序》“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来说明“神完”之说,并引姚鼐《古文辞类纂》与曾国藩《日记》对其解说评注。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也提出了“神气说”。姚永朴认为以上几条关于“神”的论述,都可以相互参观。其后,姚永朴还论及“古人精神兴会之到,往往意在笔先”的情形,引用文献有《史记·管晏列传》《文心雕龙·神思》等。至此,关于“神”的相关概念,经过姚永朴的梳理,基本上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姚鼐《古文辞类纂》
关于“理”,姚永朴从《说文》中寻绎“理”的本义“治玉也”。他阐发道“盖玉既治,其文理始昭著。故引申之,凡事物之有条不紊者,皆谓之理”。他还分辨了“理”在音乐与文章之中的区别,“其在音乐,则《孟子·万章篇》所谓‘始条理’‘终条理’者是也。其在文章,则《荀子·非十二子》篇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由上可知,“理”从具象的本义逐渐衍生为抽象的引申义,从切实可以感知的物象变成不可捉摸的意象,其间反映的是“理”的含义不断沉淀的过程,是文化观念不断变化的结晶,是形而下的思维向形而上的思维的演进表现。既然“理”是抽象的概念,那么又该如何把握?姚永朴指出:“若夫理之天下,无论见于事,寓于物,皆赖文以明之。”这就指明了“文”在诠释“理”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和唐代古文运动时所提倡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之说相符。姚永朴引张耒、苏轼、魏禧等人论文之语,发明要“文理通达”之旨,并引曾国藩之论,阐明理达与积理之间的关系。姚永朴针对曾氏之论,继续探讨关于“积理”的文学要素。他引洪迈《容斋四笔》里关于明理与意的关联,强调“理虽积之于书,而意则摄之于我。既有意矣,又必有术以行之,然后能执简御繁,化腐为奇”。另外,姚永朴还引了桐城派成员一些文论观点以说明“理”与文学的关系,如刘大櫆“义理与神气”、姚鼐“积理与翻新”、方东树“文章述理‘旁见侧出’之妙”等。
姚永朴对“神理”的阐发,几乎串联起了整个文论史上关于“神理”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桐城派对建构文学理论和批评史框架的新贡献。这些在其他篇目中也有很好的体现,比如《气味》《格律》《声色》等。
卷四篇目分别为《刚柔》《奇正》《雅俗》《繁简》《疵瑕》《工夫》,这自然属于文学风格论的范畴,姚永朴进行的阐释也是别出心裁,现例引《刚柔》篇论之。“阳刚”与“阴柔”这对文学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史上的讨论由来已久,姚永朴正本清源,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如,他引《易·贲卦·彖传》“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引《说卦传》“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证明“文章之体本于阴阳、刚柔,其来远矣”。在考察“刚柔”说的演变过程中发现此说产生时间之早与后世文学家的关注程度出现不对称,即“后世文学家未有论及此者”;又指出唯有《宋书·谢灵运传论》“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里论及“刚柔迭用”的事实;至于刘勰《文心雕龙》之作,也仅在《熔裁》中简述“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姚永朴指责其“未畅厥旨”,相较其他文学概念,刘勰对“刚柔”之说似乎论述相对较少。考其原因,也许是将此风格论融于其他文学范畴之内,比如“风骨”就能与“阳刚”生发联系。
桐城派对文章“刚柔”风格格外重视。桐城派倾心于“刚柔”风格论,也即认识到“刚柔”风格对于古文的重要性,也反映出桐城派对古文内在属性的自觉体认。姚鼐可谓“刚柔”说集大成者。其“刚柔”论主要见于《答鲁絜非书》与《海愚诗钞序》二文。姚永朴对“刚柔”的阐发,主要立足于姚鼐《答鲁絜非书》一文:“篇中言‘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恐世之浅者借口,以犷悍为阳刚,以靡弱不振为阴柔也。其言‘一有一绝无’、‘不可言文’者,盖阳刚、阴柔之分,亦言其大概而已。”他认同前辈之论,认为“必刚柔相错而后为文,故阳刚之文,亦具阴柔之美,特不胜其阳刚之致而已;阴柔亦然。止可偏胜,而不可以绝无”。姚鼐之后,曾国藩推演“阳刚阴柔”,析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论点主要见于曾氏《家训》《日记》及弟子吴汝纶《记古文四象后》中。曾氏将文章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所构成的文境,分别以四字对应:“阳刚之美,莫要于‘雄’‘直’‘怪’‘丽’;阴柔之美,莫要于‘茹’‘远’‘洁’‘适’。”并对每种文境进行了阐发。姚永朴大篇幅引用了曾氏论文境之言,也足见其对曾氏之论的认同了。继曾氏之后,张裕钊也对“刚柔”说有论述。据吴汝纶记载,张氏以二十字分配阴阳:“阳”为“神、气、势、骨、机、理、意、识、脉、声”;“阴”为“味、韵、格、态、情、法、词、度、界、色”。
由姚鼐的阴阳刚柔说到曾国藩的“四象”说,再至张裕钊二十字说,“刚柔”说在桐城派成员的论述中越来越精细化,从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逐渐衍生落实为由一系列各有侧重的不同文学风格,是桐城派对文学风格论的系统贡献。在面对具体作家作品时,姚永朴引管同《与友人论文书》“仆闻文之大原出于天,得其备者,浑然如太和之元气。偏焉而入于阳,与偏焉而入于阴,皆不可以为文章之至境”,表明了自身对“刚柔”说的立场。“阴阳”调和是达到“文章至境”的途径,任何偏执都有可能造成文境的破坏。对于经典著作《史记》,管同认为司马迁为阳刚类型,而曾国藩则认为是阴柔类型。姚永朴见出二说之间的分歧,并推测造成差异的原因为二者对文章“气之雄奇、跌宕之姿”的不同看法,补正以“文章之道,刚柔相济”。
综上可知,姚永朴对文章“刚柔”说的阐发,既对其渊源流变进行检视,明晰了历来对“刚柔”说的接受历程,又对各家所论及的“刚柔”说进行了批评,见出不同论者之间的差异,将桐城派历代关注的“刚柔”说大大往前推进一层,这是姚永朴对传统文论“刚柔”说的新贡献。此外,姚永朴详尽梳理论述的还有“奇正”“雅俗”“繁简”等概念,其论述的方式,皆可与“刚柔”说相参。完全可以说,姚永朴是在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这两个维度上,对一系列涉及文学风格和本质的文学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具有文学“史”的广度和深度。我们甚至可以说,姚永朴以史论文,从而建构文学理论史、批评史之框架。
四、努力与绝望:学术史意义的生成
《文学研究法》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也极为重要。前文所及的疏证,关涉经史子集,举凡征引考核,会通评论,不出学术史的范畴。此外,该著还对桐城派发展史的得失进行了自觉的检讨,并有意做出补充和调适,这见出晚期桐城派的包容心态和新变气度,但亦遭到刘师培、黄侃等批驳,其间涉及桐城派与选学派之间的学术史公案,学者对此多有探讨,无需赘述。兹引刘师培所言:“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文之制作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如姚氏曾氏所选古文是也。)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刘师培以骈体为宗,在貌似辨体的论述中,对桐城派大加鞭挞,归罪“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如果抛开对这段话公正与否的讨论,那么这一归罪,恰恰可从反面证明桐城派对“经”与“史”的重视以及传承到姚永朴的手上真是由来已久了。章太炎曾言:“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辩。或语季刚: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喧嚣声里,桐城派与选学派渐次退出近代文坛,曾经烜赫一时的两大派别,谁也没能抵挡新文化潮流的撞击,最终都曾被裹挟覆灭得悄无声息。就此而言,对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的史学考察,恰恰镜鉴出传统文化断裂时期,一代人不同努力和共同绝望的一段历史。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研究法》的史学效应,它见证出该著的又一价值所在。
以上对《文学研究法》其中与背后所涉 “史”的几个层面进行了分次探索,实际上,这几个层面并不是孤立的,有时,它们不仅互有交织而且还互为因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著在论说过程中时有阐释未周之缺失,如,论说文章的“根本”时,除了“明道”和“经世”之外,于安身立命、寄托情怀等别无只言片语。这固然有桐城派固守“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之限,也实属上述种种“史”的局限。这样,它又属于1910年代系列高校教材的历史缩影。
总之,该著对传统文化的坚定守护和应对策略,正可以通过“史”的考察而证明,阐释构建“文法”之中,深藏着桐城派一以贯之的“经史”之思,“史识”如影随形,堪称灵魂。由此可见,这部著作的意义远不止于是“文章学的总结”,完全可视为晚期桐城派挽救传统文统和道统的最后努力,是其于历史的无奈中走向穷途末路的最后叹息。
参考文献
[1] 姚永朴:《姚永朴文史讲义》,凤凰出版社, 2008。
[2]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许结讲评,凤凰出版社, 2009。
[3] 姚永朴:《起凤书院答问》,郭康松、林璐校注,华夏出版社, 2013。
[4] 姚永概:《素园丛稿序》,宋昱辑《素园丛稿》,京华印书局,1912。
[5]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6] 章学诚:《文史通义》,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4。
[7] 吴德旋、吕璜纂:《楼古文绪论》,中华书局,1985。
[8] 章太炎:《讲演录·文学略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9] 姚鼐:《古文辞类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10] 洪治纲主编:《培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11] 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主编:《派名家文集·姚永朴集、姚永概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
[12] 杨福生:《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述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13] 许结:《姚永朴与〈文学研究法〉》,《文学知识》2010年第1期。

《江淮论坛》2018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转发。为阅读方便,现已将注释略去,仅保留参考文献。

主编:马丽敏
刘建欣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