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5200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出的楔形文字,是人类最早发明的文字,由这种文字写出的文书,又被称为“楔形文书”,由于载体是泥版,因此又被称为“泥版文书”。在随后的三千多年中,楔形文字的使用范围扩展到整个西亚地区,乃至埃及,很多民族都使用楔形文字,并形成了各自特色的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苏美尔等楔形文字,在当时形成了一个“楔形文字文化圈”。大约公元1世纪时,整个楔形文字逐渐灭绝。
1472年,一个意大利人游历伊朗时,发现了楔形文书,但当时无人知道其来历,也无人能够释读。1700年时,英国人托马斯?海德将这种文字命名为“楔形文字”。1900年后,整个楔形文字基本被西方学者破解。
从发现楔形文字到宣告破解,中间大约相距400年,用时不能算短,但甲骨文与现代汉字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至今尚且破解不到一半,那么当时楔形文字已经成了一种几乎没有传承的“死文字”,为何西方学者还能将之破译,甚至还知道每个楔形文字的读音?鲜为人知的是,破解楔形文字过程中,关键钥匙之一是《圣经》等西方古代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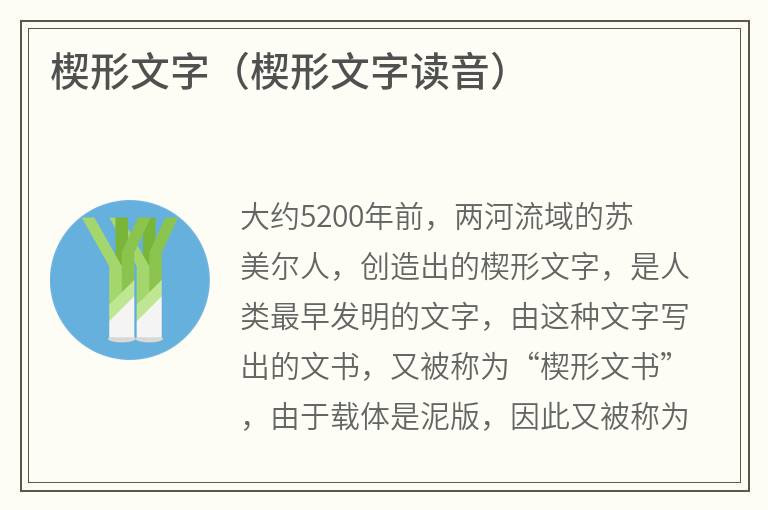
楔形文字(楔形文字读音)
回顾楔形文字的破解过程,学者刘昌玉在《楔形文字是如何“死而复生”的》一文中有过总结,破译楔形文字有三个先决条件,即:首先是双语文献或三语文献的发掘发现,其次是伊朗古代文献的辅助,第三是《圣经》及西方经典作家的著述。在此前提之下,经过数百年的探索与天才的灵光一现,最终西方学者破解了楔形文字。
破解楔形文字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挖出与其有关的双语文献或三语文献,最好其中一种或多种语言在今天还有传承。
在出土的泥版文书中,不少属于双语文献,少数是三语文献,比如刻有三种楔形文字的贝希斯敦铭文(上图),每种文字记载的应该是相同内容,在这些多语楔形文书中,其中一种语言被认为是古波斯语。由于古波斯语与现代波斯语之间还存在一点关系,这就让楔形文字的破解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两者之间联系极其微弱,因此要说借此破解古波斯语楔形文书,还是异想天开,尤其是其中涉及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等专有名词,必然需要依赖于传世文献。
破解楔形文字的前提之二,是伊朗古代文献的辅助,就像中国人研究甲骨文时,就必须借助关于商朝的相关文献,破解楔形文书,也必须要有本地文献的支持。
破解楔形文字的前提之三,是《圣经》及西方经典作家的著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圣经》、古希腊等著作中记载了一些西亚上古事迹,这对于破解楔形文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甲骨文与现代汉语之间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传世史书上还有众多商代记载,即便这样,如今还有半数以上的甲骨文无法释读。相比中国的甲骨文,破解楔形文字的条件更艰难,毕竟古今波斯语的联系极其微弱,伊朗与西方著作中对楔形文书中的历史,有没有记载或记载的对不对,其实是说不清的。
既然如此,西方学者到底是如何破译楔形文书的呢?其实,西方学者重点是以《圣经》、《历史》等西方古代典籍为依据来破解楔形文字的,以贝希斯顿铭文中古波斯文的英国学者罗林森为例:
学者拱玉书的《西亚考古史》记载:“巴兹的研究结果表明,罗林森的解读方法基本上与格罗芬特的方法相同,也是从专有名词入手,即首先确定专有名词,再把希腊古典作家著作中保留的读音分解成字母,然后再把具体字母与具体的古波斯楔形符号对号入座……由于贝希斯顿铭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基本都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希腊古典著作,这就使罗林生成功解读古波斯文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包括罗林森在内的很多西方学者都从专有名词入手,从西方经典著作入手,相信西方著作中提到过楔形文字上的人物国家等。罗林森就相信贝希斯顿铭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在西方著作中都一一出现过,并大概以“古波斯语的音译词”的方式存在,于是将这些分解成字母而与古波斯语对应,最终破解了古波斯语,还搞清楚了古波斯语的读音。
其中,罗林森的上述破解过程之所以没有详述,原因在于“罗林森对他解读楔形文字的经过总是轻描淡写。在回答人们的追问时,他写道:‘我已经讲不出我当时确定每个字母读音的方法。’”后来人们只能猜测他的破解方法。
但问题在于,如果希罗多德的《历史》等西方古典著作,对古波斯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记载有误呢?更何况,这种破解方式明显存在逻辑问题,最多只能作为辅佐手段。因此,当时就有不少学者质疑罗林森等人的破解,甚至认为他们的解读不可能正确,“如果照他们的方法去做,不但会给一切不确知的事情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就连古代亚述人自己也绝不可能读懂这样的文字”。
除了上述与罗林森破解方式大致相同的格罗芬特之外,西方还有不少学者研究楔形文字,但彼此结论都不尽相同,一直没有公认的结论,到1857年时终于出现了重大改变。
1857年,罗林森给博尔塔特寄了一份刚刚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之后博尔塔特按照自己的方式将之释读。博尔塔特释读之后,将之寄给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并要求将之封存,然后让罗林森释读一下,以比较两人的结果。博尔塔特的意思是,如果两人释读一致,那么说明解读方法的科学性和结果的正确性。
随后,罗林森扩大了范围,建议“皇家亚洲学会”召集爱尔兰人欣克斯和法国人朱利叶斯一起参加考试。于是,罗林森、欣克斯、朱利叶斯被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释读出一篇楔形文字文献。最终,“皇家亚洲学会”组织鉴定认为:各家解释虽在细节上有一定出入,但总体一致。
1857年的“闭门考试”标志着亚述学的正式诞生,这三位被尊为“楔文三杰”,其中贡献最大者罗林森被冠以“亚述学之父”的尊号。更为重要的是,不管他们的结论在之前受到多少质疑,但之后他们的研究结论得到公认,成为权威。
当然,对这一次“闭门考试”不是没有疑问,抛开“私下串通”的阴谋论不谈,即便三人解读“总体一致”,也不能证明三个人都正确!毕竟,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都是以西方古代著作为重要依据去破译的,得到大概一致的结论也不奇怪。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是三个人都错了,因为在甲骨文破译中,同时多个大学者判断错误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还有比如二里头遗址刚出土的时候,众多顶尖学者都认为是夏都,现在随着考古的深入却逐渐有了不少质疑。
由于罗林森发现的贝希斯敦铭文中,除了古波斯语之外,还有埃兰语、阿卡德语,于是随着最年轻的古波斯语被“公认破解”之后,埃兰语、阿卡德语先后就被破解。更妙的是,古巴比伦人编撰了一部苏美尔—阿卡德语双语词表和语法书,于是西方学者据此就把苏美尔楔形文字给破解了。因此,贝希斯敦铭文在破译整个楔形文字过程中的地位,可以与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罗塞塔石碑”相媲美。
按照西方教科书的说法,到1900年时,虽然还存在一些词汇问题和语法疑惑,但阿卡德楔形文字(分为巴比伦与亚述两支方言)、赫梯楔形文字、胡里楔形文字、乌加里特楔形文字、乌拉尔图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等基本都全部成功破解,连读音都神奇的被标了出来,尘封数千年的历史大白于天下。
不过,以西方学者对楔形文字的破解过程来看,只能说是一家之言,而不能肯定地说已经成功破解,已经揭开了真相,或许恰如学者金寿福在“发现和重构古埃及文明讲座纪要”中指出的“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维模式”一样,楔形文字的破解也是这样。
参考资料:《楔形文字是如何“死而复生”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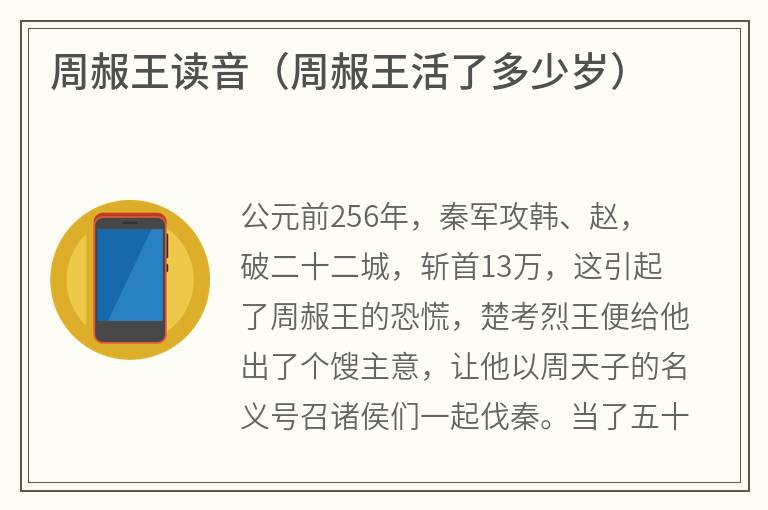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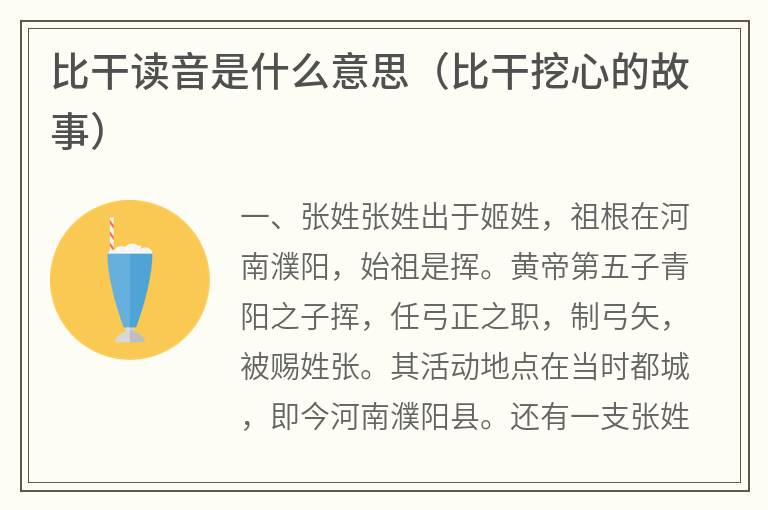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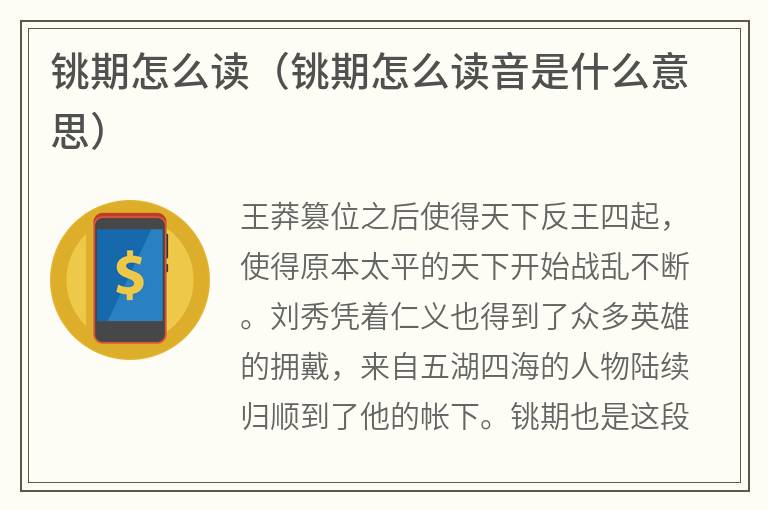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