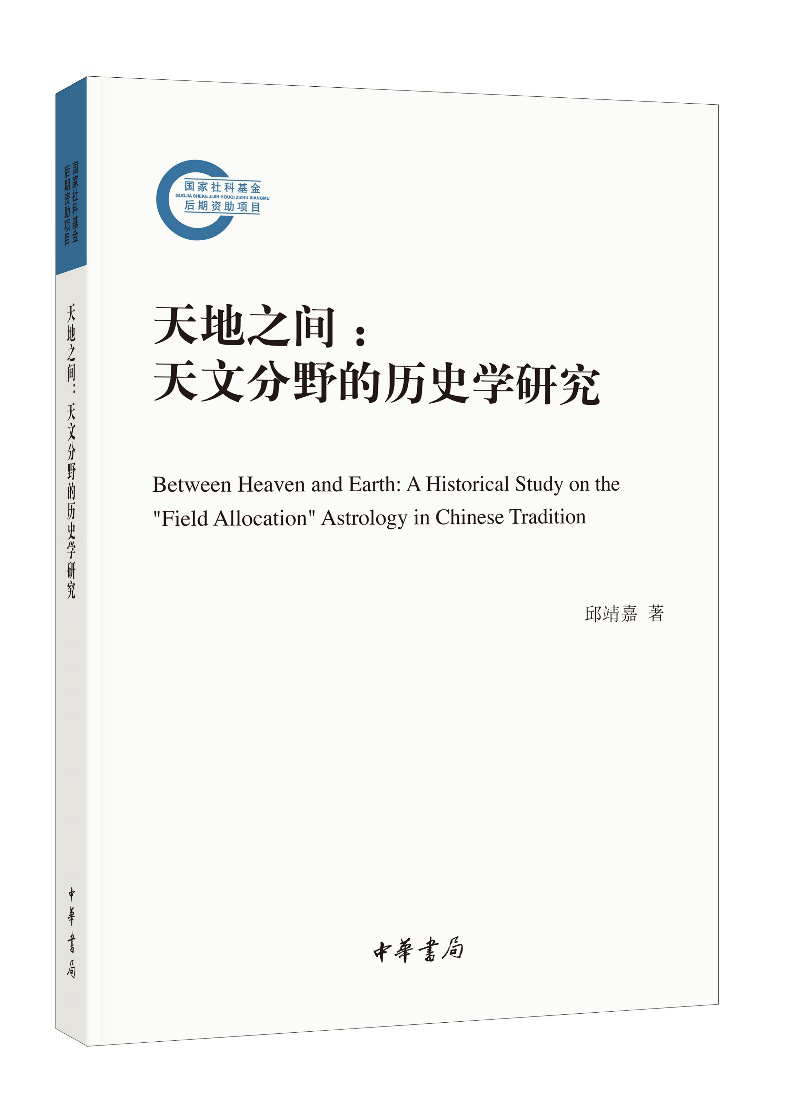
《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邱靖嘉 著,中华书局,2020)
关于本书
天文分野是由中国传统星占学衍生出来的一套认知天地对应关系的理论体系,它既是传统星占学的理论基础,又是古代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又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与世界观,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书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首次对中国古代天文分野的历史演变、理论模式及其政治文化涵义做了系统研究。全面梳理了天文分野学说的起源、释义和理论类型,重点考察影响最大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体系的形成、定型与衍变,以及在古代王朝政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折射出的天下观思想,进而透过天文分野的视阈对东西方世界观试作比较,体现出一种全球视野。
关于作者

邱靖嘉,男,1985年生,浙江桐乡人。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刘浦江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2018年9月—2019年8月,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赴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一年。2020年9月—12月,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九期邀访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宋辽金史、历史文献学、科技文化史。出版专著《〈金史〉纂修考》,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发表各类学术文章三十余篇。
目录
绪论
一 选题之缘起
二 学术史综述
三 研究思路
四 研究内容
第一章 天文分野学说的历史与理论
第一节 分野之起源
第二节 “分野”释义
第三节 分野类型诸说辨析
第四节 历代星土分野学说
第五节 星土分野诸变种
第二章 “十三国”与“十二州”:释传统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说之地理系统
第一节 “后战国时代”的文化地理观念:十三国分野系统
第二节 “大一统”的政治地理格局:十二州分野系统
第三节 二十八宿分野地理系统的整合与定型
第四节 十二次分野说之衍变
第五节 传统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体系的方位淆乱问题
第三章 传统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体系之革新
第一节 “以山川定经界”:古九州分野系统的地理学解析
第二节 “山河两戒”:一行分野学说的思想与理论
第三节 黄道十二宫与传统分野体系之融合——兼谈黄道十二宫中国化问题
第四章 “依分野而命国”:中古时期的王朝国号与政治文化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禅代型王朝建国之分野依据
第三节 自立型政权国号的来源
第四节 “依分野而命国”的政治文化涵义及其余绪
第五章 天文分野说之终结
第一节 “分野”之末路
第二节 传统政治文化崩溃与分野说的消亡
第三节 西学东渐:西方科学对分野学说的冲击
第六章 “普天之下”:传统天文分野说中的世界图景与政治涵义
第一节 “中国即世界”:从分野说看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内涵
第二节 疆域主权与政治臣属:分野学说的政治涵义
第三节 中国传统世界观转变问题再探讨——基于中国的立场
第七章 天文分野的全球视阈——东西方世界观之比较
余论 天文分野说与传统地理学的结合
附录 李淳风《乙巳占》的成书与版本研究
主要征引文献
后记
余论(部分)
通过以上各章的研究可知,自战国秦汉以来,传统天文分野学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涉及政治军事、历史地理、学术知识、思想文化、中西交通等诸多问题。笔者在绪论中已交代,本书并不是有关天文分野面面俱到、教科书式的研究,而是选择若干前人不曾关注或研究不足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本书论述内容的散漫,实际上,各章之间既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又各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第一章全面梳理中国古代天文分野学说的起源、释义和理论类型,这是研究天文分野最为基本的一些问题,必须首先予以厘清。尤其是关于各种分野学说的清理,是一项很基础的工作,尽管前辈学者已有不少总结、归类,但其对历史文献记载的蒐讨并不彻底,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经笔者搜抉整理,共发掘出包括星土分野及其变种在内的历代分野学说多达二十二种,并对每一种分野说的源流和内涵加以辨析。在历代分野说中,二十八宿分野与十二次分野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两种分野理论。此二者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而前人研究讲得都比较简略,有许多疑难问题尚待解决。譬如,二十八宿分野与十二次分野分别是如何形成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次所对应的十三国、十二州地理系统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地理格局和地理观念,其后又有什么衍生变化。这些问题都需详加论证,于是便有了第二、三章对传统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说的专题考察。以上三章为本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传统分野说之所以广泛流行,其最重要的社会功用就是通过天地之间的对应,将天象灾异落实到地理空间,并借助星占学的解释,进而影响人间政治。自战国秦汉以至隋唐,分野星占与王朝政治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这是研究天文分野无可回避的核心议题。不过,在这方面,前贤时彦已有许多个案研究和精彩论述,笔者并不打算重复前人的研究路数,对某些具体的分野星占实例作单独考察,而是选择了一个相对宏观的视角,从贯穿于整个中古时代的“依分野而命国”思想出发,分别考索诸多禅代型王朝和自立型政权的建国历史与国号来源,然后再进行综合分析,以期发前人未发之覆。因此,第四章便从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说的理论研究延伸到王朝政治的层面,以专论的形式回应分野与政治这一核心议题。
正所谓原始要终,既知分野之起源及其兴盛,也应知其衰亡之势。曾经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遍流行的传统分野学说是如何走向末路的,这也是研究天文分野的一个基本问题,但此前缺乏系统论述。其实,自宋代以降,不断有学者对传统分野说提出各种质疑和批判,并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股否定分野的思潮,最终导致乾嘉以后分野学说被彻底摒弃,这一发展脉络正可与第四章所论中古时期天文分野直接影响王朝政治的情况相接续,并凸显其巨大反差,从而折射出社会思想之变迁。
此前学者对于天文分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野学说的起源、理论体系、地理系统、星占应用、政治影响等方面,如何进一步拓展天文分野研究的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深层问题。第六章从思想史、观念史的层面,探讨传统天文分野说中的世界观念与政治涵义,就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而第七章更是跨出了分野研究的中国边界,试图将古代世界诸文明中的类似天地对应学说纳入考察视野,进行比较研究,以期窥探东西方世界观之差异,不过因笔者学力所限,该章所论仅仅是一个很粗浅的分析,与其说要得出什么结论,毋宁说是提出问题、抛砖引玉、启发思考,希望能够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总之,本书研究虽各设专题,但又自成体系,仍不失为一部系统研究天文分野的专著。此外,绪论亦曾交代,“分野”此前多归入天文学史的范畴,属于科技史的研究领域,而作为历史学者,本书研究区别于科技史家论著,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寻求天文分野与各方面社会历史相交叉的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综观各章,关于分野学说起源、释义和理论的梳理,主要基于历史文献学的分析;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地理系统的考察,则属历史地理问题;传统分野说对中古时期王朝政治的影响及其走向衰亡的根源,与政治文化有关;历代分野体系所呈现出的中国古代世界观、天下观及其变迁,又是思想文化方面的议题;黄道十二宫与中国传统分野体系的结合,明清时期西方科学对分野学说的冲击,中外天地学说之比较,皆为中西交通、中外关系史的考察内容。由此可见,本书旨在突破传统科技史的研究框架和视野,在大历史中充分发掘天文分野研究的广阔空间、多重面相和重大价值,这既是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同时也是科技史回归历史的必由之路。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作一补充论述。前文提到,天文分野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常被纳入地理类文献的纂述之中,成为一种地理学常识,多见诸古人诗文。在清代科学的经纬度知识和地图测绘技术推广之前,人们甚至还认为可以依靠天文分野来辨识地理方位。我们知道,天文分野最初起源于星象占测,那么它究竟是如何与传统地理学相结合,进而深化为古人的一种地理观念呢?这个问题本书各章虽时或有所涉及,但均未展开论述,故需在此加以集中解释。
战国时期,由于星象占测的需要产生了天文分野之说,至汉代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理论体系形成时,也是作为星占学思想而出现的。如二十八宿分野之十三国地理系统始见于《淮南子·天文训》,二十八宿分野之十二州地理系统首载于《史记·天官书》,目前所见完整的十二次分野说最早出自费直说《周易》,皆与天文星占相关。分野学说首次与地理学的结合是西汉末刘向所言“域分”,今见于《汉书·地理志》。它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分野区域,分别记述各地的人文地理状况。因《汉书·地理志》是第一部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影响巨大,使得这套分野体系广泛流行,被视为汉代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二十八宿分野学说,同时也将天文分野与区域地理联系起来,这是天文分野与传统地理学的初步结合。
不过,《汉书·地理志》所记分野体系只涉及较大范围的地理区域划分,尚未深入到在此之下的郡国层级,至西晋陈卓厘定二十八宿分野说,进一步将天文分野体系加以细密化。据《晋书·天文志》所记陈卓“州郡躔次”,在十二州系统之下,又析分星宿度数以对应诸州所辖郡国,从而使分野区域细分到郡、国一级政区,标志着传统分野理论更趋细密化。而且分野体系的这一新变化很快便在西晋地理总志的编纂中得到反映。《隋书·经籍志》记云:“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挚虞所撰《畿服经》虽早已亡佚,但据《隋志》可知,此书记述西晋全国州、郡、县三级政区,即包含有各地分野的内容,从《隋志》表述及陈卓“州郡躔次”来看,其分野划分的细密程度至少应到郡国层级。由此,天文分野与传统舆地之学更为深入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不过,西晋以后,地理文献记述天文分野还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据今所见,《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郦道元《水经注》等南北朝时期代表性的地理著述均不记各地分野,惟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记载巴、蜀、汉中的地理形势,提及分野对应之星宿。这说明此时在地理纂述中,天文分野尚未成为一个必要元素。直至唐宋时期,天文分野才逐渐完全进入地理志书的编纂体系之中。
后记
终于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增订修改完毕,可备付梓了。此刻回首自北大求学以来的学术经历,感慨良多,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幕幕难忘的场景,愈加怀念我的授业恩师刘浦江教授。
2007年考研,我跨专业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当时尚对历史学懵懂无知,承蒙刘老师不弃,将我收入门下。刘老师以研治辽金史名家,所以我入学后在先生引导下也逐渐进入了辽金史研究领域。2010年,我又继续跟随刘老师攻读博士学位。然而我的博士论文却选定了一个与辽金史完全无关的题目,可能许多师友会感到有些诧异,其实这背后有着刘老师对于指导学生的深邃思考和长远规划。
博士论文作为青年学者的起家之作,对今后一生的学术发展和研究领域的确立往往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因此博士论文的选题不能只盯着毕业、求职的眼前利益,而必须深思熟虑,要有长远的学术眼光和发展规划。在刘老师看来,博士论文选题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比较一般性的题目,此类选题往往针对性强,四平八稳,时代、问题和材料的边界都很清楚,难度较低,只要肯下功夫全面搜集史料,认真写作,基本可以确保顺利毕业,但不容易出彩;其二是具有挑战性的题目,这里所说的“挑战性”可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采用全新的视角研究某一传统议题,或是在前人已有充分讨论、形成定论的领域继续开拓进取、推陈出新,或是就某一宏观问题开展长时段、多面相的具体研究,等等。此类选题往往具有跨断代、跨区域、跨领域、乃至跨学科的特点,时代、问题和材料的边界都相对模糊,并不确定,这就对研究者的学术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难度和风险都比较大,有可能延期毕业,甚至完全失败,但如果研究成功,则必定是一篇出类拔萃的优秀博士论文。刘老师指导学生因材施教,会根据学生的禀赋特点、兴趣专长和学术能力选择适宜的论文题目,我与陈晓伟同届读博,大概先生觉得我们两人的研究能力尚可,故倾向于让我们做有挑战性的博士论文选题。不过,在具体的选题方向上,我俩又有所不同。
刘老师认为,中国古代史学者最理想的学术成长路径是首先成为某个领域(如某一断代史或专门史)的专家,占据自己的学术阵地,然后再逐步向外扩展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最终在某方面研究中贯通整个中国古代史(乃至中国史)。若针对我等辽金史方向的青年学人来说,则应先在辽金史研究领域站稳脚跟,然后根据个人兴趣打通宋史或者蒙元史,最后再开辟一个能够贯穿中国古代史的全新领域作为兼治对象,而这种开拓精神和贯通意识又必须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即开始着力培养,那么博士论文的选题便是决定能否达到这一学术训练目的的关键。我与陈晓伟长期参加刘老师主持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修订项目,共同研读《辽史》,硕士论文做的也是辽史方面的题目,已具备独立从事辽金史研究的能力,因鉴于此,刘老师并不打算让我们再做纯辽金史方向的选题,而是希望能够走出辽金,开辟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具体而言,陈晓伟专擅民族史,博士期间曾前往内蒙古大学学习蒙语,有一定的民族语文基础,故刘老师对他的学术规划是打通辽、金、元,进而研治北方民族史,后来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北族王朝行国政治研究,即由辽金入蒙元,且兼及其他游牧民族,做出了很好的研究成果。而我因为花费一年时间做《辽史·历象志》研究,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有所涉猎,并撰写发表了两篇与此有关的文章,所以刘老师觉得我不妨趁热打铁,选择与科技史相关的题目,以后可将科技史发展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回想起来,定下这一选题方向,已是博士一年级末,既然先生如此交代,我自然惟命是从,但当时我对具体的研究题目尚无任何概念,对于能否做出博士论文也缺乏信心。
2011年暑假,我大量阅读了天文历法方面的论著,希望从中找出一个合适的研究题目。在此期间,我与刘老师也有过数次邮件或电话讨论,但始终未能落实明确的选题。直至秋季开学后,记得9月下旬某天中午,刘老师与我坐在北大图书馆北侧的长椅上又谈起论文选题一事,我向他汇报了暑期读书的情况,他突然提到天文分野,问我有没有了解。我急忙回答道,之前看书主要都集中在天文历法方面,对于分野虽略知一二,但并未查看过相关论著。刘老师随即说,纯天文历法的研究需要有理科背景,掌握推算技术,此非我所长,建议我应当从历史学的视角去研究科技史,天文分野涉及历史地理,不妨去仔细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研究余地。于是我谨遵师命,赶紧回去查阅有关天文分野的论著,一个月后,我回复刘老师说,目前已有的分野研究都比较简略,缺乏系统论述,迄今尚无专著问世,我想可以将天文分野作为研究主题。至此,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才最终得以大致确定。当时,刘老师给我定立了三个基本要求:第一,一定要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利用尽可能丰富的各种文献材料;第二,做长时段的通代研究,但不要面面俱到,突出问题意识;第三,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科技史与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等相结合。他希望我通过做这篇博士论文,拓宽知识面,扩展学术视野,锻炼思辨能力,熟悉各个断代的基本文献史料,今后将古代科技文化史作为长期兼治的对象。这番期许其实就是我博士论文研究的主要宗旨,在努力践行的过程中,我感到获益无穷。
后来,在具体的研究与写作中,刘老师亦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每当我遇到困惑,都会向先生请教,尽管他并不研究天文分野,但仍会给出重要的建议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当我写出各章初稿后,刘老师都会仔细审阅,提出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包括我的论文标题《天地之间: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也是先生亲自拟定的。可以说,我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到最后成稿无不浸透着刘老师的心血。然而不幸的是,2014年3月刘老师查出癌症,接受治疗,以致无法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不过,当年我与陈晓伟的论文双双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可说明先生用心指导学生论文选题的成功。2015年初,先生与世长辞,无法见到本书出版,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此时此刻,我心中充盈着对刘老师无尽的感激和思念。
在做博士论文期间,我还很荣幸地得到了校内外诸多老师的指点和赐教。邓小南、辛德勇、张帆、党宝海、叶炜、李新峰、赵冬梅老师参加了我的论文开题、预答辩或正式答辩,给予我许多有益的指导和启示。我曾登门拜访李孝聪教授,请教天文分野方面的问题,李老师提出了很宝贵的意见,并惠赐相关天文分野的图像资料。此外需特别提到的是,经军事科学院钟少异老师介绍,我联系上时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的孙小淳老师(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孙老师是从事天文学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慨然允许我参加他的天文学史研讨班,并引荐我参与天文史学界的学术活动,后又担任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孙老师非常注重科学逻辑思维的训练、问题意识的培养以及跨学科视野的开拓,令我受益匪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李勇研究员是国内研究天文分野的专家,他欣然接受邀请,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并对我的研究给予鼓励,提出重要意见。我谨在此向以上诸位师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方平老师为我查阅文献、复印资料提供了诸多便利。康鹏、林鹄、桂始馨、曹流、高宇、陈晓伟、任文彪、肖乃铖、陈捷、苗润博、张良、乐日乐、赵宇、张思远等诸位同门,以及孙昊、魏聪聪等学友,在我北大期间的学习生活中给予很大支持和帮助。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就读的吕传益、储姗姗、杨帆、石爱洁、李伟霞、刘宜林、吴玉梅、肖尧等同学也为我学习天文学史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一并向以上诸位师友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订修改而来的。其中,正文第四章和余论部分为新增内容,主要写成于2018—20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感谢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的访学邀请,使我得以利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开展研究。附录《李淳风〈乙巳占〉的成书与版本研究》则撰写于2020年夏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其余各章在原有基础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修订,第二、三、五、六章的部分内容此前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但有大幅删减,本书则保存全文。第七章原为我博士论文的代结语,介绍中国以外古代世界诸文明中类似于分野的天地对应学说,并尝试比较东西方世界观之差异,老实说,这一部分只是提供了一些很粗浅的分析思考,并无深度,原本我打算在毕业后对世界古代诸文明中的天地学说进行深入研究,重新撰写,但工作后却发现时间和精力严重不足,很难再像研究生时期那样可以鼓足勇气、集中全力去钻研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于是只好暂且作罢。最近在整理文稿时,我曾一度想删去这部分内容,但又转念一想,当时我的确是下了一些功夫做相关研究,如为解释古埃及《维也纳世俗体交食征兆纸草书》残卷所记星占学说,我专门旁听了一学期颜海英教授的古埃及史课程,且对托勒密星占学著作《四书(Tetrabiblos)》记载的分野说也有所研读,故删之又觉可惜。后来决定将此部分列为本书第七章,其意旨在提出问题,提示一个天文分野研究可供延展的新方向,以引起学界注意,就此话题展开讨论,希望感兴趣的学者能做出更好的研究。此外,我的博士论文原本还附有一份《传世天文分野图录》,收录历代天文分野图一百六十余幅,今本书删此附录,容日后另行整理。
本书由中华书局推荐申请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获得立项资助,感谢徐俊、罗华彤先生对本书的大力支持以及责编樊玉兰老师付出的辛劳。书中论述恐有不周及疏失之处,敬请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外婆、父母和妻子骆文长期以来对我学习、工作和学术研究的理解与支持,书中有多幅插图系由骆文帮助绘制而成。
2020年秋季学期,我幸运地成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第九期邀访学者,重回北大静园二院,本书的出版和校对工作恰巧进行于此时,这令我十分感慨。拙著始于北大,又终于北大,可谓是给我的博士学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斯人已去,不能再聆听刘老师的耳提面命,不禁唏嘘潸然。伤感之余,回想起刘老师对我的学术规划和期望,吾惟觉“任重而道远”。
2020年10月12日
写定于北大静园二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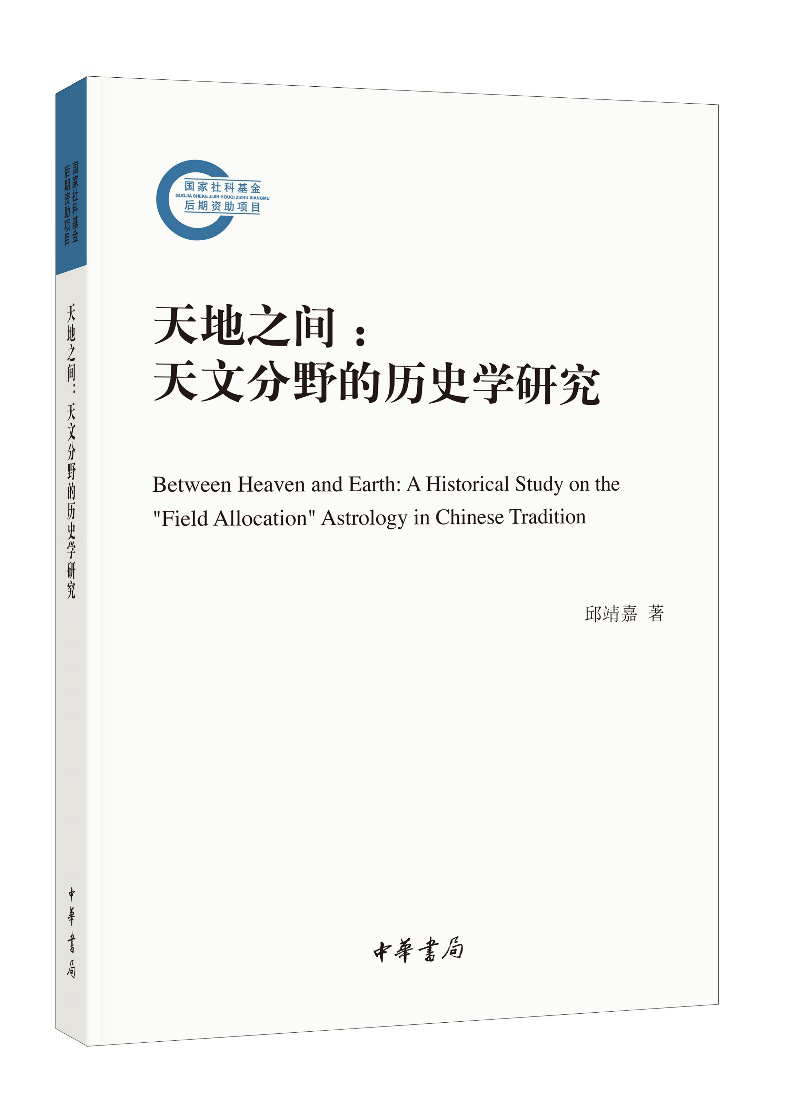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