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书香上海”设为置顶星标
让书香与您常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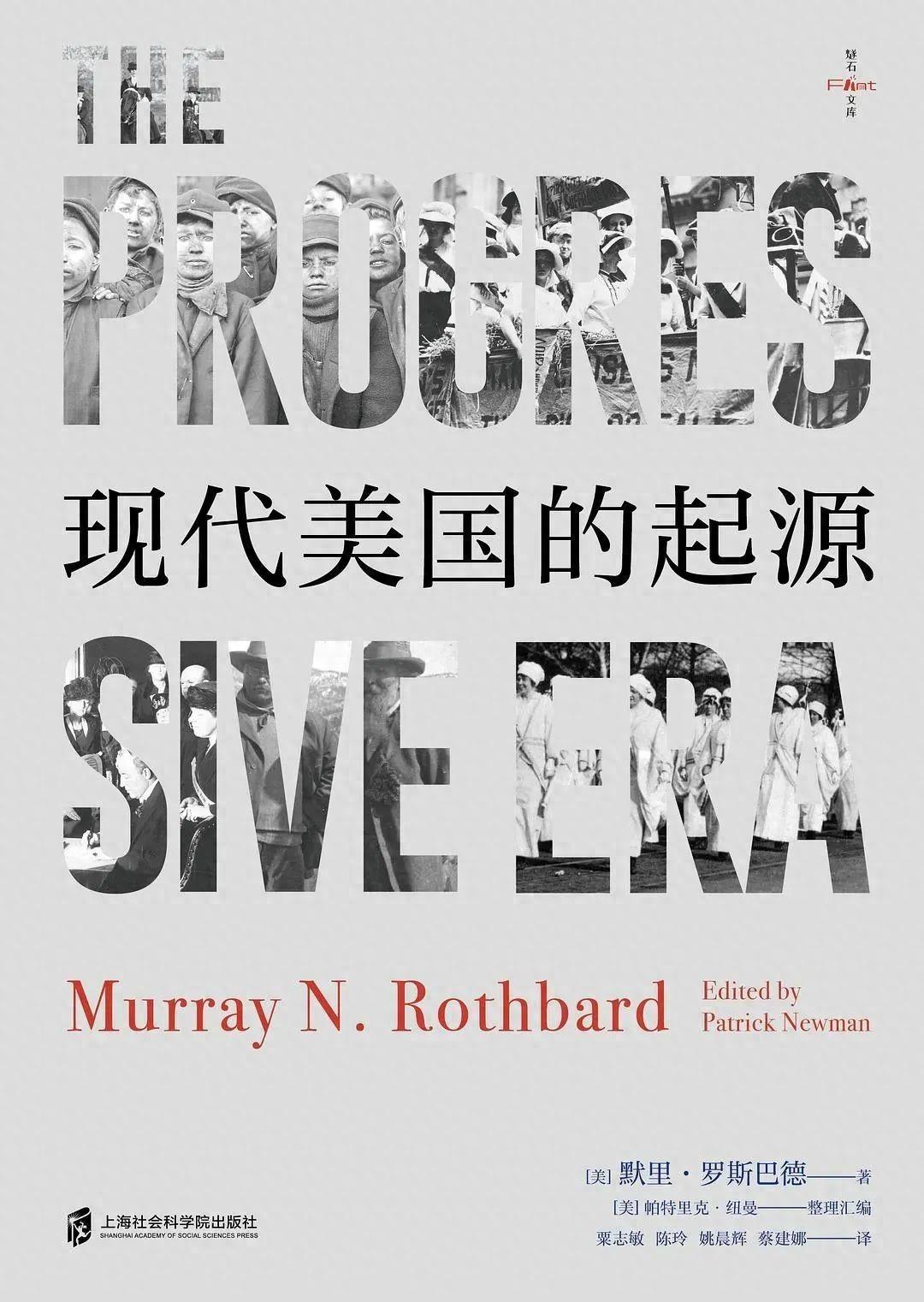
《现代美国的起源》
粟志敏、陈玲、姚晨辉、蔡建娜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默里·罗斯巴德和新左派史家一样,罗斯巴德用以描述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法团主义国家”(corporate state)。对中国读者来说,“法团主义国家”不算是一个常用概念,在熟悉它的人们眼中,最典型的“法团主义国家”或许是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新左派倒并不认为美国这个“国家”已与法西斯无二,因此他们又发明了“自由法团主义”这个概念用以描述美国,与法西斯国家的“独裁法团主义”相对。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阐释,自由法团主义指“与议会、政党和代表制选举并存的政治过程和制度……其基础是职能代表,即是说,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各种组织,被政府当局允许在商讨政府政策过程中拥有特权地位……”。用罗斯巴德的话来说,所谓“进步主义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的本质,其实就是大企业(Big Businesses)借政府之推手实现联合(cartelization),在此过程中大企业与大政府(Big Government)、大工会(Big Unions)结成了联盟。结果是美国“从一种自由放任的(laissez-faire)经济体变成了一个福利-战争国家(welfare-warfare state)”。
罗斯巴德将美国进步主义时期发生的这一系列发展过程称为向“国家主义”(statism)的转变,此一转变虽近乎“实现”了温斯坦所说的“法团主义理想”,却给二十世纪的美国带来了各种破坏性后果。值得注意的是,从罗斯巴德书稿的前言看来,他认为“知识分子、技术专家和专业人士”在促成美国这一转变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与大企业同政府的合谋几乎是同等重要的。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就是新左派史家詹姆斯·吉尔伯特(James Gilbert)笔下的“集体主义知识分子”(collectivist intellectuals),或是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所说的“新阶级”(New Class,见中译本“前言”第3页)。原书手稿第五章的标题是“科学与道德:信奉法团主义的知识分子”,足见罗斯巴德曾计划专文论述进步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文化。鉴于罗斯巴德本人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我们也许可以期待那会是一份上佳的关于二十世纪美国智识文化的研究,或许能媲美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尽管奥地利学派对于德国实证主义史学颇有反对,但米塞斯自认为“行动学”是一种近似于历史主义的方法论素养。比如,“行动学”对于人的行动的“时间性”的重视就与历史学的关注点几乎重合。此外,“行动学”强调行动的个人所具有的知识是“有限的,异质的、分散的、私人的和隐含的”,因此很难对行动的结果加以预期。基于此,奥地利学派认为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是不存在的,他们要研究的是“真实的人”,这也深合历史学家的智识取向。罗斯巴德所构建起来的进步主义时期社会上层的人际网络,可以说正是当时多数人的知识盲点。“耙粪者”们通过明察暗访,或许也能对一些隐秘的社交关系进行曝光,但他们的揭发是零散的,难以对“权力精英”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行整体图绘。而罗斯巴德所提供的这一图绘的直观效果之一,是使得霍夫斯塔特所提到的大企业董事会成员“交叉任职”(interlocking)的现象变得一目了然了。当然,罗斯巴德的这种“情意学”路径与历史学研究本身仍有较大不同。比如,“情意学”要求尽可能充分地掌握历史人物的背景性资料,这意味着它关注的人物只能是精英阶层,在罗斯巴德的“历史学”研究中很难看到具体的、有名有姓的普通人(他们的确常以数据的方式出现),这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历史学的社会史取向是很不一样的。
这一底层视角的缺失,似乎使得罗斯巴德低估了普通民众在美国走向“国家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影响。此处已触及本书最本质的学术史定位:一份出自奥地利学派、反映“自由意志主义”政治见解的关于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政治、社会转型的批判性研究。因此,尽管本书的观点与新左派历史学家有相似处,其批判的出发点和结论则与之大相径庭。新左派揭露政府与商人的共谋,是为了批判资本的伪善,背后的动机近似于马克思主义,他们为美国社会开出的药方是更大程度的平等、更完备的福利和更大规模的政府。这些正是哈耶克所反对的内容,也是罗斯巴德不可能接受的,他们的批判意在警醒世人:国家主义的泛滥对于自由市场会造成何等严重的毁坏,一旦国家的性质变为“福利的”,似乎就必然与“战争国家”捆绑在一起!尽管本书没有结论,但罗斯巴德早已在其他著述中疾呼,美国的出路在于重树“自由放任”原则,这显然是一种越来越稀有的“老右派”主张。但他的药方对于已成为“一项冷战遗产”的美国政府来说显然是过于苦口了。虽然经过罗斯巴德本人和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等经济学家的努力,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在1970年代以后在欧美学界受到了更多重视,但新古典主义的主流地位依然稳若泰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甚至称其为“糟糕的经济学”。
而在政治上,罗斯巴德和他所代表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崇奉者们,由于其坚定的和平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立场,在美国保守主义阵营中也处于边缘地位。可是到了今天,当“进步主义运动”已过去百年,由于资本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国际地缘政治逻辑的奇特发展——这种波谲云诡的不确定性正是令奥地利学派感到兴奋的——美国的国家主义和整个政治文化似乎面临着比以往历次危机都更为严峻的形势。政治本身的衰朽与混乱,似乎正使得一种处在休眠状态的政治意识形态焕发生机。美国的共和党人、保守派、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或许因为自身哲学的贫困,如今也将信将疑地在自由意志主义这口井中汲取合法性的源泉,罗斯巴德等人创立的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也开始扮演一个智力中心的角色。本书编者帕特里克·纽曼即是这一思想背景下渐渐升起的一位学术新星,他有两卷本的美国经济史《任人唯亲》(
王禹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资料:上海书评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