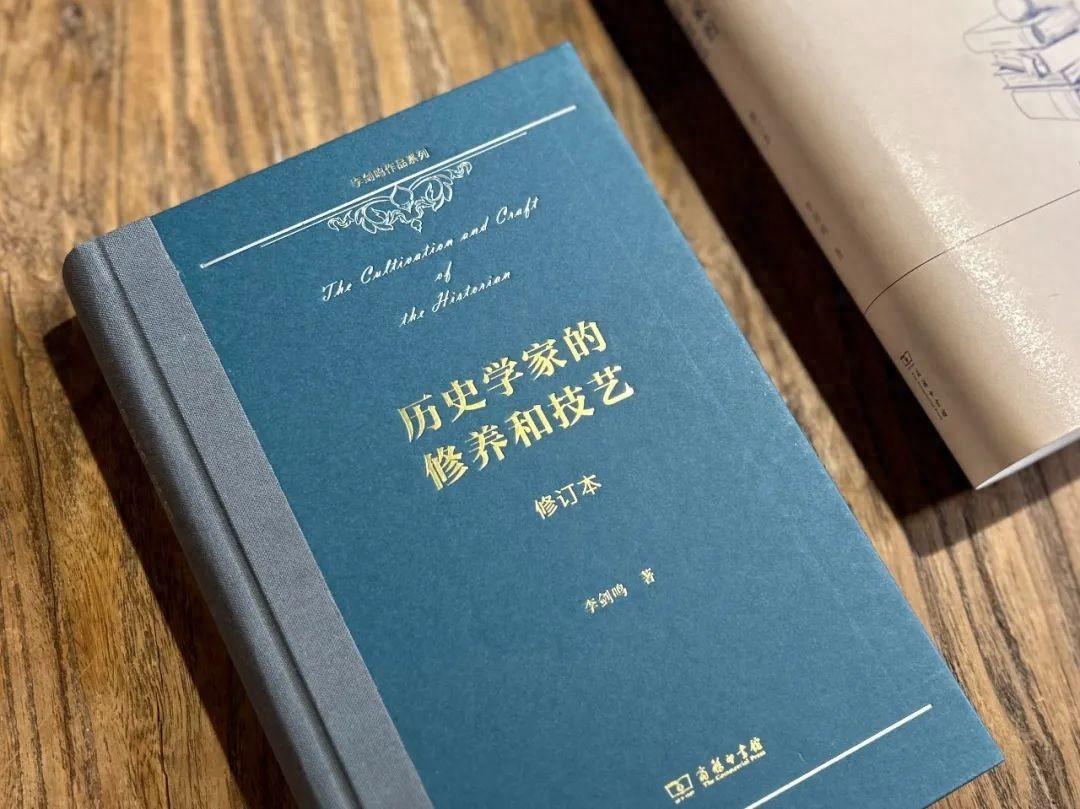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历史学家李剑鸣教授著作《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修订本)
不论从事什么学科的研究,对于这个学科的特点,对于自己工作的性质,多少都应当有一些了解。在其他一些学科,虽然研究者对本学科的内涵和性质并非漠不关心,但他们很少纠结于本学科“是什么”这一类问题,更没有像史学界一样,反复就“历史学是什么”掀起热烈的讨论。
历史哲学家和专业史家都曾为此花费不少笔墨,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近几十年来,欧美史学颇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这个话题再度成为讨论的热点,由此出现多种不同的新说。
反复纠缠于这样一个“入门”话题,难免使初学者感到费解和沮丧;不过,这也说明史学可能确实具有某种复杂性和特殊性。初学者既有志于治史,就有必要明了史学的特性以及它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对于理解和奉守专业主义原则,选择适当的研究路径,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和规范,或许是一件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
专业化之路
史学乃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中国如此,在欧洲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也是这样。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还拥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在欧洲,只有史学、数学和天文学在成为制度性的学科以前,就已经独立存在了两千多年。而且,史学还孕育了其他一些新的学科,因而有“母学科”(mother-discipline)之称。
但是,史学作为一个专业化的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的学科,又是相当年轻的,与众多后起的学科并没有多大的分别。在知识体系和教育制度中,史学长期没有独立的身份,写历史的人大多是业余爱好者。
换言之,史学长期只是一门学问,而不是一个学科。史学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或学科化(disciplinization),最先在19世纪出现于欧洲,进入20世纪后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专业理念、专业规范和专业技艺,大多也是在专业化过程中或专业化完成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中国自上古便有史籍留传,而史之为学,则是汉代以后的事。古代史官的主要工作,是记录上层当权者的言行,所谓“君举必书”,“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但记史不等于治史,史官也不完全是历史学家。他们所留下的记述,自然就不能算作史学论著,而只是刘知几所说的“当时之简”。
在史学的形成中,司马迁和班固厥功甚伟。清人钱大昕评论说:“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不过,在司马迁和班固生活的时代,史学还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知识门类。
《汉书·艺文志》梳理古代学术源流,依循刘向、刘歆父子把《史记》归入“春秋”的先例,将多数史籍列在“春秋”名下,而未专设史学一目。三国时魏人荀勖作《中经》,把书籍分成甲、乙、丙、丁四部,史籍归入丙部,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东晋人李充整理各类书籍的目录,调整了乙、丙两部的位置,将史籍置于经书之后。到梁元帝时,已有“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目。这反映了魏晋时期“经史”分离、史学独立的实际。《隋书·经籍志》依例而行,用经、史、子、集“总括群书”,以史部居次,进一步肯定了史学地位的上升。
《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著作817部,共13264卷;若包括亡佚书籍,则卷帙更为浩繁。“从东汉到唐初,民间史家也为数众多,富有文学修养的文人撰史成风,即便官书正史,也多由文人主笔,史官的地位随之下降。

从唐朝开始,国家控制正史的编纂,官修国史成为定制。唐宋是古代史学成就十分突出的一个时期,不仅史书的纂修富有成绩,而且在体例与理论上也有新的变化,专业技艺和规范随之发展。但严格来说,修史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古代史学和现代史学之间,在内涵、范式、材料、方法和旨趣各个方面,均有许多的不同。
及至清代,史学的专业技艺和治学规范又有新的进展。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清人章学诚颇为推重,赞许其著作“寓意深刻”,对史学的原理、原则有着独到的思考。梁启超则径直称章学诚为“集史学之大成的人”。在一定意义上,章学诚的思想昭示了史学专业化的前景。他张扬史学在知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强调史家要有独立见解,称治史重在阐释历史的意义,即“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
不过,章学诚的言论既不见重于当世,也颇受后来学者的贬抑。相对而言,清代学者的治学实践,对史学的专业化是一种更直接的推动。梁启超对清代所谓“正统派”的学术特色做了总结,推许这些学者的专业意识,肯定他们在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上的建树。
梁启超认为,这些学者“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反对“隐匿”或“曲解”证据,并重视比较研究;对前人学说加以“明引”,以“剿说”为“不德”;为学喜相互商讨辩难,在争鸣时则“词旨务笃实温厚”,“尊重别人意见”;“文体贵朴实简絜”。
照此说来,清代前期的史学已初步具备专业主义精神。不过,中国史学并未在清代完成专业化,这个进程的最后几步,是民国时期在欧美史学的推动下走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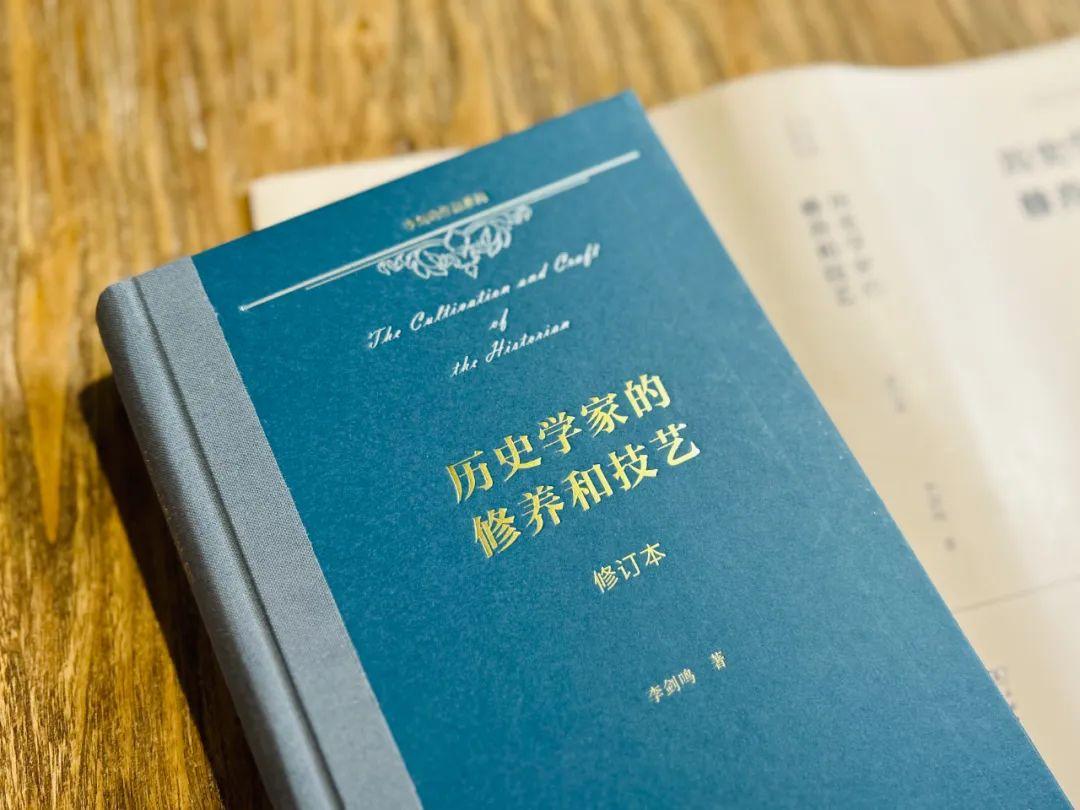
欧洲史学起源于远古的传说和歌词,到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时代,开始出现整理史实、组织叙事、探讨原因的意识、规则和技巧。不过,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史学一直笼罩在哲学、文学和神学的影子里,虽然编年史书为数不少,但治史的规范和技艺,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发展,史学的学术特性尚未形成。
史学和其他知识门类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尤其是与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和神学纠缠不清。18世纪的伏尔泰仍把史学视为哲学;到19世纪,英国史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还有心与时髦小说家一争高下。
美国学者查尔斯·比尔德曾说:“历史学已有各种叫法:一门科学,一种艺术,一种神学的例证,一种哲学的面相(phase),一个文学的分支。”史学名号繁多,归属不定,正说明它在学术上还没有取得确定的身份。作为史学主体的史家,不仅不具独立的职业身份,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史学当作政治、道德或娱乐的工具。
在欧洲史学成为独立的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法国和德意志的学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博学时代”的法国学者,在史料、领域、方法和学风各个方面,都对史学的发展大有推动。
英国史学史名家乔治·皮博迪·古奇特别推崇德国的巴托尔德·乔治·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称赞“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独立科学”。
利奥波尔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更是功不可没。他不仅发展了尼布尔考订史料的方法,而且构筑出一套史学的研究范式:强调事实的确定性、细节的精确性和当时人记述的权威性,反对将个人情感和偏见掺杂在历史解释之中。这样就使史学同传说、文学及哲学彻底分家。
兰克的主要著作《教皇史》以“客观叙述”和“资料丰富”而闻名,而兰克的学术也成为19世纪史学专业化时期欧洲史家的典范。及至20世纪初年,德国史学界围绕卡尔·兰普勒西特(Karl Lamprecht)的《德国史》展开讨论,对兰克的史学范式发起挑战。
兰普勒西特本人主张打破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模式,拓展研究视野,向社会科学靠拢,以建立“新的历史科学”。这种呼声在德国受到正统派的压制,却得到一些美国学者的响应。随后,多国史学界出现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趋势。
李剑鸣作品系列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修订本)
李剑鸣著
本书系统而条畅地论述治史所应具备的修养、技艺和规范,并对史学的学科特性、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理解的意义、历史的用途等问题加以讨论,对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念也做了适度的回应。

李剑鸣作品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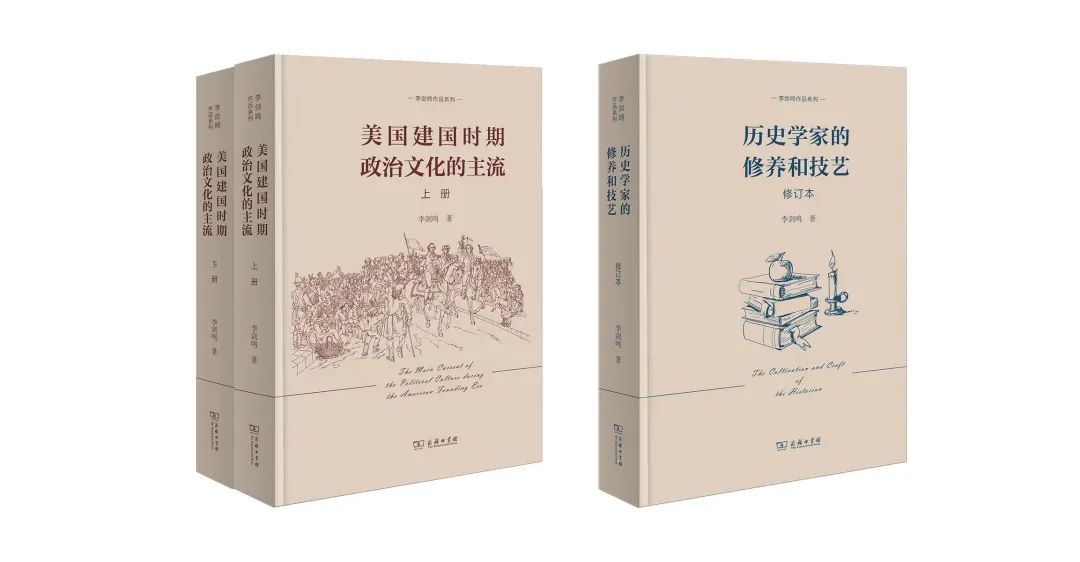
本书博采国内外史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基于丰富多样的史料和其他文献,借鉴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遵循由宏观而入精微的探讨方式,对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源流加以系统梳理,以揭示美国建国一代政治思维的方式、内涵及其意义,展现美国早期政治史上诸多纷纭复杂、变幻多姿的场景。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