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艺人的天职——评布洛赫》
“献给亨利·皮朗,他曾在铁窗内撰写了一部欧洲史。此时此刻,他的祖国和我的祖国正在为正义与文明并肩战斗。”——马克·布洛赫为自己在二战中另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写的献辞。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法国历史学家,专攻中世纪史,与好友吕西安·费弗尔同为年鉴学派(Lucien Febvre)的创始人。他们承继了上一代以皮朗为代表的史学家的学术成果,推进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开创了科学实证历史研究的新篇章。1944年布洛赫在参与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期间被纳粹逮捕,并于诺曼底登陆10天后被盖世太保杀害,享年不到58岁。

马克·布洛赫
在最开始我想先承认我的傲慢之罪。毕竟我究竟何德何能能给这样重要的一本书写评语?马克·布洛赫的鼎鼎大名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经常把其他历史学家的名字和布洛赫作对比以彰显那个历史学家的重要性。人们在介绍恩斯特·康特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的时候,会用“齐肩马克·布洛赫”来彰显他的学术成就。甚至于霍布斯鲍姆在介绍马克思与历史学的时候,也会专门提及布洛赫的大名并将他称为“唯一能和马克思并驾齐驱的人。”对于如此重要的史学大师在战乱年代中专门想要流传给后世的治世心德,我又怎敢妄加评判?布洛赫可是在书中专门教导我们不要尝试去当历史的判官啊!但是,这本书本身的精彩性,迫使我不得不在阅读之后写下一些东西,来表达出对这本小册子带给我的和它的体积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震撼。本文不会过多地介绍行文结构和内容,毕竟这本书篇章较为精小,感兴趣者大可以自己前往阅读,另外就算想省时省力,豆瓣上也肯定有远胜于我的总结。
这本书有两个标题。一个主标题:为历史学辩护;以及一个副标题:历史学家的技艺。乍看起来,这两个标题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张力。当一个人为一样事物辩护的时候,一般会将自己想为之去辩护的事物连接到某种可以,至少是部分可以,被认为为“真”的东西上。而本书的副标题,历史学家的技艺,则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布洛赫在本书导言部分的结尾说到:“我所呈现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是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对什么为“真“不感兴趣的工匠的形象。它不需要所谓的真理来指引自己的生活——他的手艺已经足以提供他所需的尊严。因此,我们就来到了那个以赛亚·柏林式的问题:布洛赫到底是有一位精通某一领域的刺猬型学者,还是一位多知的狐狸型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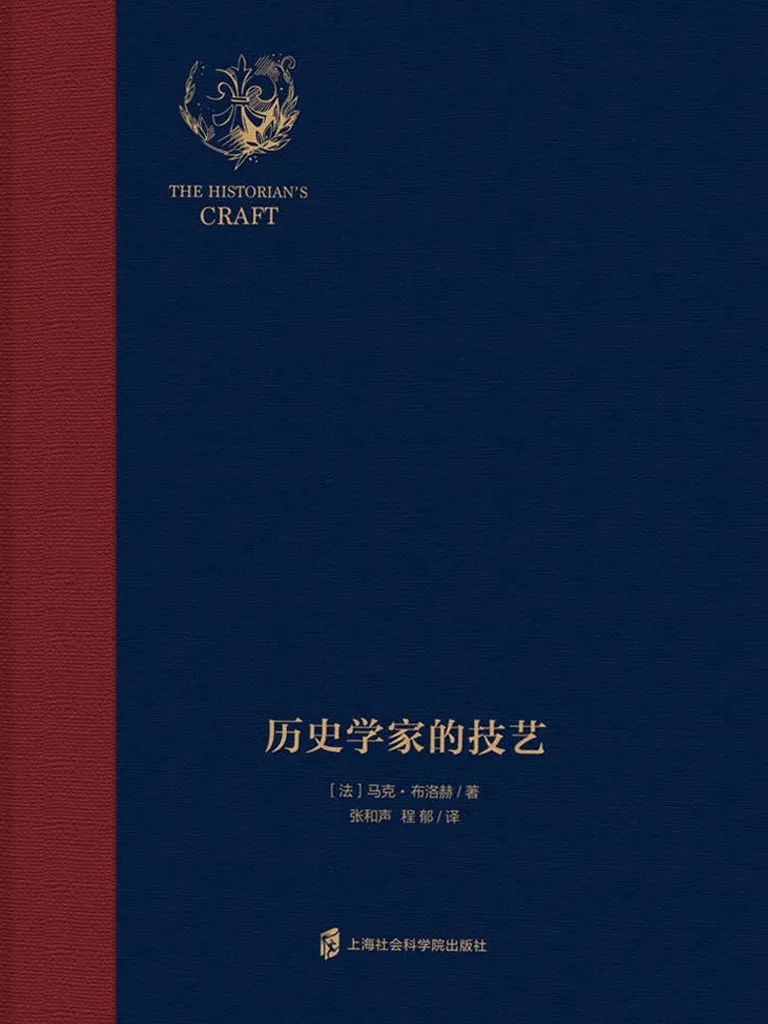
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
张和声 程郁 译
布洛赫本人是从前者入手来展开自己的小册子的。生活向他一次又一次的抛出了“历史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最为宠爱的小儿子向身为历史学家的他提过这个问题,在1940年战败的法国人也一次又一次的质问:“难道历史已经背叛我们了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历史本身的最大价值在于历史本身的魅力。历史本身的乐趣使得像莱布尼茨一样的大数学家都抛下了手头的微积分而去投入对古代宪章的研究。可是,单单基于此的历史,又跟喝茶打桥牌式的消遣有何区别呢?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历史本身就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科学的巨大进步已经使人类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相比于这个光明的时代来说,对于过去的一切研究,都只是消遣而已,不值一提。这两种倾向本身是基于同样的假设的——某种过去和现在的完全割裂。我们一般将前者称为古董迷,后者称为科学主义者。
要为历史作为一种科学辩护,最关键的是要破除人们对历史学家的最关键误解——需要去大声宣称历史学家不是单纯的古董迷。历史学并不是基于过去与现实的割裂的。恰恰相反,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将他们联系起来。布洛赫在书中举了他和皮朗之间的一段趣事(这个故事现在已经借助这本书变得如此又名以至于我的朋友黯天将这个故事与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及勒高夫的”历史哲学是历史学最坏的敌人“并列称为历史圈三大烂梗之一)。1928年,他们两个人同时被邀请参加位于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在到达斯德哥尔摩之后,皮朗却要求首先去参观斯德哥尔摩新市政厅的落成典礼。布洛赫对此感到十分费解。对此,皮朗解释道:“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对于布洛赫来说,历史是对符合如下特征的事物的科学命名:这个学科既关注死去的过去,又关注活着的当下。

亨利·皮朗,比利时历史学家,在《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中提出了著名的皮朗命题
因此,历史学从根本上就始终拥有着两个向度:过去与现在。这两个向度,同时也与布洛赫在前面批判的历史学的两大敌人相联系,构成了历史学这个独木桥两边的深渊:纯粹的实证与浪漫式的艺术。这样的平衡表明了历史学,不同于一般基于确定性的科学(不过就算自然科学在二十世纪之后也无法纯粹基于确定性了),是基于不确定性的。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势必是处于不断运动中的,因为历史研究所基于的那个现实生活也是在不断运动的。布洛赫在书中后续章节中对历史学的两大基本功,考证与分析的介绍,都是围绕着如何在这个独木桥上保持平衡而展开的。这也为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问题史学”奠定了基础。
那么,我们如此看来,布洛赫真的就是个纯粹的刺猬型学者吗?他说自己只是个手艺人仅仅是完全的自谦?并不是这样。对于布洛赫来说,历史学的精髓在于考证和分析的手艺。只有依靠这门手艺的成熟历史学家们才能屹立于两个敌人之间——既不倒向对历史的浪漫化追忆,也不直接消解历史的价值。也只有屹立于两个敌人之间才有可能使得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而这也正是历史学的价值所在——困在两边都是深渊的独木桥上的不光是历史学,还有那一个又一个的现代人。我们这个时代,正如同那个身处于浪漫主义时代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一样——这正是布洛赫身处其中的那个欧洲——处在一个看起无解的二律背反之中:一端是似乎一切已经被祛了魅的,以及位于历史的终点了的,完全被理性化的原则和权力所支配着的现代社会,另一端是最终似乎只能沦为在现实的生活中“嬉戏”,与真实的生活脱节的了对于“真”和“美“的追求。在不断的对自己的手艺精益求精的过程中,作为手艺人的历史学家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这也让我们可以回到对历史学本身价值的追问。历史学追求成为科学的旅途必然使其摆脱这两者,而对这两者的摆脱就会使人类在征途上更进一步。正是因为历史学的基础是现实的不完善,而我们目前完全不知道“完善“应该是什么样的(现代社会已经被无可避免的祛了魅了),因此历史学家无法承担起判官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布洛赫才会说:历史学的明灯永远是理解而不是评判。也是因为如此起源的偶像才如此有害——因为对起源的偶像的追寻本质上只是那种有害的判断癖的延申罢了。起源的偶像假设好像我们明白了一个东西的开端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这样的癖好同时踏入了深渊的两端:他要么假设了我们对历史演变的科学的完全的把握,要么用一种兰克式的手段将过去本身放在了神的位置上——“如实直书”本就是对神迹的赞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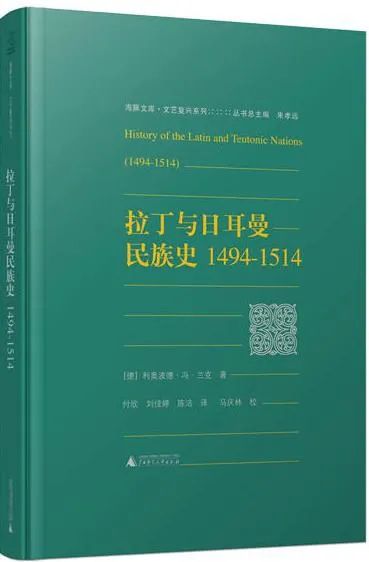
“如实直书”是兰克在他的成名作《拉丁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提出的治史原则
合格的历史学家既不是理性教徒也不是政治的浪漫派。历史学家的使命让其不可避免地同时面对面前和身后的敌人。正如本雅明笔下的新天使:它必须一边面对眼前过去的废墟,一边面对身后来自当下的那场名为进步的风暴。布洛赫在本书中反复表达过对于未来历史能够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的期盼——这样的期盼不是一种进步主义式的神话,而是一种对于拯救的可能性守护。在这个意义上,布洛赫才会说出:“因此,我必须请求宽恕。尽管罪不在我,但还是必须说:‘我服罪。’”当下的时刻感迫使布洛赫去做出这样的回应。原罪是自由的前提条件。
这本书的副标题:历史学家的技艺,技艺的法语原词是“métier,”我在机缘巧合之中才知道,这个词不光有工作技艺的意思,还有那种韦伯意义上“志业”“天职”一般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书的主标题和副标题最终联系到了一起——正是因为要通往拯救的彼岸,必须直面当下先知不再降临的现实。在直面祛魅的现实的斗争中,坚定自己对于拯救的信念——历史学家必须具有战斗性。在经历如此这般的漫长的战斗之后,这场探索——探索本就是“历史”的希腊语原意——才会最终达到这样的一个时刻。生活本身在其中浮现,并向遍体鳞伤的历史学家说出自己的真谛:“服从吧!你将因此获得自由!”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历史学家才能在生活面前大声说出那象征着拯救的自白:“我已经看清了你对我所施加的诡计以及我自己的命运了。除了你已经给予我的以及将要给予我的东西以外,我将别无所求。”

在法国拉鲁西永,布洛赫被处决处的烈士纪念碑,最左边那列从上往下数第四个铭刻有马克·布洛赫的名字
布洛赫何曾缺乏过战斗性!在祖国再次面临入侵的时候,他以50多岁的高龄再次入伍。前人的事迹一直在感召着他:皮朗就在一战被德军俘虏的时候写出过一本欧洲史啊!只可惜,布洛赫本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完成他的这个志向了。当德国人连最后一点生存的空间都不留给名义上的法兰西的时候——1942年轴心国占领了维希法国,布洛赫毅然加入法国地下抵抗组织。他也因此再也无法完成他设想的那本《欧洲文明结构中的法国史》以及本书了——1944年6月16日,布洛赫因为参加抵抗组织,在诺曼底登陆10天后被盖世太保杀害。本书的第五章,《历史的因果》,永远地停止在了那象征着未完成的由三个句号组成的省略号“。。。”上。
正如布洛赫的挚友费弗尔所言,本书没有完成的部分本来应该是最有创见的部分。事实也确实是如此。让我们设想一个没有后半部分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假设韦伯演讲一半突然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这篇演讲的后半部分正好也被大风刮走了)。在前面反复强调了学术本身的局限性之后,在即将迎来的关于天职与责任的黎明的那一刻(上述关于历史学家该如何获得拯救的故事恰恰是韦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演讲却结束了。那该是多么压抑的一篇演讲啊!而这本书恰恰是这个样子。本书未完成的三章:历史的因果,历史的解释,历史的预见——全都是在前面让人们了解到历史学的艰辛之后重新让人们能够重新感到力量感的内容。难怪虽然布洛赫本人的乐观情绪虽然贯穿全书,译者却在前面和后记中表达了些许悲怆之情。
让我们来谨记着布洛赫的教诲,以一个纯粹文字游戏的态度来畅想一下另一个历史的可能性。布洛赫如果真的迎来了法国解放的那一天,如果真的迎来了法国政府对他抵抗活动的表彰,他的内心活动可能会最接近于接近于电影天国天朝的那个结尾:
狮心王:“我们来到这里找耶路撒冷的保卫者贝里昂。”
贝里昂:“我是个铁匠。”
狮心王:“我是英格兰国王。”
贝里昂·:“而我是个铁匠。”





而对于历史女神克里奥,这将会是他的最终告白:“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