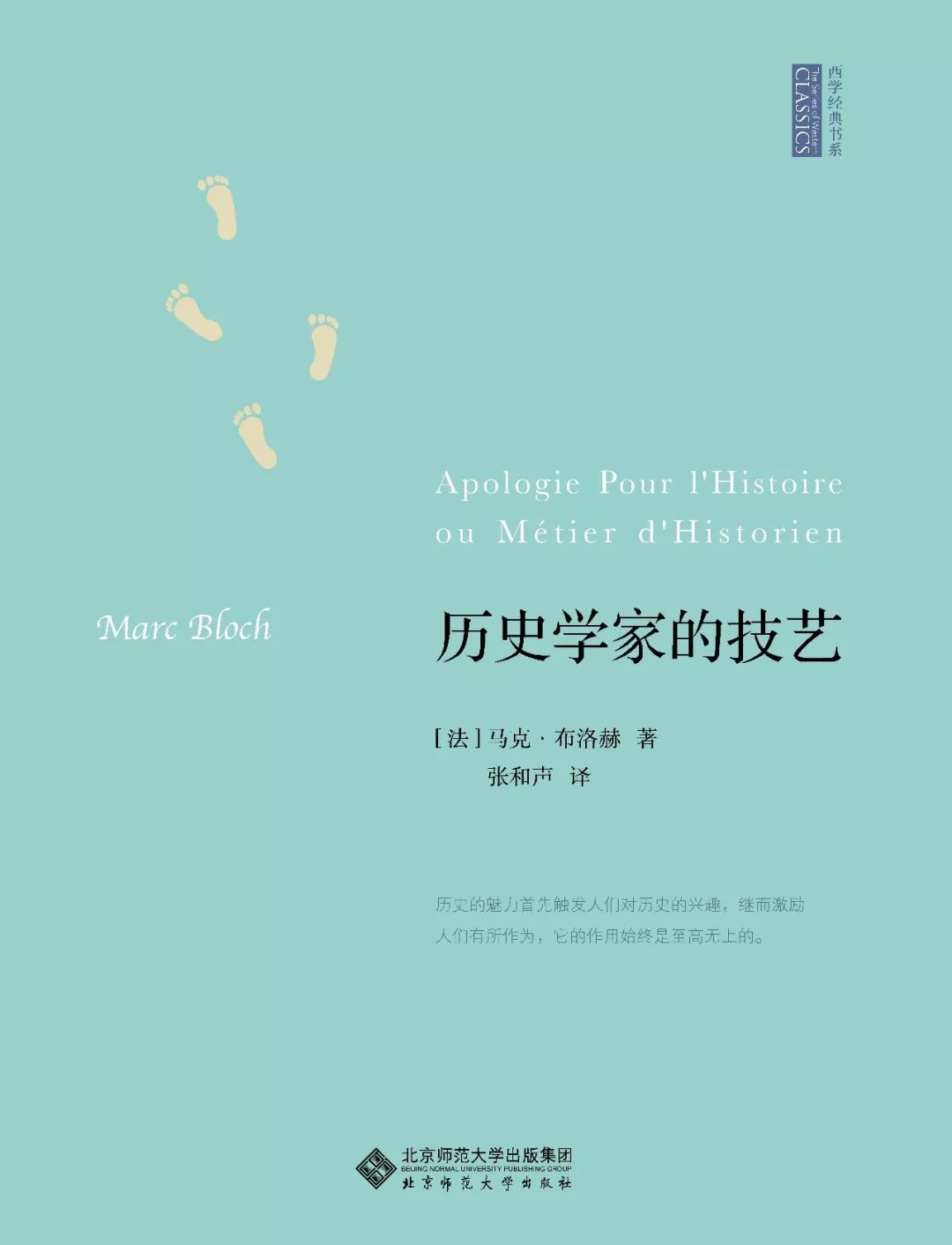
马克·布洛赫 著 张和声 译: 《历史学家的技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
武士弄墨,尚可附庸风雅,学者扛枪,只能归咎于命运的残酷。1944年6月16日,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因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在里昂市郊被枪杀,噩耗传出,西方史学界为之震惊。
布洛赫并非著作等身的史学家,而屈指可数的几部专著,如《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等,都堪称别开生面的扛鼎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便沦入敌手,在这极其困苦的时刻,布洛赫开始了《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写作。在该书的卷首,他痛苦地写道:“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这是一部愤世之作,同时也是他一生史学思想的总结,可惜,书未杀青,作者却赍志而殁了。战后,布洛赫的好友费弗尔将残存的遗稿整理成书,这部遗作方流传于世。该书译成汉语仅十万余言,其中颇多精义,为后代年鉴学派发扬光大的总体史思想、长时段理论等均可在此找到源头,为此,有人将它称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我所呈献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话虽出于自谦,可也使人感到亲切,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只是些娓娓道来的治史心得。
为历史学辩护
一门学科的存在需要辩护足见其地位之不妙。“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曾遭到其幼子的质问,法国沦陷后,他的一位同事也发出类似的感慨。的确,当昔日的价值观已被无情地抛弃,当人们一再无视历史的教训之时,历史又有什么用呢?作为一个以治史为天职的学者,布洛赫力图在书中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认为,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它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史学以人类活动作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至少,历史具有娱乐的价值,大而言之,整个西方文明又都与它息息相关。一般来说,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历史自身的魅力引起人们的兴趣,继而激发人们进行深入的探讨,而系统严谨的研究展开之后,其魅力也并不会因此大为逊色,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研究进行到何种深度,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但是,这一魅力并不能成为历史学存在的唯一理由。因为,卖弄学问并不是知识分子所应追求的东西,绝不能像打桥牌那样来“玩”历史。尽管这个可悲的世界可以为科技的进步而自豪,却没有为人类自身创造多少幸福,“当今之世已不容纯粹的娱乐,哪怕它是有益心智的娱乐”。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其形象就会显得不那么完美。而且,这一点更使史学家受到特殊的压力,因为,史学的主题正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现实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他们就会感到愤慨,就会斥历史为“无用”。但是,“历史的‘用途’(指严格的实用意义上的‘用途’一词),不应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的理智合法性混为一谈。”确实,历史学无法提供解救燃眉之急的锦囊妙计,也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然而,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用”之物往往有大用,但在急功近利者的眼中也无非是屠龙之术而已。可见,历史学受到冷遇也是不难理解的了。
布洛赫指出,即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实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于科学之列,但就目前而言,“这位知识领地的新到者尚处于摇篮之中”。虽然,史学已存在千年之久,但长期以来以政治、军事重大事件为内容的叙述史始终是史学的主流。进入19世纪之后,实证主义思潮独步一时,历史学也迷恋于孔德有关自然科学的观念,人们似乎认为,若不能最终提出如同几何学一般精确的公式,就算不上真正的科学。为此,布洛赫提醒人们,要防止近代以来习以为常的学问和经验主义的滥用,即使一门学科不具备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也无损其科学的尊严,一成不变的思想模式原是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没有必要再把它强加给每一门学科,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历史学还十分年轻,“在一系列最为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史学尚未超出初步的尝试性摸索阶段”,尽管如此,历史学没有必要舍弃自身的特色,更不必因其特色而自惭形秽,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它将展示不断更新的历史研究的前景,只要不懈地努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史学的不完善性与完美无瑕的成功都同样是富有魅力的。对真正的史学家来说,耕耘时的喜悦未必亚于收获时的欢欣。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
要了解现实就必须超越现实,要探讨历史亦不可囿于历史。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往往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漠然无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布洛赫一再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书中记载了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的一桩逸事。在斯德哥尔摩游览时,皮雷纳主张先参观新落成的市政大厅,面对同行惊愕的目光,他解释道:“如果我是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只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我热爱生活。”对此,布洛赫大为赞赏,他认为,正是这种要求理解生活的欲望反映出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出色的历史学家无不具备这种素质,尽管有时他们在表面上显得有些冷漠。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并不因其对现实的懵然无知而有所减色;而一位史学家,若对周围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漠不关心,那么,“应该称之为古董迷,他还是明智一点,不要自称历史学家为好吧”。此一语正中要害。校园中的学子常戏称历史系的师生为“出土文物”,史学的圈内人也怡然以“老夫子”自居,殊不知这正是对历史学的误解。有人说,书斋就是历史学的实验室,而治史的灵感有时偏偏来自现实的启示。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当今的知识、现实的生活往往以一定的方式更直接地帮助人们了解历史。作者感慨地说,尽管在史著中他多次描绘过战争的场面,但直到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谈得上真正理解“战争”的含义。汤因比自幼便熟读古希腊的历史著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身处于那种曾激发修昔底德秉笔著史的转折点,他才对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了全新的领悟,深感古人先得我心,从而萌发撰写《历史研究》的志向。陈寅恪先生也有类似的描述:“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及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从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陈述辽史补注序》)
由今可以知古,布洛赫因此提出“倒溯”的历史研究法。他指出,人们以为学者考察历史的顺序与事件发生的先后是完全一致的,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虽然学者事后会按历史发展的实际方向来叙述史实,但在着手研究时,则往往是由近及远倒溯而上的。因为,任何研究工作,其自然步骤通常都是从已知推向未知的。“为了阐明历史,史学家往往得将研究课题与现实挂钩……只有通过现在才能窥见广阔的远景,舍此别无他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永远静止不变的景象强加给每个阶段,史学家所要掌握的正是它在每个阶段中的变化。但是,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必须从已知的景象入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读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马克思那句至理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无怪乎,早在20世纪40年代,布洛赫就说过要把马克思的塑像奉入革新派史学的先贤堂。
由今知古的目的还是为了由古知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类的教诲早已被人说滥了,值得注意的倒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它认为历史距今愈近愈有教育意义,愈远则价值愈低。布洛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等于把人类演进过程视为一系列突发事件的组合,忽视了许多牵制社会发展的惰性力量,事实上,那些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所造成的强烈震荡完全可能是由古及今的。社会思潮的波动、技术的更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左右人类命运的潜在因素,它对历史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次政变或战争,历史上最深层的东西往往是最确凿无疑的。“为了正确把握当今世界,我们必须了解清教运动和天主教改革,又想了解那些距今不远却转瞬即逝的思潮和情感,几百年过去了,然而,谁敢断言对现实来说前者的重要性远远低于后者呢?”同样,对当今国人来说,孔子的影响未必亚于雷锋,我们从古代史籍中所获得的启示也绝不少于近现代的某些论著。时间的远近不能成为衡量历史价值的标准,正如不能因为月亮较近就断言它对地球的影响比太阳还大一样。对历史做实用主义的裁断,实质上是对历史学变相的轻视。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古今参照,相得益彰,过去与现在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历史研究可以分成各种专业,但切忌画地为牢。布洛赫认为,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总体史的思想也是针对实证主义史学见木不见林的倾向而发的。以阅读为例,只有通过上下文才能确切地理解某个词的含义,只有抓住全文的主旨才能掌握某章某节的论点,同样,对全局的把握有助于对局部研究的深入,反之亦然。布洛赫提出的总体史思想,经第二代年鉴学派史学家的发扬光大,大大拓宽了史学的领域。然而,“求尽则尽无止境,责实则实无定指”(钱钟书《史传通说序》),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却对宗师的思想提出了质疑,“总体史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一种愿望,标志着一个方向”,只是“一种不明智的雄心”。可是,若无当年布洛赫的大胆设想,就很难想象会有年鉴派史学的累累硕果。总体史(Universal History)也未尝不可译成通古今之变的“通史”。事实上,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正是当今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有意”的史料与“无意”的史料
布洛赫反对实证主义史学,但并不轻视史料考证工作,他本人就是一位擅长运用史料的中世纪史专家。他把史料分成“有意”和“无意”两大类,前者指成文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作者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后者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及各种文物等,这都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前者虽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后者更为可靠。若仅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当代史学家就会成为前人思想的奴隶,成为旧时代偏见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得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的结论,因为当时的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现代人就可能忽略中世纪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所占的位置远远不及贵族战争。总之,注重无意的史料可以帮助后人考辨历史的真伪,填补历史的空白。当然,并不等于说这类史料是完全可靠的,但至少其制造者在主观上并未想到欺骗世人或影响后代史学家的看法。
一个时代也如同一个人,并不愿把自己及祖先的隐私全部抖搂出来,它有意将精心粉饰的形象公之于世,史官便是它的代言人。这就为后人了解历史真相设下层层雾障,留下了种种千古之谜。随着史学的进步,史学家已日益注重“无意”的史料,自觉地抵制“有意”史料的束缚。
布洛赫相当重视史料的辨伪正误,本书就专辟一章探讨史料的考证,其中既有对考据学历史的纵览,也有对考据方法具体而微的论述。布洛赫认为,长期以来,史著的编纂者与考据学家似乎各行其道,前者蔑视后者的烦琐,后者又嘲笑前者的空疏。他进而指出,一方面,将史料整理与史书编纂完全割裂开来会给史学带来双重的危害,轻视史料考证与“求实”这一史学基本准则相悖,使历史学难以推陈出新;另一方面,把手段当做目的,为考证而考证则无非是虚掷光阴的博学游戏。仅仅考出史料的虚假只不过完成了一半的任务,还必须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人们作伪的动机,其背后必有难言之隐值得进行研究,这样,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况且,即便是伪造的史料也不是一无所取的。如中世纪作家曾撰写了大量的“使徒行传”,其中不乏子虚乌有之事,但是,若把这些材料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资料来利用的话,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这又使人想起陈寅恪先生的一段精彩论述:“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所谓史识,正在于能独具慧眼,发现前人所不愿透露的东西,化腐朽为神奇。诚如布洛赫所言,“尽管历史学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些,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同时,他不无愤慨地指出,当今之世,弄虚作假、造谣惑众之事盛行不衰,公众对宣传媒介的不信任,竟使口耳相传这一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得以奇迹般地复活,如今,“在学校的课程中居然没有考据学的一席之地,实在令人感到可耻。”这真是书生之见,区区考据学又岂能阻止世人的弄虚作假呢!
历史学家的技艺译者的话年鉴派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后者则推崇“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布洛赫指出,任何人研究历史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对一个新手的劝告最糟莫过于劝他耐心地在文献中寻找灵感,因为消极的考察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一份文献如同一个见证人,正像大多数见证人那样,只有在面对提问之时,他们才会予以说明。”如“电气化”对人类历史的意义远远大于某些政治事件,但史学界对此视若无睹,其原因并非缺乏这方面的资料,而是因为历史学家根本就没去碰这些资料,该责怪的只是史学家自己。另一位年鉴学派大师费弗尔说得更为明确:“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如今,以“问题史学”为指导思想的史著已蔚为大观,这不能不使人叹服布洛赫等年鉴派先驱的远见卓识。
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曾高举“如实直书”的大旗,为历史学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年鉴学派是作为兰克学派的对立面出现在西方史坛上的,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反对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但并不全盘否定史料的考证,矛头指向那种把史料等同于史学的唯历史的历史观。布洛赫等人的史学实践表明,他们对史料的重视和运用史料的能力绝不亚于前一代史学家。可见,他们对兰克学派的批判是一种“扬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才标志着西方史学的进步,反之,若是导致轻视史料、大发空论的批判,就难免使人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
评判还是理解?
“入史局须手硬”,故常把史家喻为法官。不畏权势的法官自古少见,刚正不阿的史官亦屈指可数,但其威风又何其相似,魏征就曾以掌有“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的史笔而自傲。这种心态并非东方人所独有,布洛赫就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死人任情褒贬。人总是希望像上帝那样判定此为善、彼为恶,史家在裁断死人的是非时更是下笔无情。他提醒人们注意,褒贬前人要比理解他们容易得多,对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探索,要比简单的定性论断难度更大,“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定是非善恶吗?”空洞的评判,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给史学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败坏了史学的声誉。将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绝对化,并据此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只能得出荒唐的结论。
“‘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而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历史学家真该放下假天使的架子,少一点评判,多一分理解,对古人表一种同情。
在喧嚣嘈杂的名利场中,在你死我活的人生舞台上,史学家要求“理解”的呼声是多么微弱啊!当法西斯的铁蹄步步逼近之时,布洛赫预感到已无法用笔来为历史学辩护了,终于,他拿起了枪,结果,他死于枪弹。本来他有机会亡命英美,或许他可以袖手旁观,独善其身,那样的话,可能会写出更多的传世之作,对此,人们惋惜不已。有人曾强调“学者以学术为生命”,这固然是学者神圣的选择,也未尝不可作为苟且偷生的遁词。《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那位老于世故的教师曾言:“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不错,但更多的成熟男子只是为了活着而卑贱地活着。生亦吾所欲,义亦吾所欲,布洛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评判”还是“理解”呢?
“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的回答基本上是乐观的,但诚如他在导言中所言:“当一个年迈的工匠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从事这个行当是否值得之时,他心中难道不会产生一丝困惑吗?”布洛赫心中的困惑,也未尝不是古往今来许多史学大师心中的困惑。“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历尽风霜才谈得上看破红尘,饱读诗书才有资格说读书无用,也只有以史学为天职的学者发自内心的疑问——历史有什么用?——才是最为深沉的。
张和声1991年12月于上海师大11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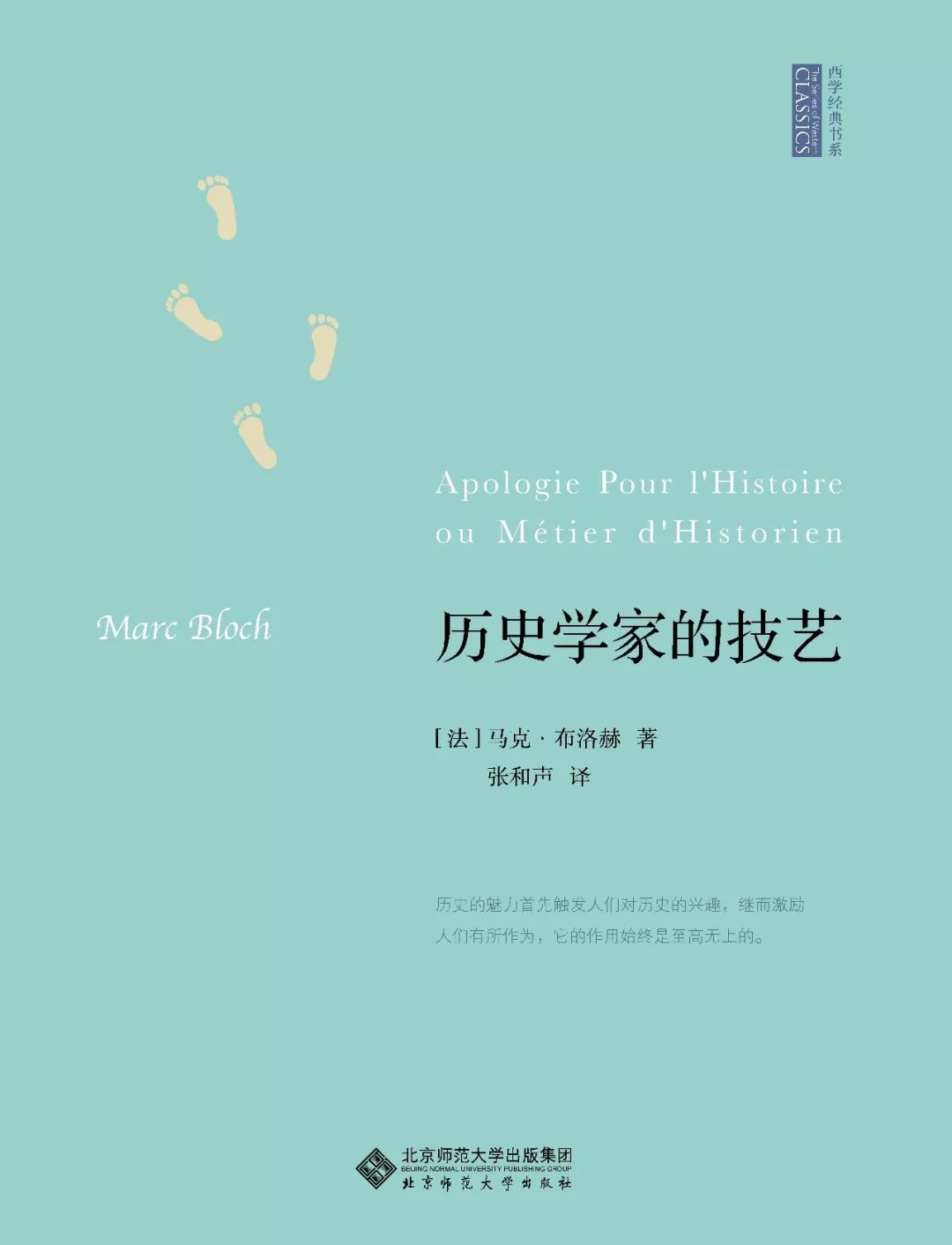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