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晚,在北京举行的“口述历史在中国”沙龙上,崔永元与马勇、丁俊杰、张钧等嘉宾结合近期出版《述林》MOOK,分享了口述历史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从2002年开始投身口述历史项目,14年来他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如何保证被采访者说的是真实的?崔永元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口述历史是资料采集,并非是去辨别真假,“如果想探求历史的真相,有一点我可以分享,千万不要想办法去找一个结论,那一定是不可靠的。”
“口述历史”是无用之用
崔永元第一次与“口述历史”结缘,源自1999年他去日本NSK访问的时候。崔永元回忆道,他当时看到一群人在编辑一个电视片子,“我印象不太深了,反正跟中国历史是有关系的。”当时如果在国内做类似的片子,肯定会考虑投入多少钱、怎么审、什么时候播出之类的。但是这几位日本同行做这些事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想留做资料,将来有一天用的时候资料很丰富。”
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对口述历史仍然不熟悉,也常常会问一个问题,这东西有什么用?对这个问题,崔永元有点无奈,“无用,无用之用。现在口述历史已经是热词了,但是从专业角度来看,大部分做的,不是口述历史,你找一个人,做成一个电视节目,采访30分钟,用28分钟,那个不是口述历史。其实口述历史,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资料采集,这个就是2002年到现在,我和我的伙伴们干的事儿,资料采集是非常复杂,又非常专业的一个工作。第二部分是,采集的资料要整理、录入和校对,要把它做成资料库,让研究者去使用。第三部分,就是使用,现在我们还一直没有做使用这件事情。”
显然,这些资料并非没用。前几天,崔永元碰到了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这位副校长就找他借资料用,“我说 可以,但是我想知道你用它干吗? 他说是想看语音语韵的变化,那些老人既说过去的语言,又说现在的语言,你能很清楚看到他的变化。我觉得将来,我们口述史的资料做得多了,很多研究会会找我们,比如说一些新的词汇的介入,现在大家都会说,你out了。什么时候出现的 out了 。我们不能确定哪年哪月哪日,但是确定一个历史阶段应该差不多。其实口述历史的资料,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整个社会的推动是有很大益处。”
不必苛求讲述人都讲真话
口述历史一个很直接的用途,体现在历史学研究上。历史学家马勇认为,历史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是一个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结果,而近代中国留存下来很多史料,但有很多需要去纠正和纠偏的。而口述的历史,或者是类似于口述的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大家都做口述史,都从不同侧面提供一些记录的话,才能使历史讲得更逼近真相,脉络才能出来,如果少了这些多元性,可能就很孤立相信某一种说法,就使我们形成一些偏见。希望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给历史学研究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谈到历史研究,崔永元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14年来经常有人问他,如何保证被采访者说的是真实的?他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口述历史是资料采集,并非是去辨别真假,“如果想探求历史的真相,有一点我可以分享,千万不要想办法去找一个结论,那一定是不可靠的。”而探究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多方面对照,如果资料丰富了,可以360度地去对照。他说:“我记得唐德刚先生说,历史研究就像登山,爬得越高,越云山雾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掌握的资料越多,你越没有办法确定哪个是历史真相。”
在14年时间里,崔永元的团队采访了4000多名受访者,完成5000人次的采访。崔永元笑称,在这个团队他主要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是“骗钱”,这十多年拉来了3个多亿。“第二件事就是跟受访人打交道,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坐在你面前,向你吐露心声的,这非常难。有的人要几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需要你持续不断地给他做工作,直到他想通,采访才能完成。我记得张钧做梅娘的工作,大概用了两年时间才采访到梅娘,和张爱玲齐名的一个文学家,大家都不太知道她。”
崔永元说,做口述历史其实是非常枯燥的,但要是真心投入进去了,也会发现是件好玩的事儿,“现在就有一个采访对象,我保持着差不多每个月都跟他吃饭这样的精力,现在已经三年了,还没有说动他。之前还有一个采访对象,我跟他吃了三年饭,直到他去世了也没有采访到。但是他临去世之前说了一个好话, 小崔是个好人,我建议你们去拥抱他一下 ,我觉得心里也算有一点安慰,但是其实没采访到他,还是非常非常失落的。”
第一期《述林》对准年轻人
当天,崔永元团队带来的《述林》是国内第一本口述历史类MOOK,近期出版的《述林1: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收录了二十一位中国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及其家属对抗日战争的点滴回忆。这些世纪老人回忆年轻时代遭遇这场战争时迁徙漂泊、辗转求学、敌后杀敌、远征缅甸、文艺抗敌,用故事和细节勾画出一部普通民众的抗日战争史。书中所收录的这些讲述、手记,用故事和细节,为我们提供了触摸那场战争的另一种路径。
《述林》的主编张钧透露,这套书的选题策划过程跟别的书不同,是反着来的。“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们想把抗战这个事拿出来再说说,又不想只是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这些事。于是,我们就想聊聊当时抗战时期不同人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到我们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资料库里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材料,在巨大的素材库里面,我们抓取出来这样一些东西,就形成了这样一本书。”
为何选定了“年轻人”这样一个主题,张钧说:“年轻人这个概念,其实和我最初的设想也不完全一样。我最初想的,是反映一下当时抗战时期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内容做出来之后,和年轻的编辑团队一起开会时发现,参与这本书编辑的大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而这本书里面讲述的主角在30年代、40年代也就这么大,所以年轻人这三个字是这本书的一个关键词。”
书摘两则
第二天晚上,日本人给我们发了请柬,是在国际饭店的十四楼。我记得去的有王引、刘琼、舒适,我印象深的就这几个。去了以后,日本人还闹了个笑话。先是日本人讲话,然后一个汉奸代表发言,他讲扬州话。说什么大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啊,我们要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啊,我们要怎么样子维持社会啊,讲了这么一通。先前说打倒英美帝国主义,讲得很清楚,讲着讲着来了一句,“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吓得脸都黄了,马上收回来。谁都不习惯不是?之前都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改成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别扭。
摘自《孤岛及沦陷时期的上海影剧界》吕玉堃口述
有一次我追着一艘军舰,那军舰在长江上从东往西走,我就俯冲下去,对着他打,我们打的时候都是曳光弹,打出去你也看得到底下冒火,他也对着我打。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想撞上去算了,同归于尽。快到了,哎呀,撞上去明天不就没有人来打了,还损失一架飞机。那不行,临到头上就再拉起来,回到机场——落地,看到飞机屁股底下二十几个弹孔。现在想起来真是玩命,可以说置生死于度外了,哪怕同归于尽都可以。
摘自《南侨雄鹰长空逐日》彭嘉衡口述
京华时报记者田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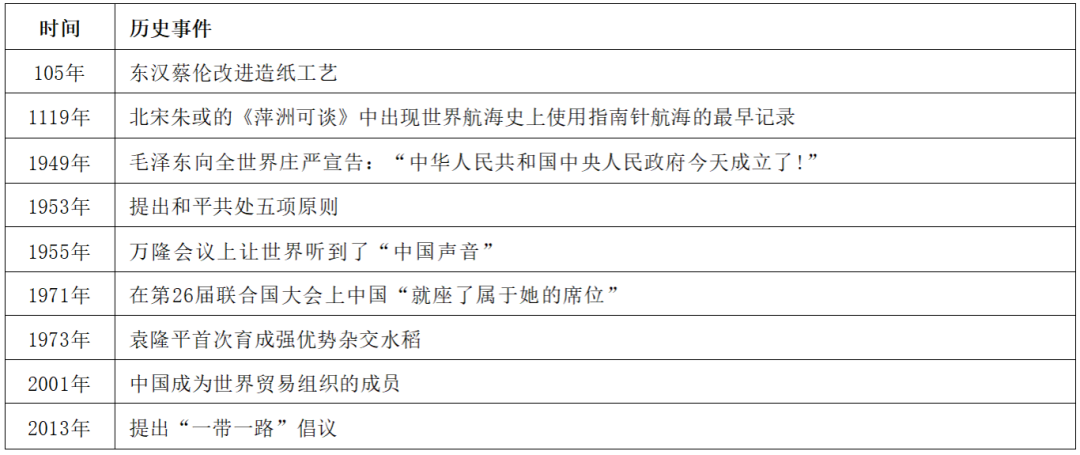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