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处理三农问题的时候,要考虑什幺是可为的,什幺是不可为的。提高农民收入当然应该是国家政策的目标之一,但是,拔苗助长似地提高农民收入,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比如,1998-2000年实行的粮食购销政策 —“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人为地抬高国家收购价格,结果是导致大量的粮食积压,国家因此而承受的损失估计在3000亿元。如此巨大的损失最终还是要老百姓负担。
这里涉及到国家的角色问题。因此,在讲三农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下国家问题。我想做的,是区分积极的国家和消极的国家。消极的国家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最小国家,这是像哈耶克和诺齐克那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认同的理想国家。在最小国家里,国家的唯一责任是制定和实施法律,在法律之下,人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不多也不少。比如,比尔.盖茨并不比非洲的饥民享有更多的自由,失业和破产的人应该自己负责,国家没有责任。这种最小国家是不是可能的呢?
如果人是单面的、完全理性的,那幺最小国家是可能的。这里,我解释一下理性人,理性人就是做了一件事不会后悔,用经济学的词语来说,就是要符合序贯理性。理性人不会出现反社会的行为。如果是这样,最小国家是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自觉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国家不用为他们担心。但是,如果人是多面的,那他就会考虑多个方面,除了收入,他还要考虑地位、自我价值等等。事实上,每个文化都包含对公平的追求。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每种道德理论体系中都包括平等的内容,只是各自强调的方面不同。大多数人容易只强调一面,比如权利,而忽略其它方面。我们应该更全面地看待平等。中国的传统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不是人们常说的“红眼病”,而是一种对公平的基本认识。西方基督教里也有基本的平等的思想。此时,最小国家就不成立了。
历史也告诉我们,最小国家也是不存在的。卡尔.波兰尼在《伟大的转变》里指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不是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垄断资本家有意设计的,因为自由竞争符合他们的利益。同时,自由竞争被限制在他们自己内部,对于外部竞争,他们极力反对。比如英国的自由贸易,它只是对自己、对本国自由;对其它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相反,对工人的保护却是社会为了保护自己而自发形成的。经济学家认为,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对缓解美国的经济大危机没有起到什幺作用,但是,罗斯福却建立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制度在过去的七十多年里不断完善,对美国平稳地度过后来的经济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历史上不存在最小国家。
另一种消极的国家是被挟持的国家。被挟持的国家就是指被利益集团所左右的国家。比如,东欧的激进改革为什幺失败呢?哈佛大学教授施莱佛做了很多研究,他认为东欧改革失败的原因是政治势力将经济改革搞坏了。一个国家,不管是转型期的国家还是民主程度发达如美国的国家,如果成为了利益集团的工具,那幺经济势必要受到破坏。比如印度,它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民主国家,是一个受利益集团左右的国家。我有一个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朋友,有一次应邀到印度访问,介绍中国改革的经验。印度同行要少讲经济改革的经验,而讲一讲中国反腐败的经验(笑)。中国可以处决一个副委员长的官员,印度实际上该处决的人很多,但是无法做到。印度的政党分左派和右派。右派执政时想对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左派就带领工人游行,使得右派的改革无法进行。但是当左派上台后,它也想私有化,因为国有企业的亏空太大了。此时,右派也去发动工人游行,阻止改革。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不管谁在台上,改革都无法进行。国家被政党政治所左右,就不能达到社会目标。
第三种消极的国家是商业化的国家。中国就有这样的倾向。它的特点是政府与企业的行为方式相同,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来讲一下中国的财政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单一的共和国,地方服从中央,地方性法令、法规也必须处在中央的法令、法规之下。由于执政党独一无二的地位,中央在政治上对地方严格控制。但是在财政上,自从1958年放权之后就一直没有收上来,财政制度显示出强烈的联邦化倾向。而且,这种联邦化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邦化。像美国的联邦制,它在一个州之内的财政还是统一的。但是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每个县、每个区的财政都是独立的,最典型的,比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这些都统一不起来。对待企业也是这样,每级政府都不想要亏损的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将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拿在手里,其它的下放到各省;到了省一级也是如此,将一向效益好的企业拿在手里,其它经营状况不太好的企业就下放;各个城市也仿而效之。有一次,我们进行改制调查时发现,统计年鉴登记着的企业数远大于各市拥有的企业数。原来都在一年期间下放给区县了。到了区县一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放工人回家,工人失业,没有饭吃,这样就容易激化矛盾。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不配套。政治体制是高度集中的,而财政上相互独立,这就会使政府产生商业性行为。地方政府都变得非常理性。有一次,一个城市经贸委的领导对我说:“我们比学者都开放,有一次把一位教授都驳倒了。这个教授认为像水电煤气这样的公用事业是不能让私人经营的。我说,怎幺不可以?香港不是把公交线路都拍卖了吗?”
在企业改制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是重庆。它是这样做的。企业改制时,先把工人划出来;然后清算资产,挑选一些职工留在企业,剩下的由政府来负担,从此,企业和政府就一刀两断了,各自的权责明确。重庆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做法,对社会有利。遗憾的是,很少有地方能做到这样。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做的:你要想买我的企业,行!但必须全部接受我们企业的工人。这样一来,政府的危机就解除了,工人开不了支就会直接找经理,而不到政府来“上班”了,(工人上访、静坐叫“上班”)。企业是私人的了,有问题要找法院去解决。这是一个转移矛盾的做法。但是购买企业的人也不能平白无故增加这幺多负担,他们就会跟政府谈判,要求资产打折,就是要以比企业的实际价格低得多的价格来买企业。各地都有资产打折的公式,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按照这个公式来做。这就要看企业经理跟市领导的关系了。根据了解,有的地方卖出土地的价格只有工业用地价格的五分之一!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造成人员和资产一锅粥的局面。企业到了新的经营者手中时,如果想进行新的资产组合就可能出现问题。有一家澳洲的公司买了一家天津的企业,当时低价买进,接受了全部工人。一段时间后,公司发现这个行业没前途,便把企业转手卖给另一个企业。它不管人,只卖资产;新的公司接手企业,自然要大裁员。工人要求公司承诺就业,但新公司说:“我买的是企业的资产,又不是连工人一块买的!”澳洲公司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合同上没有规定卖企业的时候要怎幺处理、安排工人。新的企业更没问题,买的是企业的资产而不是工人。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政府不承担责任,而是全部推给了企业。政府的行为是理性的。老板不给工人钱,工人自然会去找老板,而不是找政府;解决不了的话,就把老板告上法院,而跟政府无关。这在理性上是很清楚的。政府变成了商业性单位。但是对政府有利的行为不一定对社会有利。政府的商业性行为造成国家性机会主义,长期下去,政府的合法性就成为问题。其它财政联邦化的国家有配套的体制,如地方选举,使得政府要对民众负责,而中国缺少了这一环,这就使政府的“理性”行为越发偏离社会利益。
那幺什幺是积极的国家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明确的目标,对什幺是好的、公正的社会做出明确的判断。比如美国,我们可以说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干涉别国的内政,但是,民主、自由的确是美国人价值观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就像我们所说的霸权主义在美国国内也是得到支持的。仔细想一想,美国的有些做法还是有它的道理的。这幺说下去话题就扯远了,跑到国际关系上了。总之,一个政府,一个社会,要有关于公正的标准。老百姓不管你说你代表谁,而是要问:你代表了我什幺?你给了我什幺?社会的分化日益明显,没有谁可以代表所有各阶层的人,关键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从理论上讲,一个公平的社会,就是一个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社会,公平就是全体公民所认同的最小范围的伦理规范。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社会公平的标准,就会被变成消极的国家,不是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就是一味追求政府自身的利益。中国虽然没有明确的利益集团,但潜在的利益集团仍然发挥着作用。对于一个以代表全体人民为宗旨的政府而言,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都要照顾到,政府因此变成了一个“救火队”,哪个集团喊得凶,就赶紧跑去安抚,国家因此变得被动而消极。
有了“公平”这个目标之后,积极的国家还要担当起社会的责任,而不是逃避责任。比如九年义务教育,只要求公民的义务,没有权利。我们大家来想一想,如果一个穷人连过日子都很艰难,我们怎幺能要求他尽子女教育的义务?就好比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你能期望他对社会负责任吗?我的父亲半身瘫痪,他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负责,你能要求他对社会负责吗?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但道理是一样,对于一个人挣扎在生存边缘上的人,我们无法要求他对社会负责。国家必须在九年义务教育中担当起责任。但实际上教育经费基本上都是各县自己解决的。我想到了1993年实行的新税制,当然设想是好的,当初设计了收入转移机制,不发达地区能从中得到好处。但实际上,不发达地区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受损了,因为基本上没有收入转移。中央拨给地方的资金跟着项目走,而要想接下项目,地方必须要有一定的资金配套,这个不发达地区是很难办到的。有一次我们到湘西访问,湖南省财政厅的一位副处长在会上声泪俱下:湘西历史上就是吃皇粮的地方,国家一直给补贴;到了现在,反而不进反出。湘西以烟酒业为支柱产业,国家对烟酒业征收特种消费税,此税是中央独享税,湘西因此出大于进。所以,1993年的财政改革让湘西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一谈到国家应该负责任,很多人会问:你是不是要强调国家干预?你是不是要全能的国家?当然不是。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的,国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的国家不是一个利维坦的全能国家,它承认自己能力的限度。借用森的话来说,这种态度表现的是assertive incompleteness,即用积极的态度来承认不完备性。那幺,为与不为的界限是什幺呢?国家作为的界限是为公民的能动性提供基本能力的保障,为公民提供一个起飞的平台。低于这个界限,就是消极的国家;超出这个界限,国家的作为往往不能成功,比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粮食政策。
具体讲到三农问题,我着重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村庄民主,一个是农村基本社会保障。
很多人认为村庄民主意味着国家的退出,因此有“村民自治”的叫法。但是,这个词不好,这样一级级推上去,就是乡自治、县自治、省自治了,那幺大家都自治?实际上,村庄民主是国家架构的一部分,是积极的国家的体现。但有人对村庄民主提出批评,认为民主是外来的,成本又太高;因为人口多,而且整体文化素质很低,选举的方法是得不偿失的。有人认为古代的乡绅自治的方法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管理成本低。他们没有看到,古代能够建立这种权威,是因为那时候具有权威建立的基础。一个是家族,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那样;另一个是知识优势,像白嘉轩的姐夫那样。但现在中国的农村不再具备这样的权威基础。家族势力已经很小了,有的地方即使保留祠堂,也成为老年人活动中心什幺的,而不再是权威的象征。从文化层次来看,在比较发达的地方,也大都是初中毕业的水平。1950年代的时候,刘绍棠可以靠写书在北京买得起一座四合院,但现在就绝对办不到了。为什幺呢?不是因为刘绍棠的书贬值了,而是因为别人拥有的知识多了,少数知识分子的相对价格就要下降,就是这个道理。在农村中也一样,知识已经不能成为权威的来源。乡绅治理因此没有了社会基础。
村庄民主是建立新型的村庄文化的一个突破口。通过村庄民主来治理的成本并不高,投票率低也不是个问题。投票率低不能说明不民主,不能用投票率的高低来衡量民主的程度。有的人不投票是认为谁当选都行:天下太平,谁当选都一样,这难道不是制度的胜利吗?村庄民主不应该向后退,而应该向前推进;不是做得过火了,而是做得还不够。现在是村庄民主可以叫做“孤岛民主”,因为只能在一村的农民之间实行,到了村外就不行了;而且,按照法律,村委会还要受党支部的支配。然而,现实正在冲破这种格局。广东省有一个村长,是选举出来的,得到村里的新兴商业阶层的支持,因此很有信心,敢向支部书记挑战,如不列席党支部的会议等。选举一年后,支部书记坦言,下届书记他不会做了,他要推荐全体村委会成员当党支部成员。
再谈农村基本社会保障问题。改革前一直实行的是合作医疗制度,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也解决了基本的医疗保障。合作医疗制度靠公社财政的补贴,当公社垮台的时候,它也就随之垮了。现在农村有7亿人口,有医疗保障的还不到1%。我们再看看其它的数字。农村识字率在公社时代提高很快,但近二十年慢了下来;全国的婴儿死亡率是32‰,发达国家是15‰左右。这个数字在发展中国家里还是不错的,但改革后的进步速度慢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想一想农村有什幺保障。经过多次改革,城市保障体系渐趋完善,建立了从养老、医疗到失业和低保等一系列社保制度;而农村却毫无保障。根据最近一次的全国健康调查,农村贫困人口中中因病治贫的比例为39%,有些典型调查发现这个比例更是达到70%。在座的农村来的同学大概体会很深,农村人生病,尤其是壮劳力生病,是一把双刃剑,不光失去了劳动能力,而且还要借钱治病;欠下的债,几年之内是不可能还清的。农村大部分人毫无保障,针对这种情况,政府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在土地上,国家给了农民自由。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朝着土地的事实私有迈进了一大步,它给了农民权利。但这还不够,国家还应该给农民使用这个权利的能力。这是国家应该有所为的。
当前,卫生部正在考虑农村医疗体制的改革。卫生部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恢复低层次的合作医疗。但我认为这不是个很好的路子。现在的农村都有私人医生,价格也都很低,就算有了合作医疗,农民也不一定爱去。一方面是出于不相信地方干部,钱在他们那里放着还不如在自己手里放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价格上也不一定能和私人医生竞争。从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来说,合作医疗所能解决的疾病对农民的意义也不大,因为它不保那些对农民影响巨大的大病。如果以农民的需要为前提,首先建立大病保险系统可能更好一些。当然,这只是推测,还需要调查,有了数据就能更准确地说明问题。至于资金问题,国家至少要在初期负起责任。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将农业税直接转化为保险基金。
总之,国家在三农问题上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的就是要为农民的自我发展提供起飞的平台,其它的则不能做。比如提高农民收入,一时能起作用,但不能持久,因为国家财政有限,不能长期这样支持农村收入的提高。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三五年能够解决的。政府要有所作为的是培养农村的造血能力,而不是只给它输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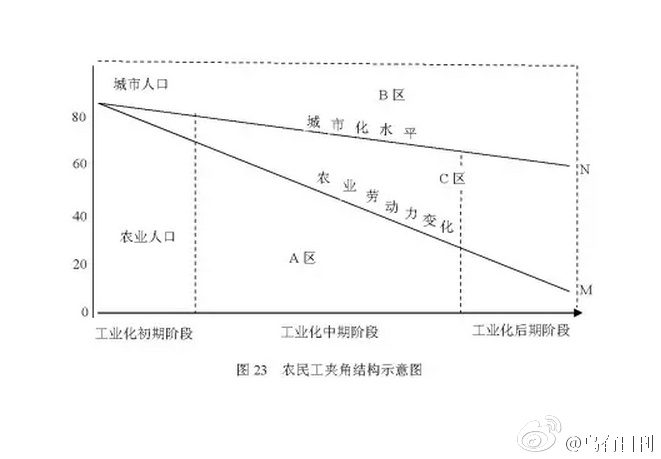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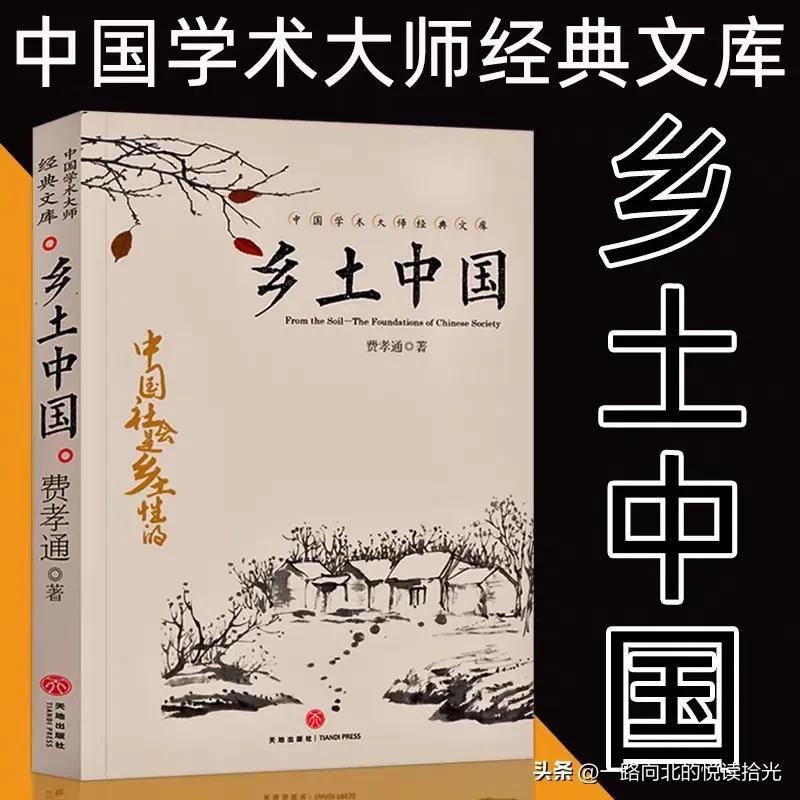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