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únez-Flores, J. I. (2022). Decolonial and Ontological Challenges in Social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本文作者 Jairo I. Fúnez-Flores
社会理论中的非殖民化和本体论转向反对现代性的整体化、一致化,关注他者的主体性。反对殖民主义并非二者首倡,但它们的贡献在于突破既有解释模式,真正彻底地在方法论上反对现代的单一性/客观主义和后现代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这是通过挑战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完成的:只有如此,才能彻底否定本质主义,进而避免像后殖民主义理论那样以被殖民民族的民族主义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民族主义,也不致走向彻底的相对主义,否定文化之间翻译的所有可能;只有如此,才能“肯定真实的、存在的、历史性的他者”(Dussel, 1988)。
本文将对这两种转向作一概述,研究二者在概念和方法上的一致和分歧之处,考察它们如何打破现代性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霸权基础。
本体论转向概述
社会理论最近朝着本体论问题的“转向”,应当理解成是关注民族志中背离且凸显了现代性的主流现实假设的局限性的偶然事件。它主张本体论层面的相对主义,即,通过民族志材料,而不是既定的分析方法,质疑占主导地位的对于现实的假设,以解决建立在二分的现实概念基础上的传统分类方法的限制。
重点之一是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分,它是分析现实和他者的基础。当代人类学围绕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提出先验的本体论假设,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类别,也不志在发现世界的本体或自然和生命的本质,而更多地“不感兴趣具体如何,而感兴趣可能如何”(Holbraad and Pedersen, 2017: 68),研究他者概念化世界的方式及其揭示的对人类和不属于人类范畴的各种关系的本体论假设。“如何看待事物这个认识论问题被转化为本体论问题,即首先有什么可以看待”(Holbraad and Pedersen, 2017: 5)。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类别不仅涉及认识论问题,即人们如何在语境中认识这些领域,还关涉到人对现实的观念,以及什么构成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
因此,人类学的本体论关怀避免将他文化及其创造实践还原为世界观、信仰或自然的文化表征(Viveiros de Castro and Goldman, 2012)。例如,受控疑义旨在翻译不可比的民族志偶然经历,发掘自然和文化的主流本体论假设的局限性,以及基于不同的现实概念的世界的存在。
本体论转向的方法论创新在于目的:通过翻译其他存在模式,而不是发现新的存在方式,来发明新的概念。的确,“‘概念’在这里应该理解为或多或少与听起来更严重的‘本体论假设’同义”(Holbraad, Pedersen, 2017; 15)。概念的本体论假设——例如,术语而非内容(Mignolo, 2021)——提供了主流的现代调查模式所依据的基础。本体论转向不是探究一群人“为什么”以及“如何”以文化上的方式组织起来、行动或赋予“自然”以意义,而是询问与现实概念有关的他者的概念、实践和基于偏离自然和文化二分法的概念而建立的关系是“什么”。例如,当原住民说人类是动物、动物也是人类时,他们的概念通过他们提到的关系创造了另一个世界。与其把这些命题看作是模棱两可的、错误的或相当模棱两可的,不如思考,这些命题使哪些世界、关系和实践成为可能?
本体论并不像从前结构主义者那样关心将原住民束缚在“符号宇宙的封闭系统”之中的文化差异(Ricoeur, 1974: 65)。在这个意义上,它挑战了地方、文化表征和身份同构的假设(Gupta and Ferguson, 1992),因为它拒绝将其他文化设想为自然的不同表现。事实上,它分裂了对自然的理解所依据的概念基础,反过来,也使文化是一种已经固定下来的、两种不同现实的世界观的概念不再是“自然”的了(Whitehead, 2007)。
非殖民化转向概述
拉丁美洲的非殖民化转向汲取、融合了其他思想和实践谱系,来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框架和历史学。它将现代/殖民地世界体系设想为一个从1492年开始在全球范围逐渐形成的殖民权力的矩阵(Tlostanova and Mignolo, 2012)。其分析超越了以殖民者为中心的视角,延伸到他者的历史和思想体系,强调他者同样构成了现代性/殖民性。此外,它强调使西欧的地缘文化身份和地缘政治霸权地位得以构建的话语、制度和社会实践(Coronil,1996;Dussel,1996;Quijano,2000),从而将统治的物质层面与象征层面相结合。
非殖民化的理论模式试图与欧洲中心的现代性、历史、知识、权力和存在的解释脱钩(Mignolo,2007)。脱钩不能被解释为反对西方知识生产的本质主义行动。脱离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论必定更优。“在社会上处于权力关系的被压迫一方,并不自动意味着他/她是从下层阶级的认识论位置出发来思考的”(Grosfoguel, 2007: 213)。事实上,现代/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地位取决于知识的地缘政治学和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后两个术语即是关于全球北方生产的知识通过金字塔式的全球大学系统在全球南方复制的方式的,自16世纪以来,该系统帮助维持了西欧以及随后美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地位(Grosfoguel,2013)。
非殖民理论将社会整体看作现代/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最主要的概念是权力的殖民性,基哈诺(Quijano, 1992, 2007)定义它为“统治矩阵”,由系统性的对劳动、性别、主体性和权力的控制构成。这些统治结构是由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提出的。虽然政治经济机构对权力的殖民性不可或缺,但正是对社会和文化机构的霸权控制,产生了复制前一种机构所需的主体性(Rama, 1996)。因此,权力的殖民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认知模式和新的知识视角,在这种模式下,非欧洲的即为过时的,并且由此出发,它即使不全是原始的,也是低劣的”(Quijano, 2000: 552)。
存在的殖民性(the coloniality of being)的概念在于种族优劣观。如果说权力的殖民性强调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剥削通过种族化的劳动分工进行,知识的殖民性关注在认识论层面对前者的正当化,那么存在的殖民性则更加关注生活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存在和种族层面(Maldonado-Torres, 2007)。它包含了重新解释杜塞尔(1994)提到的外部性(exteriority),即自然化欧洲的权力崛起、低劣化非欧洲世界的历史叙事和哲学话语的叙事。关注欧洲的外部性、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他性,才能够比较社会和人类学理论中的非殖民化和本体论转向。
知识的社会学和地缘政治学
在冷战结束和萨帕塔运动(the Zapatista movement)出现后,拉丁美洲多个学科的学者为了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殖民化倾向的“社会历史情况”(Mannheim, 1952)、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和未完成的非殖民化项目,开始质疑欧洲中心主义的范畴(Mignolo, 1995;Quijano, 1992)。人类学家反思了人类学在殖民化中的作用(Asad, 1973; Stavenhagen, 1971),这导致了表征危机和反思转向(Clifford and Marcus, 1986),也为解决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有关的生态危机建立了伦理和政治基础(Kim,2019)。然而,反思性转向并没有超越对表象的批判,也没有走向土著斗争的多样性所带来的改变本体。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理论产生“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实际后果”(Hall,2019:175),并且,各领域同政治的结合创造了进行其他思考的条件,其影响是辩证的。非殖民和本体论理论模式强调观念形成的环境,它们指出,问题远不止是向他人“开放”社会科学(Wallerstein, 1996),还有新殖民主义的背景下,无休止的统治、剥削和生态破坏导致了他者的认识(认识论)、关系(伦理学)和存在(本体论)方式的丧失。另一方面,社会理论的转向因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才得以可能,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因此,理论转向应更多地看作具有社会历史和地缘政治背景的知识潮流,而不是人文科学和某些科学界的知识活动中内生的范式转变。
现代的基础
非殖民和本体论的转向以不同的方式将其理论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前者采取历史、哲学、社会学的途径来考察现代性,并将其分析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的社会阶层结构联系起来(Dussel, 1985; 2000)。后者走的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的道路,通过现代性的各个基础范畴——拉图尔(Latour, 1993)称之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分水岭(the Great Divide)——来分析现代性构成。关注点之一是本体论层面的现实的二元分立(Whitehead, 2007),它导致了心/物、人/非人、观念/身体的划分,研究重点在于它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表现,以及上述划分如何使殖民化的身体被划分到静态的、可利用的自然界之中(Strathern, 1980)。现实的分叉凸显了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殖民和资本主义的统治模式构成了现代性剥削自然(即物质)、非人类和人类的黑暗底层这一方面(Mignolo,2011)。
基哈诺的现代性定义进一步阐释了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殖民地之间的纠葛:“[社会的]全体世界人口和过去五百年间的所有历史,在分化的或者可分化的各部分中共同建构的全球权力模式表现出的所有世界或历史上存在过的世界”(Quijano, 2000, p. 545-6)。他的定义与吉登斯(1990)不同,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17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一种社会组织模式,它是一个内源性的过程,随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而基哈诺强调的是殖民主义和殖民性的主流模式,而不是残余和新兴的形式(Williams, 1977)。他描述了四个明显的特征:
[现代/殖民世界体系]是第一个使其中每个领域的社会存在的所有历史上已知的社会关系相对应的控制形式得到阐明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存在的每个领域的每个结构都受一个权力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的制度的霸权的掌控。因此,在控制劳动及其资源和产品方面,是资本主义企业;在控制性及其资源和产品方面,是资产阶级家庭;在控制权力及其资源和产品方面,是民族国家;在控制主体间性方面,是欧洲中心主义……这些制度都与其他机构相互依赖。(2000: 544-5)
拉丁美洲社会理论的非殖民化转向反对通过理解殖民主义的复杂性来“谅解”殖民主义,认为它也给被殖民的世界带来进步,将殖民主义归为“人性”的必然结果。它完全忽视了欧洲殖民主义在建立第一个现代/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者说,表现为权力、知识和存在的三维殖民矩阵的全球统治结构中起到的作用。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现代性所产生的话语和实践的复杂性。本节剩余部分意在考察现代性,至少是其主导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表达方式的构想和执行;比较非殖民化和本体论的理论转向是如何定义现代性的,从而更好地理解它们是如何挑战现代性的基础范畴的。
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中,现代性的特点是它的欧洲“时空起源”:宗教的、认识的、政治的和技术的进步从欧洲产生,经历线性的发展过程,并在欧洲达到顶峰。在社会学上,对现代性的关注在于其独特的制度、规范性原则和功能;在文化上,理解现代性是通过研究占主导地位的自由生活世界、工具理性、民族国家、维持其普遍性和优越性的科学知识之间的联系;在哲学上,现代性概念往往被定义成人类中心的、形而上的人和他支配自然的能力的出现(Escobar, 2007)。这些观点最终遵循着发展和进步的逻辑,并且这些逻辑有着现代性基础的两个神话的支持,即单向进化论/扩散论(diffusionism)和二元论(Blaut, 1993)。这两个霸权主义的范式自然化了资本主义剥削、殖民统治、文化和种族的阶级和权力结构,从而为之辩护。
历史的单向性概念或进化论/扩散论是现代性进行阐述和重构的中轴(Quijano, 2000)。进步、发展,以及最近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都被视为产生自欧美的自然过程。因殖民化而被种族标签困住或是非人化的非欧洲民族和地区,被归类为不发达、专制、不民主和传统,甚或被定格在原始的过去,同时,根据他们看起来与自然的接近程度,被归类于社会和种族的某阶层;只有欧洲脱身其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依赖于粗略概括和“管窥历史”(a historical tunnel-vision)(Blaut, 1992: 295),这使得历史学家只能够在希腊找到欧洲的起源,忽略其他文化的影响。
单向进化论和二元论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的理论出发点即是二元论,具体而言,即自然化征服者的优越性和被征服者的劣等性。在线性的历史观和二元本体论的配置下,他者在象征和物质上都用来表现、证明、自然化西方人的优越性。主流的话语和实践都否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维持西方人的地缘政治、经济、技术和认识论的霸权地位这一事实,并且,二者还在当代扩散论的全球化观点中延续,并得到了全球(现代/普遍)和地方(传统/特殊)的二元论概念的支持。因此,如果不考虑单向进化论/扩散论和二元论,就不能清楚地理解权力的殖民性。
本体论的转向揭示了现代性是如何在它与被殖民化的他者的关系之中得到定义的,它倾向于强调提供了维持现代性的殖民计划(针对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的)的条件的现代范畴,即人类/非人类和自然/文化之间的分界。它阐明了自然概念是如何遭到工具化的。例如,自然概念在将他者定为“接近自然”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Viveiros de Castro, 2014)。现代人被呈现为无文化和无种族的科学存在,而其他人则被打上低等种族的标签,其文化的表达、不同及其生活整体都被看成是完全基于自然(Latour, 1993)。另一方面,本体论转向关注现代科学与其他领域的复杂联系。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在实践中没有固定的边界,然而,主流话语将科学劳动描绘成与其他领域脱节,来维持科学思想是纯粹的、未被殖民统治、资本主义剥削和知识生产的地缘政治所污染的观念。
正是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强调,使得本体论转向在对现代性的审视上与非殖民化转向明显不同。非殖民化转向往往只审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没有衡量科学话语和实践在工具理性和知识的殖民性批判之外的影响。权力也影响了我们对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分水岭的认知和演绎,以及社会制度对现代的存在、认识方式的再生产。
社会科学正是在上述基础之上建立的。这并不意味着学科知识的有效性或普遍性降低;相反,我们所理解的普遍知识取决于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本体论划分,这二者是支持法则论(nomothetic)和意识形态认识论的区分的主要范畴(Dilthey, 1989; Snow, 1993; Windelband, 1958)。只要这种区分被我们的知识实践所延续,我们就有可能延续本体论和非殖民化的转向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现代/殖民主义事物秩序的自然化。
权力的批判
拉图尔(1993)坚持认为,超越批判征服他者的物质和象征力量的思想脉络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只关注统治的学术研究往往只关注“黑暗”的民族志,而不去考虑抵抗,以及虽然轻微或不完全但实际可行的替代方案(Ortner, 2016)。如果研究局限在为批判而批判的范围内,思想上和政治上就不会有什么思考和做其他事情的空间。本体论的转向结合“解构的否定式过程”(Holbraad and Pedersen, 2017: 12),提出在方法论上转向民族志所带来的重构可能性。
即使是对权力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后现代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Mignolo, 2011),它也可能导致一种可悲的虚无主义宿命论,同时使它自我标榜,只有通过它,才能有效地通过解构进行符号抵抗。通过采取积极/重构的方法,以及对主流叙事、概念框架和社会实践的消极/重构立场,非殖民化和本体论的转向放大了被现代性/殖民性压制的其他存在和认知方式,这一点在政治领域有着实际的意义。
因此,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不是背弃那些长期以来在现代性的背景(或霸权的本体论假设)下被消极表述的人,而是将不可通约性看作颠覆现代性殖民化概念的必要条件。卡斯特罗和戈德曼提出,在方法论上向非康德或后康德人类学“转向”,拒绝用先验的范畴决定对他者经验和文化身份的解释(Viveiros de Castro and Goldman, 2012)。
这与非殖民理论的出发点有很大不同。本体论转向的起点是对抗现代性的主流本体论假设、基础范畴和科学话语,而非殖民理论则宣称自己主要针对权力、知识和存在的殖民性的认识论;一个从“什么”构成了现代性(分叉的现实)出发,一个从“如何”认识(方法论)、解释(认识论)和再生产(话语/实践/体制)出发。但是,另一方面,本体论和非殖民化理论在矛盾分析(Said, 1978, 1994)、对现代性普遍化其存在和认识方式的绝对必要条件及其帝国/殖民的权力意志的解读这些方面是相通的。它们同样拒绝将本体论与认识论间截然二元分立,并且,同样关注他性和外部性,因而可以在方法上相互补充。
方法论设计
杜塞尔的分析解释学方法将历史上被殖民和被排斥的思想体系放到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反对单一认识论的本质主义,要求诠释那些被现代性无休止的进步推力所掩盖的地区、民族、历史、斗争和哲学。其解放哲学(philosophy of liberation)使非殖民主义学者能够从外部性的伦理和地缘政治的立场来思考、行动和重新解释世界(Dussel, 1985)。外部性不是西方现代性之外的物理空间,而“是[现代性]整体的[本体论]基础之外的领域”(p. 158),它淡化了被它排除在外的一切。分析方法(analectics)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汲取营养。它与解放的非殖民化地缘政治的“具体历史实践”相结合、并且投身于这种实践(第160页),在这种实践中得到自我实现。仅仅思考那些被剥削和被支配的人是不够的,还必须思考社会斗争中出现的现实、知识和实践。
分析方法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其“出发点是一个有利于边缘受压迫者的伦理政治选择:尊重他者的外部性;从地缘政治和社会角度讲,倾听他者的话”(Dussel, 1985, p. 175)。他者——主流之外的声音——的外部性、需要和质询(interpellations)是揭露、抵制现代性总体化的力量诞生的前提。倾听,而不是仅仅看到他者,是分析方法提出的伦理-政治承诺。他性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一个在历史上、象征上和物质上被殖民化、被剥削、被种族化、被非人化和被贬低的他人。这样,“他者”也是非殖民化的学者,他们在其位置进行地缘政治思考、得出其伦理上的理解。
卡斯特罗的“受控疑义”(2014)与此相通,因为从形而上学的外部性思考需要他者(概念上的/本体论的)自决。这里,自决指的是拒绝通过探究来中和差异,并将他者的想法提升到概念的层面,而不是将前者留在信仰的领域。受控疑义方法研究、翻译他者的观念,在此过程中“控制”误解或疑义,但不是为了避免疑义,而是为了区分出人类学家自身的概念。换句话说,它是有意地破坏分析者固有的概念,使他们的现实概念接受模糊或疑义。它挑战了传统的寻求“解释、证明、解释、背景化,[和]揭示他人的无意识”(p. 57)的民族志方法。
两种理论转向在方法论的创新上都担负起伦理和政治的责任,肯定了即使现代世界将自己包装成在世界发展的无数种可能中唯一一种值得永远持续下去的,也存在其他更好的本体论假设和认识论承诺。
为什么是他性或外部性?
然而,为什么这些替代方案要从他性中产生?如德勒兹(Deleuze, 1969)所说,“他者”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它能够构建另一个世界,我们能“通过他者的缺席的影响来理解他者的存在的效果”(Viveiros de Castro, 2015: 9-10)。他者是“可能的结构”和“可能世界的表达”(10)。正如分析方法的论证,目前的伦理政治项目是学习如何从外部性的言语行为,即从他者的表达和质询中思考。在这个意义上,从他者的理解的思考,是一个乌托邦的计划,它把与他性和从外部性思考的虚拟层面作为其理论出发点,而不是只思考实际的现代/殖民地事物的秩序。
本体论转向并不是在寻找本体论的基础,而是“优先考虑一个明显的人类学任务,即充分表达民族志的偶然性”(Holbraad and Pedersen, 2017: 68)。民族志的偶然性证明了主流的现代范畴的局限性,将“他者”思想提升到观念的哲学地位。观念不仅代表、而且阐明了一种社会生活,其生产本身也是社会存在的生产和发展。这意味着,观念的生产是一种使政治承诺更加明确的实践,因为它拒绝中立化观念的本体论含义——即他者观念所阐述的世界。
认真对待其他世界并不意味着民族志学者或哲学家“相信”他人的表达和实践。如卡斯特罗(2013)谈到了他拒绝将他者的真理主张简化为信仰,以及这种做法的政治和观念上的含义。他用“山雀是人”(p. 492)这个命题来指出一个本体论的假设,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它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山雀不是人。然而,卡斯特罗问道:“问自己印度人在这方面是否正确有什么意义——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真正值得了解的是我们不知道答案的东西,即当印第安人说山雀是人类时,他们在说什么。”(p. 494)当土著人说两个生命体相同的时候,他们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观念世界?卡斯特罗(2015)解释,如果民族志学者用从他性中产生的概念进行思考,土著对话者就告诉了学者山雀和人类如何相互牵连。最终,这些相互影响表达了一种不同的形而上学,在这种形而上学中,世界是由它与现代性的二元本体论所不能容纳的关系阐明的。
同样地,杜塞尔(1973)讨论了使用分析方法倾听他人言语行为,将哲学家转化为有道德义务向那些人性和尊严被否定的他者学习的研究者的质询:
将他者的话语视为类似于自身世界的话语,同时保留他者的形而上的区别,就是尊重启示的类比。在他者之言的教学道路上,作为教师,每天都要尽力谦卑和温顺,这是一种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是分析学的哲学,辩证地与他者之言并肩而行。哲学家…………知道[这种教学关系]的开始是信任,以及对…………他者的真实性的信念;今天,它是对妇女、儿童、工人、经济落后者、学生的信任,总之,对贫乏者的信任。(Dussel, 1973: 171)
因此,有必要将他性和外部性作为两个理论出发点,使处境哲学的构建成为可能。这两种理论转向通过挑战对现代的种族阶层及其范畴的过度表述,反对对他者的错误表述、征服他者的行为(Wynter, 2003),最终都反对抹杀差异。它们推翻了充作统治工具的现代观念,同时强调了其他世界和知识的存在。二者都属于非殖民化的行动,因为它们的方法论提出了伦理和政治承诺,试图恢复、推进那些指向被剥削、被统治和被殖民的人民、地方和领土的抵抗、存在和韧性的概念。并且,它们承认,放大其他世界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被统治者所面临的问题神奇地解决了。因此,这两种理论转向的方法论和概念项目都有助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非殖民化,以及在现代性的总体化话语和实践之下仍然存在的他者世界实现自决。
编译 | nonsense
初审 | 梁乐妍
二审 | 林陌声
终审 | 李致宪
©Political理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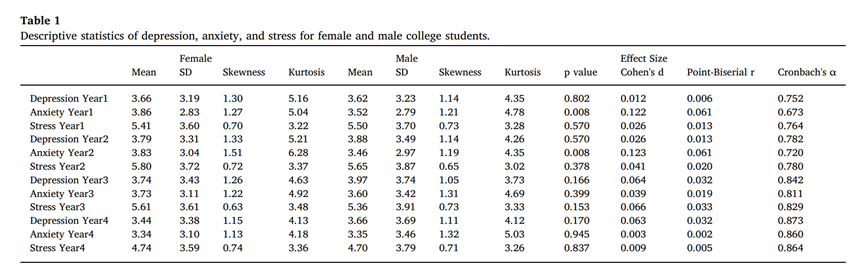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