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份”是自我的一种认知范畴,以及作为对这种认知的再现。主体在世,必然通过具体的身份来确定、展示并规范自我。本文基于对身份的这一理解,探析身份之于自我的意义所在。首先,身份是自我表意的符号化,身份即自我的命名。其次,身份可引发自我作向上或向下的还原。最后,身份之于自我的意义在于,身份是自我认知的符号修辞,使自我得以维系、规范,并将自我意义的诸方面文本化。
[关键词]身份;自我;符号
身份identity 源自拉丁语“idem”,具有两层含义,包括“人格” personality与认同 identification。所以,有学者建议“identity”全面的中译应为“主体的认同”。根据这个译法,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身份。首先,我们常说的某个“身份”其实是主体的一种认知范畴其次,作为对这种认知的再现(represen- tation),身份呈现为具体的角色(character)。从认知到再现认知的上述过程,是自我表意的符号化(semiosis),身份即自我的命名。身份可以复杂多元、变动不居,是自我投射的具体面具而承载具体身份的自我(self),是一个固定的符号模式。主体在世,必然通过具体的身份来确定、展示并规范自我。本文基于对身份的上述理解,探析身份之于自我的意义所在。

一、身份即自我的命名
身份是自我的符号化。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身份是自我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的再现。从根本上身份可以被理解为自我遭遇他者,并与他者共在所必有的经验性“面具”。这里首先涉及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正如任何概念都是将事物“对象化”的符号过程一样“我”必须通过排除他者的他异性,才使自身的概念明晰起来 同时又通过与他者的相似性,使自身划入可以从属的某个范畴。正是通过相似与相异的排列组合,自我方以某种形式得到界定。所以,身份首先是一种关于自我塑形的认知,体现为一种自我意识,是关于主体自身的元语言,即解释自我、赋予自身意义的元符号能力。
洛克(John Locke)曾将个体的人定义为具备思维能力的存在:拥有理性,可以反思,能够在不同时间地点将自己认定为那个相同的思考的个体。该定义旨在揭示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乃自我反思的能力。正是这种自反性(self-reflexivity)使个体可以在不同境遇中能够“将自己认定为自身”。反过来讲,就是能为不同阶段自我的意义活动确立同一个话语源头。这种自反性能力是一种元自我的符号能力,这种能力关切到对个体的论断,即主体能形成一套覆盖自身全域的评价体系。所以,身份即同一人格,是指个体的持续存在,以及这个人对这种持续存在的认知。如当我们在感知、品味、沉思或行使意志力时,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正在如此。哈姆雷特具备足够的元符号能力,因为他的痛苦不仅在于“生死之间”进行抉择的进退维谷,更在于意识到自己深陷其中的境遇。诚如纳博科夫所言,人的本质特性在于,能意识到关于自我的意识(Being awere of the awereness of the self)。由此,主体之于自身的关系,就是我们称自身为“self”,从而将自身与其他事物区分开的表意系统。个体身份就在于 “一个思维主体的相同性”。进一步讲,主体性是将自身定位识别为同一主体的话语能力,这是身份赖以存在的基石。

所以,身份即对同一自我的认同源于主体的元意识,即自反性的同一性,它将自我的过去、当下、未来统一于同一个符号模式(semiotic self)中。洛克曾借用《圣经•新约》说明,身份不在于个体实质的同一性(identity of substance),而在于自我意识(identity of consciousness)的同一性 “当审判的那日来临,每个人将会根据自己所行得到应有的那一杯,而自己是知道这一点的” (to receive according to his doings,the secrets of all hearts shall be laid open.)。这句话印证了对个人身份的识别与论断,不在乎外在化与肉身,而是那个人为其肉身外在化之意义负责的意识,以及同一意识所负责和承担的行为。因为所有的身体都受制于其实质的持续改变,这种改变是渐进的,而语言无法为每个不同的状态命名,所以保留了相同的名字,并被认为是同一事物。如追忆往日的叙述中“我”可以将过去“我”与未来“我”统一于同一自我中,身份成了对某种状态下的自我的命名。所以,归诸实质的身份不是完整的身份,归诸某一个身份的自我,也不是完整的自我。反过来讲,身份作为自我的命名符号化,必须具有持续性,因为它确证了主体的持续存在。正如休梅克(Sydney Shoemaker)所言 “自我是一种逻辑的构建,并且是根据记忆来界定的。”所以,洛克将灵魂定义为由连续的记忆与角色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精神状态。澳大利亚当代女作家麦克法兰(Fiona McFarlane)2014 年的新作《夜晚的来客》(The Night Guest)描述了一位在海滩独居的老太太,每天夜里都觉得有只老虎在她的房子外面徘徊,因而焦虑万分。政府出钱雇了一个钟点工来帮忙照顾其生活,她就给钟点工讲过去的故事。故事通过她们的对白探讨身份和记忆到底可不可靠的问题。
而身份的界定又源于三方主体意识竞争的结果:主体的自我认知、将自己作为认知对象 、他我(alter-ego)的认知。通过胡塞尔所说的移情,从自我的意向性出发所理解的他人关于自我的形象,以及他者的认知:即列维纳斯意义上的永远无法为我所同化、无从接近的绝对他者。所以,根据上述分类,无论出自哪种认知,它将必定不完全是关于自我的真相:前两者是自反性的认知结果,带有明显的唯我论痕迹,因为作为认知对象的自我,不可能被如其所是地再现给主体。用列维纳斯的话语来讲,认知是一种与在完全的意义上处于外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主体接近作为对象的自我的方式,构成对象自我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意向对象,它总是属于由意识的意向性赋予意义的世界。所以,身份注定是自我的片面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列维纳斯提出的主体概念可谓根本性地转向外部,“保持着对没有被归入再现或知识范畴的非自我的开放性。”而意向性也不再只是对某种事物的意识 这意味着某种事物被再现、被知悉、被归还给同者的霸权 ,而是“一种退出自身”,或者更根本而言“与他性的关系”。尽管自我认知只是为了使自我变得可以理解,而非如其所是(as it is)地呈现,即自我不会被完全知悉,但总会被不同地感知,力争成为主体知识中相对固定的内容。认知的理念让我们能够固定“我”的同一性。由此,列维纳斯认为,主体之所以能面对一切降临于它的事物而保持自由,秘密就在于认知。更进一步,身份又同时是对上述自我认知的一种再现。如果说,身份是自我的命名,那么必然包括两个方面 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该认知的再现。因为身份必然体现为主体对自我之角色的承担形式。

如前所述,身份变动不居。它是自我的临时性表演(self-performance),而非完整主体的真实再现。这在后现代呈愈发明显的趋势。因为后现代视域中的符号自我往往是零散、非逻辑、无担待的片段式身份构成的,具有浓厚的游戏和实验性质,将自我投射于某个转瞬即逝的虚拟身份。一个典型案例是粉丝的身份,人们通过做某个人物的“粉”,将自我投射于一个替代性的或移情式的身份,从而得到治愈性的自我充实。
由于自我的认知是一种西西弗式的努力,身份不仅是自我的临时性抛出,而且抛出的是无限接近,但永远无法接近真相的自我之本。每一个具体的身份,都用形式暂时遮蔽、替代了自我,“最后能集合的自我,只能是自我所采用的所有身份的集合。”
身份的表演性和临时性,让人想起“人生如戏”这句大众口头禅,根据赵毅衡的分析,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采用至少六种舞台身份来诠释人生这出戏,得以延续自我:
我认为我是的那个人(即“自我” self)
我希望他人以为我是的那个人(即“面具”persona)
导演认为我是的那个人(即“演员” actor)
导演要用以展示符号文本的那个人(即“角色”character)(笔者认为,此处的“导演”可以理解为执行自我文本化的叙述主体。)
观众明明知道我是某个人:即我本人的名字所代表的人(person),但是被我的表演所催动相信我是的人(即进入角色的人格“personality” 。)
在朱利安•巴恩斯的短篇小说《学法语》中,在养老院里走到人生尽头的那位老太太,坚持与隐身叙述者 与巴恩斯同名的作家“我” 保持信件来往,用絮絮叨叨的信件展现暮年之际她急于实现的不同身份。
二、身份与自我的还原
每个主体,都游弋于不同的身份之间,通过这些身份向自己与他人演绎、诠释自我。所以,自我与他者互为演员或观众,进而构筑具有符号意义的存在模式。因此,自我之于身份,不仅是简单的叠加关系主体的一种关于自身的感觉与思考,或者称为对自己的身份“自我说明”的解释元语言,比如哈姆莱特的装疯卖傻。如果一个人具备充足的反思能力,那么,他的身份就是其自我的自觉延伸,反而有助于调控、完善、充实自我,即个人的意识形态。如果情况相反,自省力的匮乏,会使得身份容易屈从于主体外部符号的欺骗意义,如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常常以“中立”姿态示人,使社会中大多数人相信这是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并因此作出身份的相应选择。阿尔都塞著名的例子“询唤” interpellation,通过一声“Hey,you”语境所赋予的身份,主体将自身定位于某个既定的,或者随波逐流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能欲求。所以,一方面,自我似乎拥有对身份的筛选与整合能力另一方面,身份会迫使自我作向上或向下的还原。

美国的社会符号学家诺伯特•威利(Norbert Wiley)借鉴皮尔斯(C.S.Peirce)的符号三元模式,将自我理解为一个三分符号:从时间上分为过去、当下和未来自我,分别对应于符号的对象(object)、再现体(sign)和解释项(interpretant)。并据此提出自我“向上还原” (upward reduction)和“向下还原” (downward reduction)的概念。既然身份是自我确定的必经之路,而自我是一个三元符号结构,那么,在符号自我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纵观历史上对身份的讨论,可以看出 “身份”并非自我之内在固有,但身份是主体在世生存的必有形式。换言之,身份是自我的一种“命名”。不管是前现代的既定(given)身份,还是现代性强调的自由选择(to choose),或是后现代实验体验游戏中的过程(becoming),都使自我得以塑形。自我通过种种具体的身份自我命名,而解答“我是谁”“我该做什么”“我的选择是什么”等人生问题。正因为是一种命名,身份不是实有之物,而可以游移不定、随境而迁,但与自我的界定又如影随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是观念的产物”。比如论及“为人父母”( to be a parent)时,心理和认知意义(pyschological)上的父母先行于生理意义上 biological 的父母。意即,作为具备有限能动性的主体,自我需要某个具体的身份,才能感知自我、认知自我、规范自我,从而不停地更新自我。“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不断制造意义,规范意义,而又受意义规范的过程”。借用符号自我三分模式,符号自我的图式呈现为:
对象———符号再现体———解释项
过去我———当下我———未来我
被述我———叙述我———聆听我
“我是谁”———身份———“我应当成为谁”
向上还原是指对自我身份作社会一致性的、人际互动的、责任道德的超我解释与需求,将自我置于集体再现的视域之中:向下则是向本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我的、个体心理学的、无拘无束的、无任何担待的, 甚至近乎生理学意义的位移。向上还原使自我成为他人眼中的价值、主体间性的自我,文化符号的自我,对于他人而言,这是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如《圣经•新约》中提出的最大诫命“爱人如己” (to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 love yourself)。又如中国儒学中强调的“克己”、道家哲学中的“上善若水”。哈贝马斯提出的高现代性(high modernism),就是指通过理性话语建立交往伦理乌托邦式的天堂。主张在社会一致性中思考个体身份的,还有法国社会学传统的集体再现,以及解释认知、伦理、审美批判的社会基础及文化内涵,认为集体再现不仅构成并且决定个体与集体身份的定义。集体再现的结构,告诉人们主体是如何对世界进行分类的。而认知、伦理、审美判断是身份的主要参数,使它们产生于社会互动的实际领域中。

不过,极度的向上还原,大于自我所能承担的身份,或许是一种灾难。2014年美国年度畅销小说《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描述了一个活在父母期望中的女儿最终选择自杀的家族惨案。这样的主体身份看话语交往重于内在本能。反过来,过度的向下还原,会让主体滑入不为他者保留任何余地的本能之中,甚至丧失自我控制与自我管理,成为他人的负担甚或烦恼,比如脾气不讨人喜欢的林黛玉、妙玉,“垮掉一代”文学中的浪子形象等。而大多数人的一生在上下还原之间徘徊、掂量。如《哈姆莱特》中,在“to be or not to be”之间进退维谷的哈姆莱特,《红楼梦》中在情与悟之间纠结不已的贾宝玉 电影《黑天鹅》中在黑/白天鹅角色/ 人生之间不知所措的芭蕾舞演员妮娜。这里涉及还原过程中的两个课题是首先,在多大程度上作了向上的位移?自我是以什么作为新我的标准?
作更深一步的推究,这里会卷入对自我的疑问:身份的演绎性、临时性以及上下的不断还原,是否说明自我是一个虚假概念,因为在自我进行位移时,很难断定那个真实的自我到底在哪儿,或者说,自我的持续性、一贯性与稳定性何以得到保证。在人类历史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不同时期的身份定义,跟随不同的历史 文化语境而发生着变化。在前现代传统社会中,身份被理解为外在决定之物,比如部落社会中,由血亲关系决定你是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即典型的“情景中心”文化模式中,个体的身份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人际网络中是既定的,并且,自我一生的轨迹也是因既定之物而被固定的。所谓“安分守己”,正是此意。然而,现代性语境中的身份定义日趋多元化。一方面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力量,正通过日常生活,渗入主体的 血脉之中。另一方面,随着媒介发展过程中,对个体提供的虚拟空间形式多元化,多元的社会空间和身份流 动性的增强,为身份的自主定义开启了大门。从而,我们“不得不自由地”选择身份。韦伯注意到,在很大程度上,因来自生活各领域的多元性而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的主体性正在被去中心化。所以,针对这一情况,成熟的身份意味着连贯一致,有所衡量地接受并承担起这些多元需求。
现代意义上的责任,意味着为自己行为所致的结果肩负责任,而这在日趋复杂的当下社会中显得愈发困难。在传统社会中,我们的生命在一种明确的信仰或至少是道德旨归的引导之下,是确定的。而现在却不得不由自己来决定,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身份形式进一步临时化、虚拟化,甚至形成一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有学者指出,这就是为何中世纪底层的民众享有一种精神上的宁静,这是现代的人们永远无法得到的。而当代社会的文化语境是向两个反方向发展,符号能指身份的无限增生,与所指自我意义的日趋落空与轻浮。哈贝马斯反对裂变追求总体性,应当说他为后现代的过渡分裂化狂潮提出了必要的遏制,但利奥塔则反对总体性而拥抱异质性。利奥塔斥责哈贝马斯不合时宜地重复古典哲学的宏大叙述,德里达也批判哈贝马斯不顾当代社会走向分化的基本事实,试图重复一去不复返的一统社会。后现代语境则要求更加增强对身份的这种选择意识,即个体可以下意识地实验身份,或者说身份可以游戏化。随着集体再现话语的衰减,身份似乎经历着从外在决定向上、向内在选择向下的过程。随这一衰减和转变过程的,是一种对身份的焦虑感。“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对身份过分的渴求也是致命的。
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心理学原理》中曾言 “如果可行,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如此 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游,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当他出现时,其他的人甚至都不愿稍稍侧身示意 当他讲话时,无人回应,也无人在意他的任何举止。如果我们周围每一个人见到我们时都视若无睹,根本就忽略我们的存在,要不了多久,我们心里就会充满愤怒,我们就能感觉到一种强烈而又莫名的绝望,相对于这种折磨,残酷的体罚将变成一种解脱。”身份不再是组织生命的意义单元,而更多地成为断裂自我的宣泄与欲望之投射。

历史上关于身份的讨论也是因时而定的。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所说的那种现代性的身份可谓转瞬即逝,旨在重申巴洛克寓言中的感观性。它应和了齐美尔在 20 世纪末提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种现代性其实是大多数现当代社会学理论所排斥的。随着身份的形成已经从生产领域切换到消费和娱乐领域,身份再现也从宏大叙述领域置换为离散的临时个体抒写。这要求更强程度的自反性并增长了自恋的情节。比如,我们自恋地依赖他者以成为自己,只有他者才能形成消费资本的符号价值。当身份不再是向外的投射,而是一种断裂的内化 自恋就成为一种身份“诊断”。
三、身份之于自我的符号意义
身份再现静态的、既定的自我形象,是为了催生动态的、更新的理想形象。身份体现为一种对自反性的呼吁,旨在平衡不同角色需求,使主体更加意识到对不同自我的筛选。由此可见,身份的意义在于解释项-未来我。身份是当下我抛出的临时符号文本,这个符号文本整合了过去我的经验,向未来我的期望奋进。所以,主体的存在表现为一种“争取未来的斗争”,表现为一个存在者为了维护其未来而产生的操心。未来能够为一个在当下忍受痛苦折磨的主体带来一份慰藉或补偿。这种安抚慰藉所承诺的,是一种现在因为先行到未来,而将从回忆中受惠的未来。“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詹姆斯对“自尊”提出过一个公式,认为个体的自尊受制于时时刻刻督策我们的理想及我们为理想所付诸的行动,取决于我们实际的现状同我们对自身期待之间的比率:自尊=实际的成就÷对自己的期待。这里的期待就是主体关于未来自我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the future self)。比如,整部美国文学史可以被视为一部关于“美国梦”的兴衰史。

在第一节中已经讨论过,身份是通过自我再现,而将自我认知与意义链接起来的符号再现体 它指代了单子式的自我,却通过对自我的询唤,迫使自我与他者“面对面”,而隐射共在图式中的自我。第一人称视角,“使我们通过认知他人而认知自我”。身份,使自我生活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中,自我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中涉及身份。身份使自我得以把握一个变幻莫测的经验世界,使自我的意义明晰起来。并且,符号的无限衍义的属性说明身份永远无法符合他者对我的认知,而只是无限接近,但并不能揭示显明他者。因为对于自我而言,他人只不过是另一个自我,认知他人的途径依然是通过移情向自身的回归。用列维纳斯的话而言,他人代表了一种无对象的维度,让自我形成一种没有目标的饥饿,他人是我所不是。与他人的对话关系,成为构建身份的根本方式。正如任何符号之于自我的境遇那样,主体一旦开启自我文本化,身份就在新我与旧我之间不停繁衍意义与认知。
身份成为自我反思的符号学命题在于,作为意义的符号组合,任何文本都有其身份,对任何文本的理解, 都源于对文本身份的理解。所以,主体对周遭文化的释义,始于对文本身份的了解与识别。比如,将钢琴经 典曲目视作某学校的上课铃声,此铃声背后的身份是学校的权威,对李少红版的《红楼梦》的解读,离不开对这位导演细腻风格的前理解。反过来,主体对自身的维持与发展,也是通过自觉的文本身份链接而确证强化自身。如《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述者“我”,在永不止息的写作身份中确证自我的存在。蒙田在其自传性的《随笔》中,才意识到“自己就是他现在所了解的那个人”。身份,成为关于自我认知的文本。自我实质是一个叙述构建的过程。身份的叙述符号化,是理解自我的形式条件。
当自我对身份具备自觉的整合筛选能力时,反过来,身份对于自我而言,具有一种双向调节的意义。有学者指出作为个人价值的组织者、实践的整合者及符号能力的优化者,身份对一个健全的自我而言至关重要。良好的身份是自我融入世界的桥梁。但是,假如身份对一个人从心理、社会意义来讲并不真实的话,那么,反而会成为内容与结构之间的阻碍,扭曲符号能力的正常运作。
四、结语
自我是身份关系这一形式的组成项,而主体都是通过完美地包裹着自我内涵的自我形式来理解、思考、诠释世界。形式是事物显露自身并给我们把握它的机会的途径,是事物身上被照亮的、可被领会的部分,是支持事物的载体。事物永远是立体的,它的外表包藏着它深层的东西,同时又让它显现出来。但当我们深入事物之现实 自我时,这种深入不能打破形式身份,而只是滑过了形式的表面。于是,在世之我在走向自我的同时也退出了自我,它有着一个内在与一个外在。而正是通过意义,自我的外在才得到调整,并与内在产生关联。由此,身份是自我认知的符号修辞,使自我得以维系、规范,并将自我意义的诸方面文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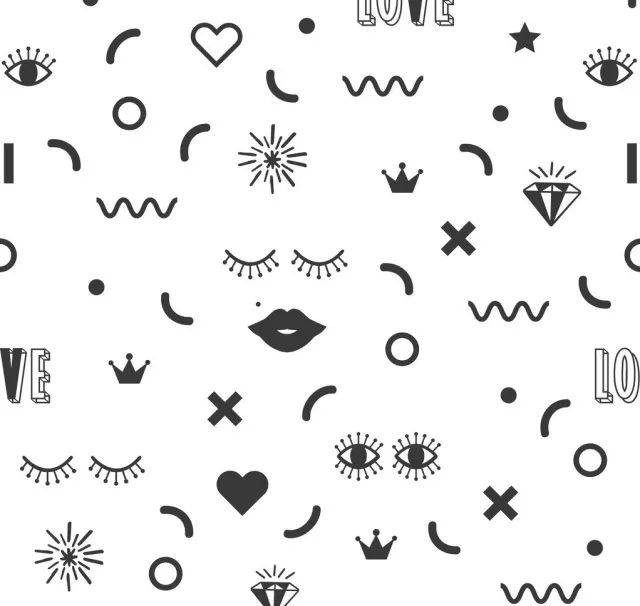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文一茗1981— ,女,文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叙述学、符号学。
本文刊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