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播技术革命可称之为一场“元技术”意义上的技术革命。所谓“元技术”,即是指在诸多信息传播技术之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起奠基作用的技术形态。新传播技术是一种“技术中的技术”。“元技术”引发媒介技术革命,释放的裂变效应是系统性的,影响范围不再局限于社会系统局部和个别系统,而是全域性的。从技术与个体、社会的关系看,其影响又不仅在社会系统层面,还深深嵌入人类自身。“元技术”的技术活性所激发的影响是全息、全员、全域、全时性的,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介技术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依赖,也打破了社会系统对技术社会化效应的刚性约束。强大的社会建构在“元技术”效应的深广影响下,社会的组织性和结构化开始解构,整个社会系统因元技术影响,其既有的结构和逻辑的有效性被大幅度稀释,社会系统开始了新一轮的系统调适,进而孕育新的结构和系统逻辑。“拟现实社会”由此孕育。

新传播技术革命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技术体系创新扩散过程,这场革命在技术层面、社会效应层面表现出与以往人类传播变革迥然不同的特征。
一是去物质化。当下的新传播技术是一种去物质化的传播技术。这种技术脱离了物质性的规定和约束,重建了去物质性的交往场域。
二是数字化。新传播技术以非连续的、离散的数字为基础,它摆脱了原子化物质形态的束缚。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它赋予传播实践更多活性、想象力、自由度,赋予人的意志和想象力更大的表现空间。数字技术不再是模拟的技术,而是建构的技术。数字化传播技术不再是被动的“冷”技术,而是更具有能动性和建构性的“热”技术。
三是个体化的社会化。数字技术释放出了人的个体活性,最大限度地让个体脱嵌于社会,一个个去社会化的个体转场数字空间,在“去物质性”的场景中重新缔结社会关系,并再社会化,而这种再社会化的逻辑迥异于传统社会化逻辑。
四是复杂性。在新传播技术建构的场景中,因摆脱了物质性的约束和现实社会结构的限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逻辑显得更为复杂,群体传播所蕴含的复杂性超越了传统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边界。
五是图像化。新传播技术借助图像符号,建构了诸多拟现实的场景,这些虚拟现实与实在现实之间相互渗透、互嵌,形成了“拟现实社会”。
出现“拟现实社会”既与新传播技术革命的历史趋势密不可分,又与人类的本性息息相关,是人类本性与新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耦合。
首先,人具有想象的天性。新传播技术革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强有力地激发了藏于人类自身深处的“想象密码”,并将其进一步放大。其次,新传播技术革命彰显了与众不同的特性,推动了社会的“拟现实化”。其一,新传播技术使对象脱离物质性规约,既可“脱域”于实在世界的牵绊,又能将“想象”以媒介化的方式呈现并建构出来。媒介传递信息所使用的“媒介”(通常以为的“内容”,如图像、文本等)成为人们关注的表象,而对其更本原的“物”之本真性(“媒介”之后的东西)却不关注。其二,以技术为中介的经验的提升以及以直接的知觉经验的下降。其三,权威与判断的转化。人类对社会现实的判断经历了从虚幻(神)—实在(个体的人)—虚幻(算法、人工智能等新传播技术)的转变。其四,“后真相社会”是社会“拟现实化”的重要表现,新传播技术在其中起到推动作用。
“拟现实社会”是一个“脱实向虚”的进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界面融合和互构过程。在这一转场过程中,现实社会与拟现实社会之间虚实相生、交互塑型,为人类社会实践打开了新的世界,催生了人类社会结构逻辑的嬗变,也给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命题和新挑战。

新传播技术改写了空间和时间对于实在性和物质性的依附,出现“脱域”趋向;与此同时,社会场域中的时间性也因新传播技术的影响,使得“时间”的表现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实在世界和虚拟空间的交互渗透,使社会“虚实交融”“持续向虚”的力度不断加强。在“拟现实社会”,人与人的交往虽然具有极大的选择自由度和便捷性,可“脱域”穿行在去物质化、去时空牵绊的时空里,可以“脱实向虚”,展开交往和行动,但由于人的交往和行动都是社会性的,不可能清空其所有的社会经验和社会化习得,也不可能祛除人的前社会记忆。那些身处虚拟空间的人,也不是社会“空心人”,他们会带着既存的社会经验和结构记忆,进入新场景,开展新交往。这种新场景、新交往预示着人类实践中结构化生产的重要调整和转向,原本更多以现实可见的结构性资源与要素为主的结构化生产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开始向来自以数字化技术为依托的技术体系的结构要素转移。因新传播技术的广义联结和赋能,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规定,社会场景、社会角色、社会行动以及长期演化的制度和文化均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化。

在“拟现实社会”中,传播技术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关键变量,成为连接社会主体和社会场景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新传播技术赋予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空间和实践可能性,人的脱域行动变得更加自由,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也更加模糊,造成社会交往空间的天量级拓展,社会关系变量也变得异常复杂。这就使得“拟现实社会”结构逻辑也显得特别复杂。“拟现实社会”的社会结构不同于传统社会结构,其结构复杂性在于:它并非清空和颠覆既有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记忆,不是在传统社会结构之外再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而是在既有的现实世界之中全面渗透了新的社会场景,嵌入了新的社会结构,即“拟现实社会”与现实社会复杂地套嵌在一起。
新传播技术革命催生的“拟现实社会”,让人类建构社会现实的主动权正在被销蚀。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信息传播的主导力量遭遇颠覆,人正在成为传播秩序之中被动的参与者和被建构的一方,天平开始向着新传播技术体系倾斜。新传播技术“自我扩充”的力量越来越强,这就使得社会现实与仿真现实并存并相互作用,社会“拟现实化”的趋势愈加显豁。这个“拟现实化社会”的未来究竟会如何,其不确定性仍然很大。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姜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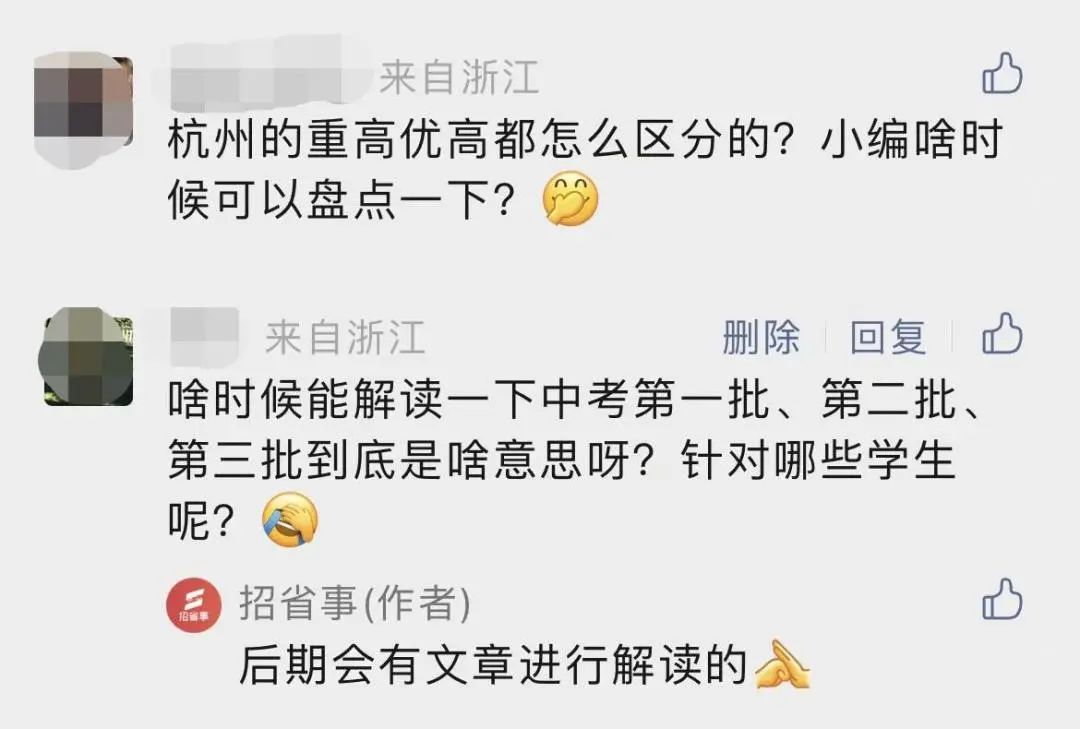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