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1为2021级MSW学生伍楚琪
摘要
世界各地区对精神健康的理解与西方不同,在全球趋于一致地定义精神疾病和治疗精神疾病的背景下,以西方的方式来承受心理痛苦的现象有:精神疾病的确诊率高企、对本土心理健康解释模型的忽视、西方医学语言促使精神疾病污名化、精神科药物的不合理使用。作为精神专科医院中的精神医务社会工作者,需敏锐觉察中国本土文化对精神健康的影响、警惕西方医学霸权对社会工作信念的打压摧毁和陷入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介入误区。
关键词
精神卫生 ;医学人文 ;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是美国著名作家伊森·沃特的著作。他以一个心理学记者的独特身份,通过采访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心理疾病案例,生动展现了关于厌食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在不同文化中的呈现,阐述美国心理学范式是如何在医药商业利益驱使下输出到全世界,潜移默化地改变本土心理疾病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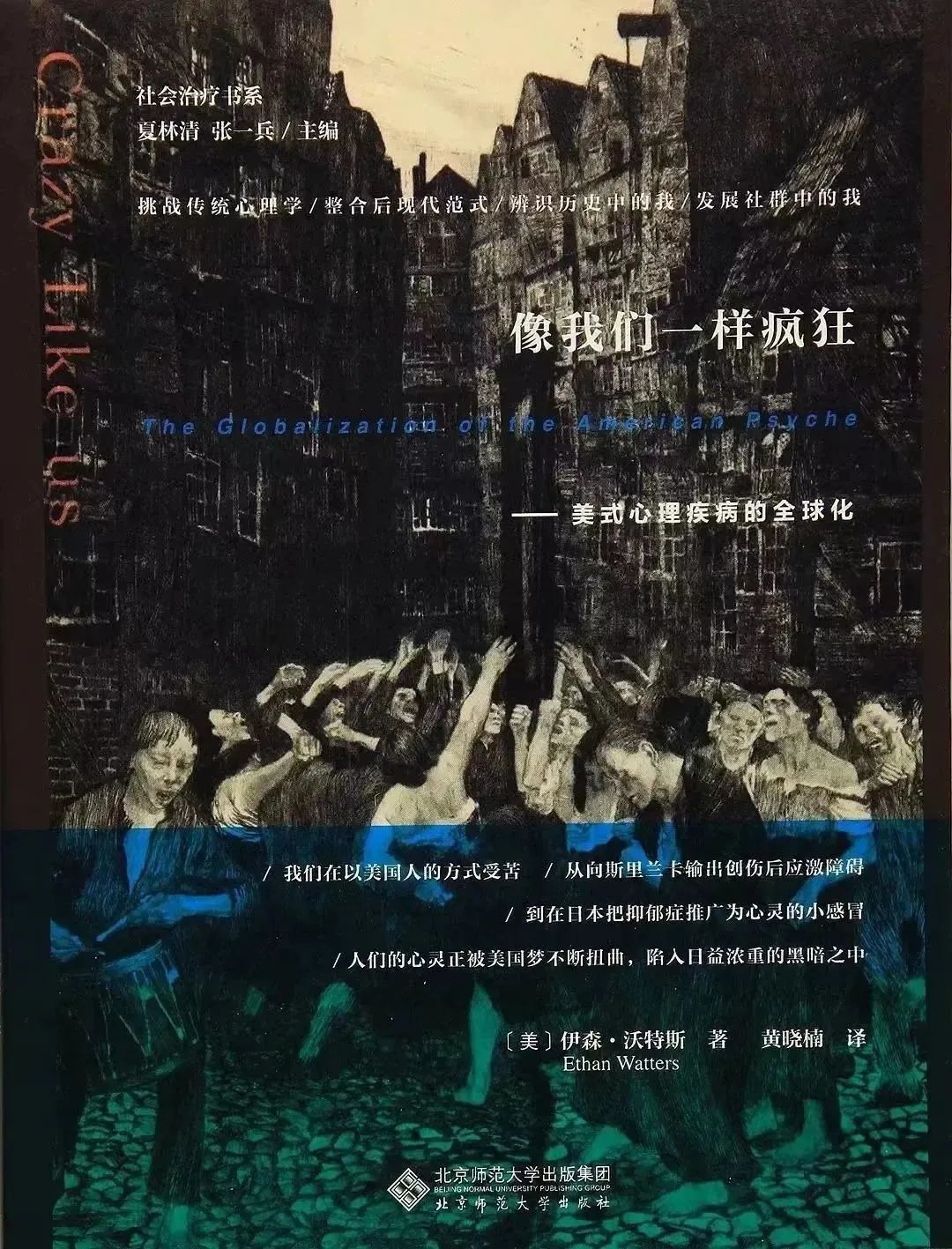
图2为《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一、我们更容易“生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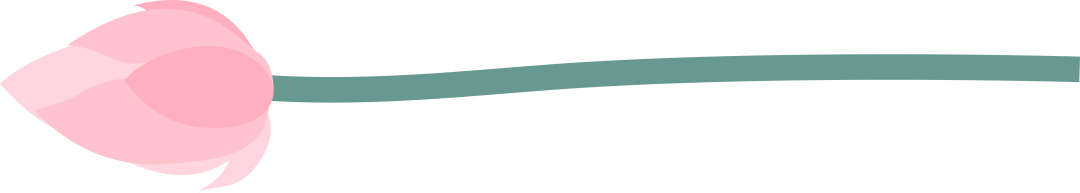
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更新,精神科医生们对于什么才算“真正的”疾病这一观念跟着不断变化,由此病人所呈现的症状也会有相应的变化。这些改变,使得身心症有着自己的动力学:症状是被医治者所塑造的。另外,当社会在经历广泛的焦虑和冲突时,新的心理疾病和外来的信念会进入我们的新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文化中的民众对心理健康的观念。
在神经质厌食症获得正式名称之后不久,这种疾病的发生率就开始戏剧性地攀升。是名称的确立让医生突然能够识别并报告他们先前忽视的案例呢,还是说病人们在无意识中努力地创造症状,以配合当下的医学诊断呢。霍乱的疫情让日本民众首次认识到西方的医药概念,西方精神医学是通过危机事件被带入日本大众意识层面的。一些新颖的心理健康话题吸引着人们持续而强烈的争论。日本人们变得不停地担心自己心理健康方面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因此反而更容易生病。这就是文化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无意识,我们在无意识中跟随大量的文化暗示,而我们却似乎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
二、不同文化下的“症状”各具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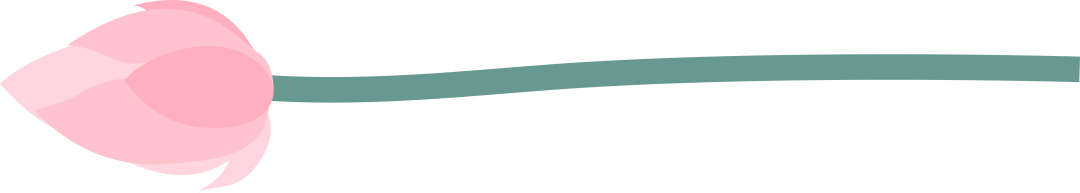
就PTSD而言,其“症状”在各个文化当中有巨大的偏差,比如,经历过长久内战的萨尔威多难民妇女常常会体验到被称作calorias的症状——身上感觉灼热。尽管这些妇女也会有睡眠紊乱——PTSD症状的一种,但当她们暴露在象征她们创伤的刺激环境之下时,却很少报告惊吓的感觉或其他躯体的反应。而对一些柬埔寨的难民来说,创伤带来的最紧迫的心理影响就是感觉有怨气的鬼魂找上门来,同时伴随强烈的难过,因为他们匆忙逃难离开自己的国家,无法为死者办理后事,在这个例子当中,很多症状都尚未被现有的PTSD清单提到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创伤的具体表现总是与同一时代的文化信念紧密相连。再如抑郁症,日本有一个关于抑郁的精神医学术语:utsubyo(忧病),它是较为接近目前我们对抑郁症的表述。忧病形容的是那种让人根本不可能正常工作,甚至无法假装正常生活的疾病,这程度的症状与抑郁症的症状清单并非一致。日本人主要是以“yojo”(养生)的概念来看待健康问题。这个概念是在七世纪到十世纪从中国传去日本的。养生将健康与节食、意志的控制、运动和禁欲联系在一起。它关注的并不是如何去去除疾病或者如何长寿,而是社会关系上的健康,包括道德、文化和教育。Utsusho(日本传统的“抑郁”概念)并不被视为一种疾病,而是一种受人尊敬的心灵境界。而时至今日,日本传统的养生观念不断地被新的eisei(卫生)观念取代。有学者在解释中国文化特有的缘、风水等现象时指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采用的是宿命自由主义( ftalitic voluntarism)的生活策略,即在认可命运安排的前提下鼓励个人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这样,既承认生活中的限制,又注重个人主动性的发挥,把承认生活中的限制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糅合在一起,同时面对和处理两个方面的生活要求。也就是说,只有同时处理好生活中的这两方面的要求,才能保证精神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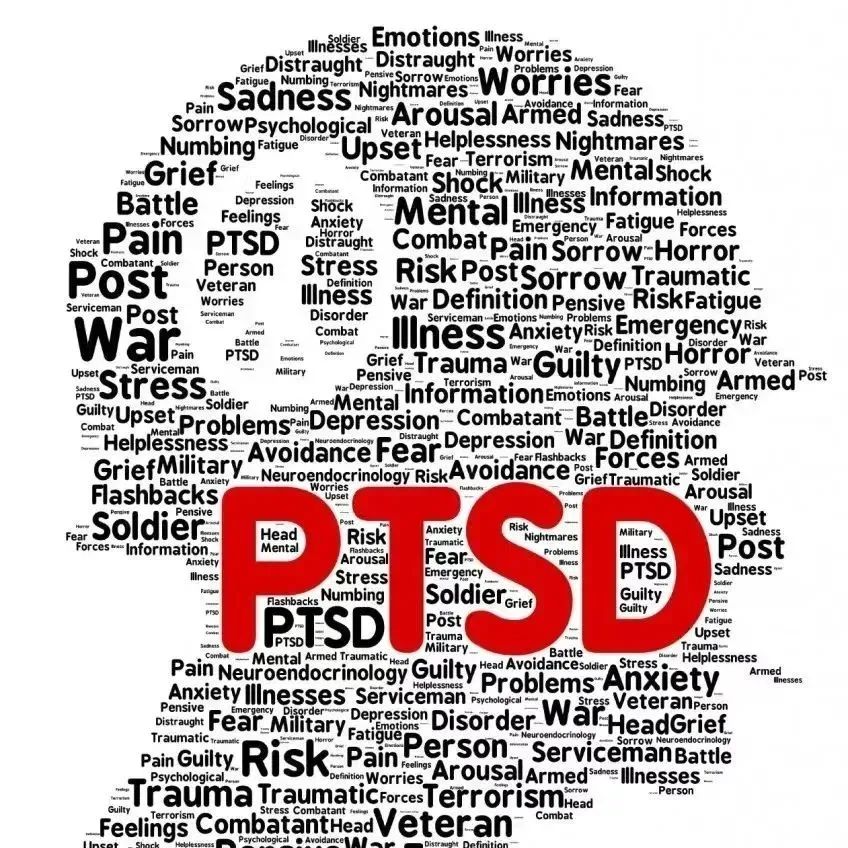
图3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研究人员科迈尔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不同文化的“解释模型”造成的,由于不同的文化对痛苦的不同阐释,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会把痛苦体验算作疾病。正如洛克表明的,一个文化所认定的病态通常就是它所宣扬的价值观的反面。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在这点上非常独特:他们既愿意对陌生人公开表达情绪和难过的感觉,又非常倾向于将心理痛苦视为一种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由于其他文化的人们通常以社会和道德的意义来解读如此的内心痛苦,他们寻求慰藉的来源通常只会是家庭成员或者族群里面的长者或精神领袖。在超出自己社会圈子的范围之外寻求医生或精神卫生专业人士的帮助,在这些传统下是无法理解的。我们理解不同文化下的“症状”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明白当地人描述痛苦的习惯用法——在这个特殊文化背景下,他们理解、体验和表达心理需求的特定方式。如果心理健康从业者无法看到自己病人身上的个体和文化差异,那他们便无法理解病人的主观的经验,无法对病人产生共情。心理疾病不能脱离社会历史背景单独存在。历史就是充满了不断变化的症状,而塑造与促成它们的,最主要的都是现时的医学体系的期望和信念。
三、生物医学语言加重污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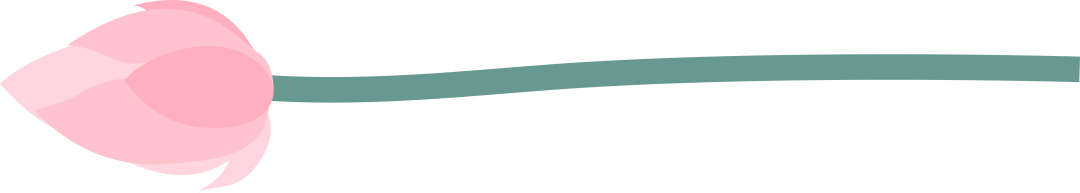
一个文化会给自己的成员提供一套现成的情感和行为脚本,以应对各种生活状况,包括疾病——它提供范例,面对病重的亲人时,人们应该或可能如何感受、如何行为。比如在本书的例子中,桑给巴尔地区的病人家属阿米娜不会认为做家务这种有效行为与健康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这和西方的康复治疗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西方的精神康复界认为,精神健康的恢复之路就在于病人是否能够有效做事或参与集体活动。而在阿米娜家中,病人时而出现的病态行为并不会带给家人太多担忧或警惕,而相对好转的时候也不会热烈庆祝,因此病人姬姆瓦娜自己并没有什么压力,她不会认为自己是个得了终生心理疾病的病人。这或是某种策略的一部分——明明是个沉重的疾病,全家人却非常默契和轻描淡写。呈现这个例子的重点不在于有效反驳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学病因理论,而是通过这些生动的例子,让人看到诸如鬼魂附身这些被现代西方医学摒弃的说法是如何使病人能够被继续容纳在社会群体里面的。
过去两代以来,西方心理学家和精神医学家认为生物医学观念能够减少人们对这些疾病的污名化,那些接受了西方生物医学疾病观念的人们就被视为更有“心理健康素养”的。在这场“胜利”背后,心理疾病污名化的倡导却“节节败退”。研究发现那些接受了关于心理疾病的生物医学和遗传学信念的人正是最不想和病人打交道的人,他们认为精神病人十分危险,充满不可知因素。这因果联系已经在全世界许多研究中被证明。不论在什么地方,对精神分裂症生物因素的强调都与更大的社会疏离表现出相关性。在公众当中宣传疾病的生化概念并不能促使人们减少对心理疾病患者的疏远。希拉·梅塔教授做的一项实验显示,当我们听到疾病术语描述人们的心理或精神问题时,我们实际上可能就会用更严厉的态度对待他们,我们总说自己很和善,但是我的行为表现出相反的结果。本书作者认为,单单是对精神分裂症这个医学名词的命名方式就能够对其愈后结果和污名化产生负面影响。当我们认为对自身的体验没有完全的控制感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深深害怕那些看似失控了的人。而现代西方精神医学的生物化学论调,认为所有的问题和痛苦归根结底是因为个体脑部化学物质失去平衡,这样便简单粗暴地把文化的影响排除在外,个体全然背负了“失控”的所有罪名,并随时需要“精神医学”来拯救。一名遵循生物医学视觉的家属会试图去管理妹妹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因为他会运用自己对疾病的生物医学的知识来证明自己对妹妹生活的掌控是有道理的。
四、药物不是解决痛苦的根本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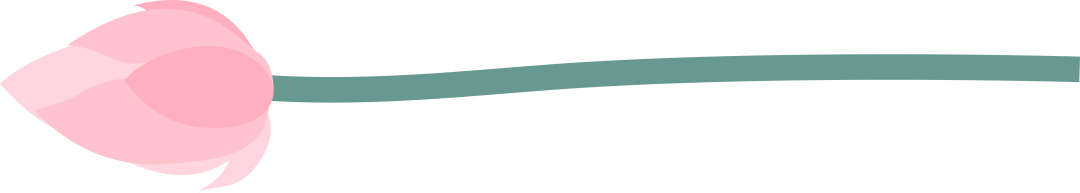
最前沿的精神疾病研究不是在人类学领域,而是在西方世界的“纯科学”的领域。虽然导致精神疾病的病理发源和大脑部位究竟在哪里,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但是大家普遍都认为,对这类疾病最令人兴奋的研究进展是来自于脑科学家的实验室。在日本,他们的长期历史中将自杀看作是一种表达个人决心的传统观念,常常被视为一种纯正日本精神的表达而能获得理解甚至欣赏。日本的悲伤文化——相比于转瞬即逝的快乐,苦难才是人生体验中更加持久不变的真实。承受深度的悲伤不但不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力量和卓越人格的标志,大部分日本人的自杀和抑郁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是因为“羞耻”而死。因此SSRIs在90年代初在日本根本没有市场。为了弱化抑郁症(日本翻译成忧病)的含义,医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市场推广人员借用了一个比喻,效果十分显著。他们在广告宣传材料中不断地重复说,就好像“心理上的感冒”——这传递了三个信息:不是严重疾病所以不应带有羞耻感、吃药很简单就像吃感冒药一样、抑郁症很常见,谁没感冒过。抑郁症如此的普遍和宽泛的定义,让抑郁症的患者剧增。在治疗抑郁症的药物中,SSRI药物帕罗西订和艾司西酞普兰的推广上均使用维持大脑神经递质5-羟色胺平衡作为宣传点,但事实却是,到目前为止科学界都没有形成共识说抑郁症和5-羟色胺缺乏有关联。美国精神医学出版社所出的《临床精神医学教科书》上清楚写着“尚无更多案例证实,单胺类(5-羟色胺是单胺类的一种)分泌不足假说”。在许多未被发表的研究中,SSRI都没有表现出超过安慰剂的药效。医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最初提交给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数据从未被发表出来,这些数据显示,制药公司在故意隐瞒药物的试验结果和被试的情况,因为这些数据显示了药物将自杀风险增加了八倍。
另一方面,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与高度的情绪表达、家庭的情绪温度、情绪上的过度卷入高度相关。常常复发的病人的生活环境里经常有至少一个亲人会规律性的批评他们或试图控制他们的行为。表达性情绪方面的专家指出,虽然他们没有在情绪温度和精神分裂的发病两者之间建立什么联系,高度的情绪表达不是该病的原因,而是影响病程和愈后的一个因素。疗养机构的职员或精神病院的护士的情绪表达程度高低的研究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高度的情绪表达(emotional expression ,EE)和其他心理疾病愈后表现之间存在相关性,被批评或不断被查看、判断的体验正好和精神病的体验本身是平行重合的。
本书作者提出在这里有一个矛盾点:如果是不切实际的社会期待和高情感表达的家庭造成了人们的压力,那为什么要每个人来吞药片来改变大脑化学平衡呢?但事实往往是,当我们的社会陷入重大的焦虑危机中的时候,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很快就会有一些新的药物出现,承诺能处理这些问题,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心理疾病标签来解释我们的痛苦。
五、美式快餐,我们正在逐渐失去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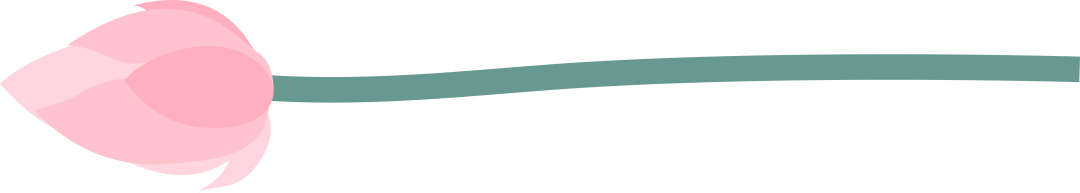
在美国DSM诊断标准下,心理症状是如何变得“流行”起来和逐渐“消亡”的呢?本书从香港的厌食症和欧洲历史中的癔症例子来说明:每次重复厌食症这个概念,都会加重人们头脑中无意识的信念,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更容易尝试用限制饮食来传递讯号,以表示自己内心正在遭受痛苦。经历这种症状的人越多,公众和媒体对此疾病的关注就越大。而新病人的表现,也越来越接近此病的西方版本。癔症方面,一旦轻度的癔症症状变得常见,它就开始不再具有传递深处内心痛苦的效力。随着这种能力的消退,这种症状渐渐开始从文化和医疗的视野中淡出。马克·麦凯尔(Mark Micale)《接近癔症:疾病及其解读》中写道:这种疾病遭到了临床上的“过渡引申”。那种带来先进知识的“西方专家”的角色——沙阿医生(海啸发生后离开美国来到斯里兰卡提供帮助的精神科医生)写道:像我自己这样的专家所突出渲染的,是一种胜利主义,它蒙住了我和其他救灾人员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那植根于当地文化中的自我概念和医疗实践。他们本能地认为本地的观念和做法是低劣落后的,他们为的是强化一种殖民灌输式劣势感,使当地人民自认软弱无能,怀疑自己有能力建设家园美好的未来。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可能对待创伤事件有着根本不同的心理反应——这一点对美国人来说实在是很难接受。CARE——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全球发展组织(Global Development Grout,GDG),美国国家PTSD中心以及欧洲创伤事件研究协会等机构和组织的服务基本概念里均认为“从根本上,全世界人们的情绪体验和表达都是一样的”。冯·比特医生认为这是一种对情绪体验的普世抽象概念,他们遐想全人类都是以基本类似的方式面对恐怖的灾祸。比如斯里兰卡人的幸福安乐感是来自于他们和自己社会关系网的联系,对一个斯里兰卡人而言,心理健康的直接表现体现在帮助他人的行为上,而不是心理健康三原则。
本书作者认为,用西方最新的心理健康理论来减轻全球化今次所导致的心理压力是行不通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大麻烦的一部分:一个文化去塑造另一个文化的人民如何归类一系列症状,替换掉自己原有的解释模型,并重新划分哪些是正常的行为和内心状态,而哪些又是病理的;通过既破坏本土的疗愈信念又削弱来自当地文化的自我观念,他们正在快马加鞭地加速这些令人迷茫的现象——这正是今天的世界上许多心理痛苦的最核心问题。
六、精神医务社会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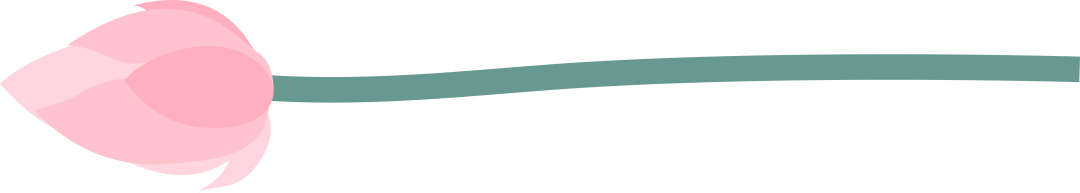
这本书可能会给整个心理和精神卫生界带来不公正的污蔑,但作者的重点并不是说所有传统文化都是对的,而是:每个传统文化都各有特色,与现行的西方精神医学诊断体系不同。《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给在精神专科医院工作的精神医务社工带来了一些共鸣和思考。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是目前医学界推行的新医学治疗模式,该模式强调除了生物机制对精神疾病的影响外,在治疗过程中要同时重视患者的心理、社会等因素对治疗的作用。医疗服务的内容从疾病为中心转向了以病人为中心,从纯粹的生理性、技术性的服务扩展至社会性、心理性的服务,医患关系由主动被动型转向了指导合作型的伙伴式关系,医生角色的专家色彩淡化,而指导者与服务者的角色在突显。随着《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2018年《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国家政策文件相继出台,社工进入医疗领域开展服务也打开了新的局面。精神科社工作为医务社工的独特分类,因其在精神卫生服务团队中的重要性而受重视,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落地提供了支撑点。
精神专科医院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近年来逐渐在传统药物治疗上增加了心理和社会治疗的元素,但效果却并不显著。归根结底,是医院虽然采取了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服务模式,但受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目前仍然沿用了生物治疗视角看待患者,从修补的角度增设心理和社会康复活动,让患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康复训练,这样不仅不能提高患者的自我判断和选择能力,也无法帮助患者整合不同的服务促进自身的改变,或者改善与周边他人的社会支持关系,医务社会工作与医学之间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的关联,医务社会工作虽然是在医疗场域内开展,但仅仅是社会福利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与发展,并没有与医学产生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1]杨锃.“反精神医学”的谱系:精神卫生公共性的历史及其启示[J].社会,2014,34(02):60-93.DOI:10.15992/j.cnki.31-1123/c.2014.02.001.
[2]童敏.文化处境下的精神健康概念及其对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5):126-129.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10.05.032.
[3]童敏.生理-心理-社会的结合还是整合?——精神病医院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探索[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7(02):1-7+23.
[4]杜治政.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实践与医学整合[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30(09):1-5.
[5]童敏.文化处境下的精神健康概念及其对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5):126-129.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10.05.032.

文/伍楚琪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