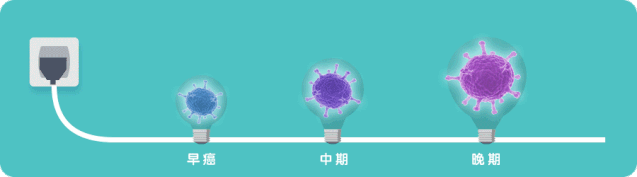
我们作为一个物种能够生存下来,不是因为我们动作快、身体强壮,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指尖拥有天然武器,而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社会保护。
例如,早期人类只能通过群体狩猎来消灭大型哺乳动物,我们的优势在于沟通和合作的能力。
但这些强大的社会性最初是如何形成的呢?芝加哥大学认知与社会神经科学中心主任约翰·卡西奥波(John Cacioppo)提出,社会关系的根源在于它们的对立面——孤独。
根据他的理论,孤独的痛苦促使我们寻求陪伴带来的安全感,这反过来又通过鼓励群体合作和保护使物种受益。
孤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为群居动物的进化提供了必要的好处。像干渴、饥饿或痛苦一样,孤独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状态,动物们会寻求解决这种状态,以提高它们的长期生存能力。
如果卡奇奥波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一定有一种内在的生物机制迫使孤立的动物寻找伙伴。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里肯定有什么东西让独处的感觉很糟糕,而当我们和别人在一起时,就会感到轻松。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已经在一部分被研究的神经元中找到了这种动力的来源,这些神经元位于大脑的一部分背叶核。
根据今年早些时候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刺激这些神经元会促使孤立的小鼠寻找朋友。这一发现为卡奇奥波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并阐明了大脑特定结构与社会行为之间的深层联系。
这项新研究是第一个将特定神经元与孤独联系起来的研究,卡奇奥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发现共同帮助将孤独从心理学和文学领域转移到生物学领域。
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孤独的神经
吉莲·马修斯(Gillian Matthews)偶然发现了孤独的神经元。
2012年,她还是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一直在研究可卡因是如何改变小鼠大脑的。
她会给这些动物注射一剂药物,把它们单独放在笼子里,然后在第二天检查它们特定的一组神经元。她对一组对照组的小鼠做了同样的实验,不过,给它们注射的是盐水而不是可卡因。
当马修斯在给小鼠服药24小时后,她期望看到小鼠脑细胞的变化——神经元连接的加强,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可卡因如此上瘾。
令她惊讶的是,接受药物治疗的小鼠和对照组的小鼠在神经元线路上都表现出了相同的变化。一夜之间,与某一组细胞的神经连接变得更强,不管是否给动物药物。
这些让她感兴趣的脑细胞会产生多巴胺,这是一种大脑化学物质,通常与愉快的事情有关。当我们进食、性交或吸毒时,多巴胺会激增。
但它不仅仅是快乐的信号。大脑的多巴胺系统可能被建立起来,以驱动我们寻找我们想要的东西。
研究人员将重点放在大脑中缝背核区域的多巴胺神经元上,该区域因与抑郁有关而广为人知。(这可能不是巧合——孤独是抑郁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那里的大多数神经元会产生血清素,这是一种化学信使,能让百忧解(一种抗抑郁药)起作用。产生多巴胺的细胞约占该区域的25%,历史上很难单独研究它们,所以科学家们对它们的作用知之甚少。
马修斯推测,可能是实验过程中的其他环境因素引发了这些变化。她测试了仅仅把小鼠移到新的笼子里是否会改变它们的多巴胺神经元,结果不是。
马修斯和她的同事凯·泰(Kay Tye)意识到,这些脑细胞不是对药物产生反应,而是对隔离24小时产生反应。换句话说,也许这些神经元在传递孤独的体验。
像人类一样,小鼠是一种社交动物,通常喜欢集体生活。把一只小鼠从笼子里的同伴中分离出来,一旦禁闭结束,它就会花更多的时间与其他小鼠互动。
为了更好地理解背脊神经元在孤独中的作用,研究人员对多巴胺细胞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对某些波长的光作出反应,这是一种称为光遗传学的技术。然后,他们可以通过将细胞暴露在光线下,人为地刺激或使其沉默。
刺激多巴胺神经元似乎会让小鼠感觉不舒服。如果有选择,小鼠会积极地避免刺激,就像它们可能避免身体疼痛一样。此外,这些动物似乎进入了一种孤独的状态——它们表现得就像独自一人一样,花更多的时间和其他小鼠在一起。
孤独也会危害你的健康
孤独不仅让人感觉糟糕,还会对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隔离饲养的动物,从苍蝇到小鼠再到黑猩猩,寿命都较短。
单独监禁被认为是人类最严厉的刑事惩罚之一,它会增加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压力,削弱免疫系统,增加死亡的风险。
事实上,一些估计表明,即使在控制了年龄和抑郁等混杂因素的情况下,孤独也会增加近30%的死亡风险,与肥胖的风险相当。
科学家们希望,更好地了解孤独背后的神经回路,不仅有助于解释孤独存在的原因,而且最终能找到新的治疗方法。可以像我们治疗抑郁症那样调节大脑中的孤独。
孤独可能是一种有益的进化
卡奇奥波在十年前首次正式提出了孤独的进化理论。
强有力的支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对孤独感的敏感性是可遗传的,例如身高或患糖尿病的风险–大约50%的个人孤独感水平可以与他们的基因联系在一起。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种群在这一特性上的一些变化是有益的。
卡奇奥波说,一个社区的一些成员一个社区的某些成员“会因断开连接而感到痛苦,以至于他们愿意捍卫自己的村庄”,比如抗日;“其他人愿意出去探索,但希望仍然有足够的联系回来,分享他们的发现。”比如洋务运动。
小鼠也表现出这种变异。在马修斯的实验中,最占优势的小鼠(那些在与笼伴侣争战中获胜并优先获得食物和其他资源的小鼠)对刺激孤独神经元表现出最强烈的反应。
换句话说,地位最高的动物比地位最低的动物更热衷于寻找伙伴。这些小鼠也比排名较低的小鼠更渴望避免孤独神经元的刺激,这表明占优势的小鼠觉得这种刺激更不舒服。
相反,排名最低的小鼠似乎并不介意独处。也许他们喜欢与世隔绝,免受骚扰。
在大脑区域称为背缝核的神经元子集(以红色,绿色和黄色显示)产生一种称为多巴胺的化学信使。科学家认为,这些神经元会激发离体小鼠与他人共处时光。
泰伊和马修斯的发现表明,这些背缝核神经元有助于解决动物所具有的社交关系与所需水平之间的脱节。
如果把孤独想象成对冰淇淋的渴望——有些动物喜欢冰淇淋,有些则不喜欢。多巴胺神经元可以驱使爱吃冰淇淋的人去寻找甜点,但对其他人几乎没有影响。
“我们认为(中缝背核)神经元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小鼠的主观社会经验,并且只对那些先前重视社会关系的小鼠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而不是那些不重视社会关系的小鼠。”
不同的反应暗示了两种有趣的可能性:要么是神经网络决定社会等级,要么是社会等级影响这些神经元的连接方式。
也许有些动物天生就渴望社交。然后,这些动物会寻找其他动物,并变得具有攻击性,试图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最终达到最高地位。
另一种情况是,某些小鼠可能一开始就有好斗的个性,欺负他们组里的其他动物。结果,这些动物的大脑线路可能会发生改变,促使它们寻找其他动物来欺负它们。泰伊和马修斯正在计划更多的实验来区分这两种可能性。
总的来说,泰伊和马修斯的研究有助于重新定义孤独,将孤独从严重的绝望状态转变成一种编码在我们生物学中的激励力量。
“这项研究关注的不是孤独的令人厌恶的状态,而是社交在神经系统中是如何得到奖赏的,这样一来,孤独感由于缺乏奖赏而让人难受就可以得到理解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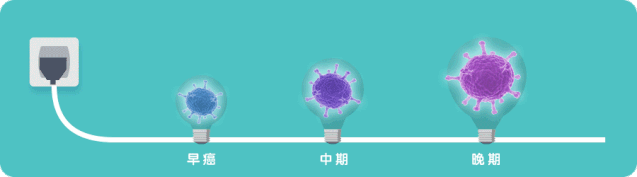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