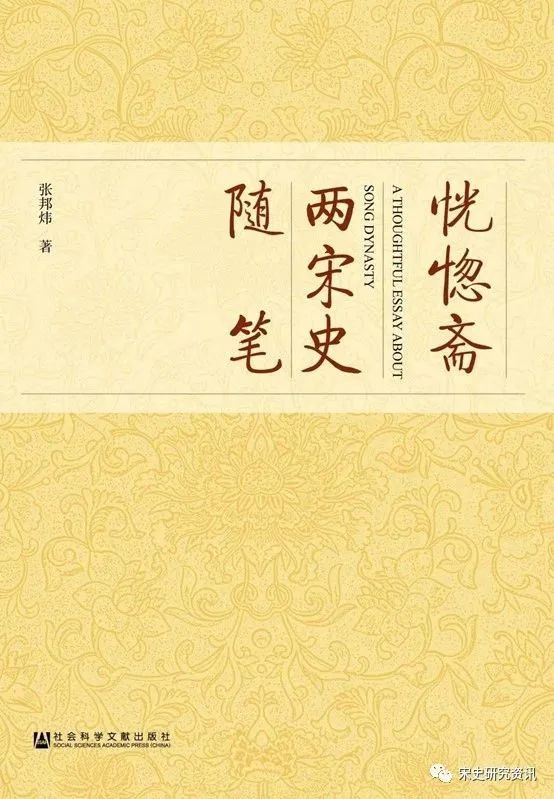
张邦炜著:《恍惚斋两宋史随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战时状态:南宋历史的大局
西汉、东汉在历史上合称两汉,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朝代。两宋与两汉不同,其最高统治集团具有延续性,实可视为一个朝代。然而北、南两宋相同之中有不同。依我之见,其最大差异在于:北宋大多数时段处于和平环境,而南宋则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制约并牵动南宋社会的诸多(不是所有)方面。要认清并理解南宋历史的若干(不是一切)实情,只怕都离不开政权南北对峙、处于战时状态这一大时局、大背景。
一、从和平发展到救亡图存
从总体上说,两宋历史经历了从“百年无事”到“天下多事”的演变。毋庸讳言,北宋战事不少。但宋太祖为巩固政权、拓展疆土而开展的一系列战争不是被动挨打,而是主动进取,战事进行得相当顺利。用宋人的话来说,即是:“所向皆捷,二十年中,边塞肃清。”[1]到开宝末年特别是景德初年以后,从全国范围来说,战争状态基本结束。难怪宋人多有北宋“百年无事”之说,说得最多、最夸张的当推北宋名儒自号“安乐先生”的邵雍。他一再声称:“一百年来号太平”,“天下太平无一事”[2],不厌其烦地强调:“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生来只惯见丰稔,老去未尝经乱离”,“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3]南宋人度正回顾北宋历史,讲得同样十分夸张:“承平百年,天下无事,四方无狗吠之警,中国有安靖之福。”[4]尽人皆知,北宋内忧外患不断,绝非“太平无事”。但就整体而言,北宋大体处于和平环境,虽然和平多半是用“岁币”换来的。宣和、靖康之际,北宋这座貌似金碧辉煌的大厦一触即溃,其根本原因固然是统治腐朽、社会溃烂,但在很大程度上亦可谓“大意失荆州”,最高统治集团忘记了“居安思危”的古训。南宋人楼钥说:“靖康艰难,事出仓猝,承平百年,衣冠如云,习于久安,不知所为。”[5]
与北宋不同,南宋重建于危急之中,一建立就不得不艰难地应对残酷的战争。正如当时人所说:“军兴以来,天下多事。”[6]南宋在东南站稳脚跟以后,宋金双方的力量对比渐渐趋于势均力敌,谁也很难攻灭谁。虽然如此,金方一旦主攻派得势,便举兵南下江浙,如兀术南下、完颜亮南下。宋方一旦主战派当政,就挥师北伐中原,如岳飞北伐、张浚北伐、开禧北伐、端平入洛。宋金战争尽管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停战时间远远长于开战时间,然而即使在停战期间,南宋也始终处于备战、迎战状态。难怪在和议达成之后的嘉定年间,袁燮仍说:“边境未宁,干戈未息,正国家多事之秋。”[7]
与从和平环境到战时状态的时局变换相适应,两宋的时代主题明显不同。如果说北宋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那么南宋则是救亡图存。毋须多说,下面两点即可见证。
一是人们对战争的态度不同。正因为北宋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士大夫一再老调重弹:“兵者凶器,战者危事。”熙宁元年(1068),元老重臣富弼建议宋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此言分明片面性极大,但在当时却受到普遍的肯定:“仁人之言,其利博哉!”[8]而南宋始终处于战时状态,韩世忠晚年“口不言兵”是对当政者软弱退让,屈膝求和的无声抗议。他发出了“自古英雄都是梦”[9]等悲愤之语。宋孝宗时,户部侍郎钱端礼迎合宰相汤思退,一再声称“兵者凶器”[10]则遭到广泛的讥评。可见南宋是个绝对不可“口不言兵”的时代。
二是社会关注焦点的转换。北宋统治集团总是围绕著如何变法图强而争执乃至打斗不休,其中以新旧党争最为著名。因此今人讲述北宋历史往往以三次改革即宋初强化中央集权、庆历新政、熙丰变法为线索。南宋人说:“国之大事,和与战而已。”[11]南宋统治集团总是围绕著和、战、守而展开争论乃至厮杀。因此今人讲述南宋历史常常以三个和议即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为线索。南宋虽然“更化”甚多,但所谓更化并不等于变法。诸如皇帝即位退位,太后垂帘卷帘,权臣上台下台,乃至更改年号,均称之为更化。正如当时人所说:“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12]即使是人们谈论较多的“嘉定更化”、“端平更化”,也未必可以视为变法,至少很难同北宋时期的庆历新政、熙丰变法相提并论。
二、“退缩东南,逼向海洋”
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是什么?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并称其意义在于“由大陆帝国向海洋帝国转型”[13]。这一概括固然不无一定道理,但显然欠周全,实有作些补充和修正之必要。其实,南宋经济的诸多方面(包括所谓“面向海洋”在内)均深受战时状态的制约。南宋经济以优先保障战争需要为主要目标,具有战时经济的某些特点,诸如税收增加,通货膨胀之类。以下数例即是其证。
一是逼向海洋。宋元时期是我国海外贸易发展的鼎盛阶段,受航海技术进步等因素驱动,南宋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在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之后,南宋朝廷依赖外贸、面向海洋的发展倾向表现得更为强烈。”[14]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发展倾向不是南宋朝廷的自觉选择,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则为了摆脱因军费开支巨大而造成的财政困境,南宋朝廷不得不发展海外贸易以拓展财源;再则因政治中心、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分立政权的阻隔,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难以畅通,不得不加紧建造海上陶瓷之路。一言以蔽之,战争迫使南宋“退缩东南”,战争逼迫南宋“面向海洋”。南宋帝王的意愿不是“退缩东南,面向海洋”,而是“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四方”,因而都城临安不称京城而称行在,帝王陵寝不叫陵墓而叫攒宫。然而他们由于腐败无能,空有恢复中原之想,并无北伐得胜之力。岂止南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改变了以农立国的传统经济格局,可称之为海洋帝国。所谓帝国者,其必备条件之一是疆域非常辽阔。至于南宋,只怕既非海洋帝国,也非大陆帝国。当然也不宜沿袭从前的思维定势,将其贬抑为“偏安王朝”。
二是片面(以不用“畸形”二字为宜)发展。依据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等著作的论述,南宋矿冶业低迷徘徊,农业生产突飞猛进;铸钱业勉强维持,兵器生产规模巨大;造船业领先世界,煤铁生产南不如北。凡此种种均表明:北宋经济的进步较为全面,而南宋经济的发展则比较片面。其原因何在,因素虽多,其中尤其重要的无疑是战争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和影响。矿冶业、铸钱业、煤铁生产的衰退分明是战争造成的恶果,兵器生产乃至造船业、制瓷业的发展也与战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由于盛产煤铁的北方地区的丧失,南宋“思石炭(即煤炭)之利而不可得”[15],煤铁生产长期低迷不振。研究者们常说宋代曾出现突飞猛进的“煤铁革命”和“农业革命”。即便确实如此,所谓“煤铁革命”是就北宋而言,而“农业革命”主要就南宋而论。消费刺激经济,技术促进生产。没有战争迫使偏好面食、会种小麦的北方民众的不断南迁,小麦生产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南宋东南地区的牧羊业较之先前有较大起色,其原因与此相似。好吃羊肉的北方民众大量南来,使得东南地区如平江府即苏州“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16]。市场需求旺盛推动南宋牧羊业发展提速,但为气候条件所制约,其发展水平始终不能同北方相比。
三是大发纸币。北宋纸币的印行和使用大体仅局限于四川地区,南宋则出现了不少地方性的纸币,如东南会子、湖会、淮交等。与面向海洋相同,大发纸币并非南宋统治者的自觉选择,而是不得已而被动为之。宋孝宗曾说:“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著。”[17]他唯恐纸币发行过多,引起物价猛涨,不许滥印纸币,以致当时纸币贵如黄金、重于现钱。后来果然不出宋孝宗所料,出现了嘉定纸币贬值、宋季纸币危机。然而即使对纸币持保守态度的宋孝宗也不可能停止印行纸币。原因何在?战争显然是个重要因素。宋金、宋元战争以及南北政权对峙造成有关资源短缺,以致钱币铸造量减少,只得印行纸币。此其一。其二在于军费开支巨大,朝廷不堪负荷,将印行纸币作为弥补财政缺口、摆脱财政困局的手段。绍兴年间朝廷在临安创行纸币,固然是适应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其目的在于“佐国用”[18]。
四是税赋太重。对此较早集中予以揭示的是清人赵翼。他指斥南宋统治者“取民无艺”,并以经总制钱、添酒钱、卖糟钱、牙税钱、头子钱、房钱、月桩钱、板帐钱、和买折帛钱等种种苛捐杂税为例,感叹:“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19]其实,当时不少最高统治者也心知肚明。如宋孝宗就公开承认:“税赋太重”,“横敛及民”。[20]赵翼将其原因归结为出于战争需要:“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21]宋孝宗当时就解释道:“朕意欲使天下尽蠲无名之赋,悉还祖宗之旧,以养兵之费,未能如朕志。”[22]加之统治者以作战需要为幌子,敲诈勒索百姓。民众理所当然地起而抗捐抗税,如淳熙年间广西发生李接事变。当时人朱熹说:“李接寇广西,出榜约‘不收民税十年’,故从叛者如云,称之为‘李王’。反谓官兵为贼。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23]然而百姓负担如此沉重,民变居然相对平和,并未星火燎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反抗行动。其主要原因显然在于女真贵族、蒙古贵族大敌当前,即从前人们常说的一句老话:“民族斗争转移了阶级斗争的视线。”
五是人身依附。上世纪60年代初,华山将直接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关系视为传统社会“最内部的秘密”、“隐蔽著的基础”。他对宋代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势作过相当深入的考察,认为两宋走著相反的方向,北宋逐步减轻,南宋“逐渐增强”。他说:“南宋灭亡前夕,江南农民已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走上了第二次农奴化的道路”。[24]如今看来,此说未必准确。朱熹的“主佃相须”论、陈傅良的“主客相资”论、熊克的“主客相依”论、袁采的“存恤佃客”论,这些大同小异的主张表明,南宋时期佃农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并不一定比北宋时期更低。南宋时期人身依附关系强烈的地域除边远落后地区(如夔州路)外,主要是战争前沿地区或战乱频仍地区。如绍兴年间淮南、荆湖等地所出现的身份低下的“随田佃客”,其原因在于“比经兵火,所以凋瘵”[25]。战乱使得势单力弱的孤立个人或家庭难以独立生存,不得不投靠有势力者。南宋的某些“山寨”类似于魏晋时期的“坞堡”,因战乱而形成,其内部人身依附关系强烈。这显然是战乱给南宋社会带来的一大恶果。治史者皆知,唐宋变革不开始于北宋,而开始于中唐前后。从人身依附关系变化的角度看,所谓“宋元变革”并不开始于元代,而开始于南宋,特别是其晚期。
三、“马上图治之时”
南宋处于战时状况影响著南宋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以对政治体制的影响更为显著。南宋人说:“今天下多事之际,乃人主马上图治之时。”[26]如果说北宋初期最高统治集团的治国方略是力图从“马上得天下”转换为“马下治天下”,从重武轻文转换为崇文抑武,那么南宋帝王则不得不“马上图治”。所谓“马上图治”,其含义与战时政治相近。人们不难发现在政治领域,南宋与北宋相比,有若干相当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大体都与南宋处于战时状况有关。下面略举四例。
一是权臣反复出现。南宋时期,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等权臣何以不断出现,较早予以专题考察者当推香港学者林天蔚。他的长篇论文《宋代权相形成之分析》[27],其重点在于探讨“制度性根源”,诸如:独相者多;继世为相及再相者众;加“平章军国事”衔,位于宰相之上;兼枢密使;兼制国用使。此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只字未曾提及“制度性根源”背后的时局性动因。台湾学者林瑞翰《宋代官制探微》一文为其论题所限,对此虽语焉不详,但触及到问题的要害。他说:“南渡以后,兵兴则令宰相兼知枢密,又重其财用之权。”“自开禧(北伐)以后,宰相复总民政、兵政、财政,三权为一而相权复振。”[28]南宋“相权复振”、权臣叠现,其深层原因分明在于战时状况,亟需军政协调、快速应对,民政、兵政、财政三权分割无法适应作战需要。
二是武将权势增大。“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29]这句古人言被南宋人一再加以引用。如所周知,南宋初年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诸大将扩军自雄,政治上暴贵、经济上暴富,公然号称某家军。朝廷因此有所谓“第二次削兵权”之举,但武将势力膨胀的问题并未也不可能解决。“四世专蜀兵”[30]的吴氏武将集团便是一个突出的事例。吴玠、吴璘、吴挺、吴曦相继执掌四川兵权,被士大夫指斥为:“吴氏世袭兵柄,号为吴家军,不知有朝廷。”[31]南宋武将出任地方行政长官的事例远远多于北宋。如余玠并非科举出身,一武职人员而已,竟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重庆知府、四川总领、夔州路转运使,这在北宋和平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南宋武将势力明显增大,原因无疑在于战争。出于作战需要,朝廷对武将不得不放权。与北宋不同,南宋再无李宪、童贯、谭稹、梁方平等巨珰统率大军出征的现象再现。南宋朝廷不用宦官领兵,废止宦官监军,即可视为一条放权措施。同时又力图坚守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放权,武将尾大不掉;削权,又有“自毁长城”之虞。南宋朝廷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正如当时人所说:“上无驭将之术,而将有中制之嫌。”[32]其结果是文臣、武将双方均颇为不满,军队的战斗力也无法切实加强。
三是言官力量削减。所谓言官主要是台谏官,即御史台和谏院官员。已故旅美学者刘子健明确指出,与北宋相比,“南宋言官始终没有力量”[33]。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这一变化“决非单纯的职官制度的变化,而是当时政治局势的缩影。”[34]他所说的政治时局专指权相政治。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其深层原因只怕也与战时状态和主战、主和之争相关。如宋高宗主和,便偏袒其同调秦桧。主战言官如若敢于弹劾秦桧,其结局只能是被罢免。宋孝宗主战,则庇护其同道张浚。他一再表示:“朕依魏公(即张浚)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35]宋孝宗甚至指责大胆陈词的言官是“卖直”[36],即以刚直敢言而沽名钓誉。少除乃至不除台谏官是南宋帝王控制言路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处于战时状态、出于战争需要又为他们提供了口实。《宋史·职官志》序称:“当多事时,诸部或长贰不并置,或并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户部不省不并。”[37]当时朝廷有相当充足的理由,对台谏官的员额予以削减。言官素称“耳目之臣”,帝王不倚重言官,势必以佞幸为耳目乃至心腹。所谓佞幸,指因谄媚而深受帝王宠幸之人。帝王宠信佞幸,实乃传统政治的一大痼疾。相比之下,南宋更为突出。
四是从严掌控舆论。压制言官只是南宋朝廷严格控制言路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举措还有禁小报、禁私史、兴文字狱等等。宋高宗时,文字狱频发。赵翼《廿二史札记》对此有简要概述:“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狱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所谓“忌讳”,分明是指对金主战。秦桧“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38]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更加严厉地施行私书之禁。史载:“其秋,商人载十六车私书,持子复(即熊克)《中兴小历》、《九朝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即今江苏盱眙)以闻,遂命诸道帅、宪司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39]总之,南宋统治者从严控制舆论,其主要理由无非是战时状态必需采用非常手段。他们强调:“议论不定则规模不立,规模不立而国家之势危矣。”[40]
综上所述,北、南两宋因时代背景不同,以致时代主题不同,时代特征有别。在不少问题上,北、南两宋都不能一概而论。北宋史的研究与南宋史的研究是不能相互取代的。最后需要说明,笔者绝无低估、矮化南宋之意。南宋时期成就辉煌,对后世的影响大于北宋。学界多有论述,本人并无异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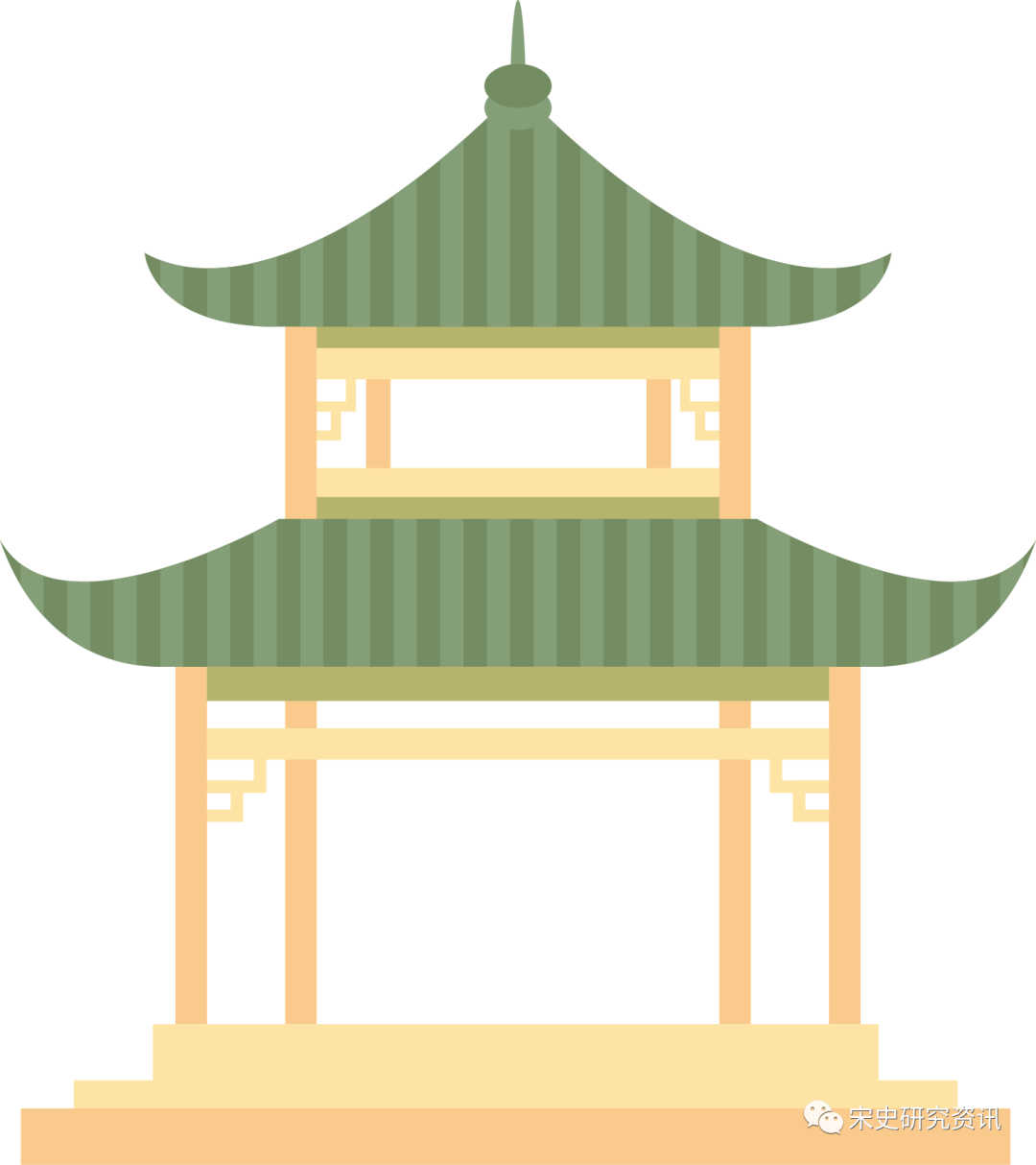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9月9日第5版《光明论坛》。
注 释
[1]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35《御边》“宋孝宗时蔡戡又论守边奏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48页。
[2]邵雍:《伊川击壤集》卷5《秋日登崇德阁二首》、卷17《观棋小吟》,陈明点校,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46、230页。
[3]《伊川击壤集》卷10《插花吟》、卷15《观盛化吟》、卷19《病亟吟》,第126、194、259页。
[4]度正:《性善堂稿》卷6《条奏便民五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楼钥:《攻媿集》卷49《王节愍公(伦)覆谥议》,《丛书集成初编》本。
[6]脱脱等:《宋史》卷161《职官志一·中书省》,中华书局1977年,第3787页。
[7]《历代名臣奏议》卷162《建官》“嘉定九年袁燮上奏曰”,第2124页。
[8]《宋史》卷313《富弼传》,第10255、10264页。
[9]周密:《齐东野语》卷19《清凉居士词》,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361页。
[10]《宋史》卷385《钱端礼传》,第11830页。
[11]《历代名臣奏议》卷234《征伐》“宋光宗时蔡戡论和战奏曰”,第3088页。
[12]《历代名臣奏议》卷309《灾祥》“嘉定九年著作郎赵崇鼎因闵雨上奏曰”,第4009页。
[13]葛金芳:《宋代经济史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7-66页。
[14]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15]庄绰:《鸡肋编》卷中,萧鲁阳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77页。
[16]洪迈:《夷坚志》丁志卷17《三鸦镇》,中华书局1981年,何卓点校,第682-683页。
[17]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14《官会折阅》,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84-585页。
[18]马端临:《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会子》,中华书局1986年,第98页。
[1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南宋取民无艺》中华书局1963年,第490-492页。
[20]佚名:《宋史全文》卷25上乾道五年九月丙寅,李之亮校点,黑龙江出版社2005年,第1714页。
[21]《廿二史札记》卷25《南宋取民无艺》,第490页。
[22]《宋史全文》卷25上乾道四年二月,第1701页。
[2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3《本朝七·盗贼》,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第3187页。
[24]华山:《再论宋代客户的身分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4月12日《史学》。收入华山:《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第49-54页。
[25]王之道:《相山集》卷22《乞止取佃客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丁未,中华书局1988年,第458页。
[27]林天蔚:《宋代权相形成之分析》,《思与言杂志》第10卷第5期,1973年1月;收入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8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6年,第141-170页。
[28]林瑞翰:《宋代官制探微》,《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2期;收入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9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7年,第221-222页。
[29]熊克:《中兴小纪》卷13绍兴二年十月庚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宋史》卷392《赵汝愚传》,第11982页。
[31]《宋史》卷39l《留正传》,第11974页。
[32]《宋史》卷《兵志一·禁军上》,4750页。
[33]刘子健;《南宋君主和言官》,《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34]刁忠民:《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第77页。
[35]《宋史》卷361《张浚传》,第11308-11310页。
[36]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5《隆兴台谏》,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125页。
[37]《宋史》卷161《职官志一》,第3771页。
[38]《廿二史札记》卷26《秦桧文字之祸》,第514-516页。
[39]《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嘉泰禁私史》,第149-150页。
[40]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綦崇礼》,《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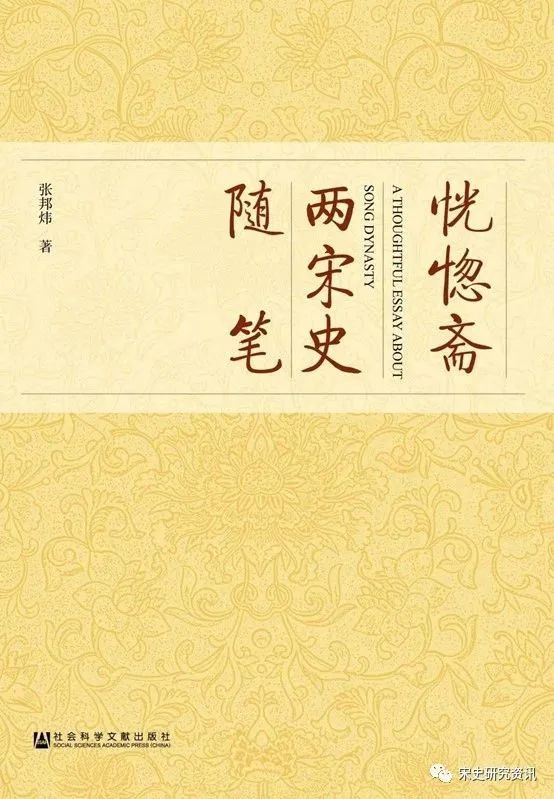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