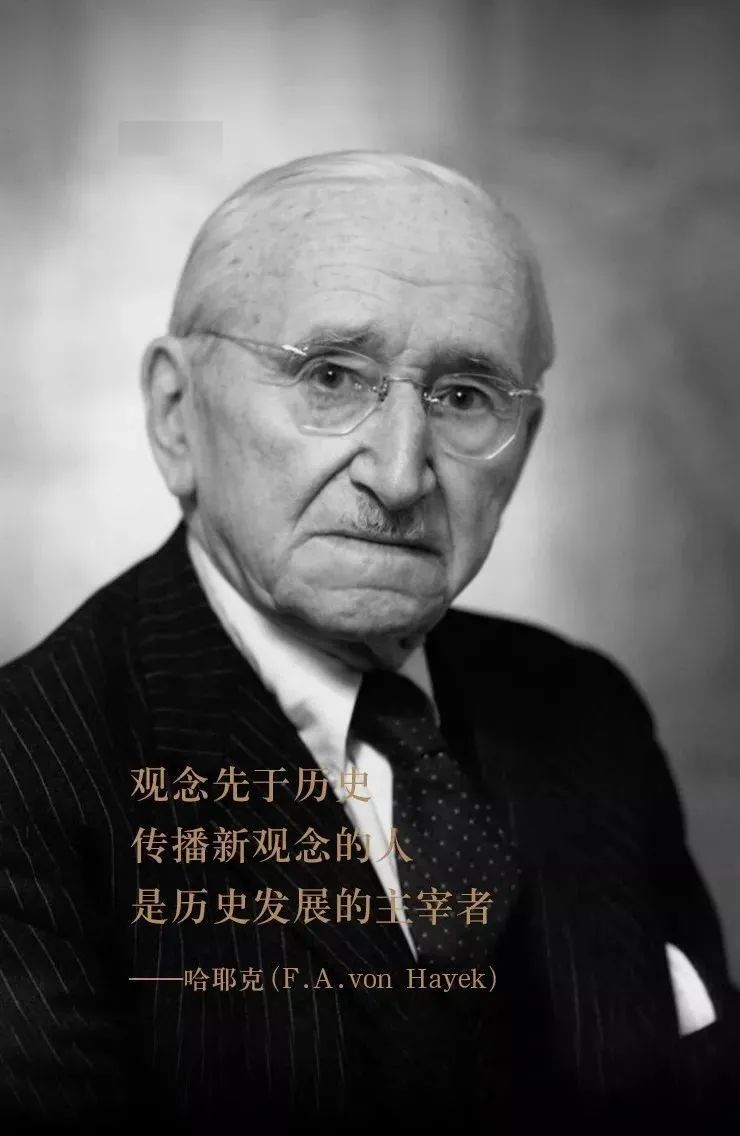
在1967年的一篇论文中,著名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探讨了“社会的”概念的政治意义及其起源。在他看来,直到19世纪初期,“社会”主要还是一个由道德主导的领域,指涉的乃是一个人置身于其间的具体且得到承认的情势,且不论道德行为的后果如何。[1]
这差不多是说,时人进行社会行动时,他们只是在适应这个社会,努力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保行动过程本身顺理成章。他们所依据的道德,本身只是一套实践伦理或智慧,一套日常生活中理智行动的过程性规则。他们不是根据最终的幸福或最高的善理念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而是基于“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2]。或者说,只求行为本身“明智”[3]。
这里所说的“求真”,也就是合乎逻各斯,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那种主观符合客观。而且这里的逻各斯是破碎的、片段的、零散的、不系统的、模糊的。在这里,如果劳动所得有结余,就渴望交易。挣来的钱,总想能自由支配。虽然这么强调自主性,很可能产生新的贫富分化,但只是要求我们不要眼红别人有钱,要自强不息。这个就叫明智,就叫求真,就叫合乎逻各斯。它要求我们根据生活中那些自明、但又不甚系统、没有明确的实质性目标的道德规则行动。

根据哈耶克的考证,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现代民主及普选时代到来之际,人们开始提醒上层阶级,他们对“下层社会”(underworld)或那些“人数众多且最为贫穷”的人的命运负有责任。自此,“社会的”渐渐具有了新的含义,取代了“道德的”(moral)甚或“好的”(good)两个术语。[4]
其结果,就是社会本身获得了一种独立人格。它不再是个人道德实践的自然结果,而是个人实践最终必须与之契合的道义本身。
新的社会情势由于把“社会的”道德化甚至人格化,强调行动的间接甚至非常间接的后果,势必导致对社会的理性控制。也势必摧毁社会自身赖以为凭的基础——对规则和日常伦理行为的尊重,以及它原本想强化的个人责任。最终势必导致正义概念向它并不适用的诸多领域扩展,对真正的政治原则如自由、独立的阻碍,远远大于其促进作用。[5]

对我们而言,公共性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特征。但确实需要警惕一种极端的倾向,就是一切都要服从一种最终的善,服从某种分配正义,将平均主义或大锅饭当作最高的社会理想。一句话,社会本身不能有太强的“爹味”,始终把个体的自由独立作为一切的前提。
但在我们见过的极端情况下,钱不能由个人自由支配,个人自身也不能由自我支配。一切都要服从大局,包括服从社会对个人本身设置的发展宏图。
事实也是这样:一旦允许钱生钱,允许自由消费,包括允许教育中的自由消费,那种想望中的平等秩序,也确实就没法维系。所以不但要“剥夺剥夺者”,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铲除一切对财产的私人占有,包括铲除对个人命运的自我支配,这些东西被认为必定会导致“剥削”关系。
这种地方不讲法律和证据,道义本身就是最高的法,超出他人想象的财产本身就是原罪,凭资本获利本身就是剥削,学识或贫富差距本身就是非法甚至违法的证据。
这样限制财产权,个人财富与知识还有鬼用?最后都只能献给国家,由国家来统筹知识、财富与人的生产。个人则开始仰人鼻息,等着国家分钱分物,压抑一切自觉或自发的活动。道德因此不再成为一种自愿活动,而成了一种义务,一种根据一项统一且有序的正义蓝图去重建社会的集体努力。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占支配地位的教育纲领,就是一种与此类似的社会本位论立场。它不是在我们尊重个人自主的基础上调整社会行动的某些结构,以落实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而是从根本上致力于一种高居于个人之上的“爹味社会”的建构,强调以社会本身的需要作为教育的最终依据,要求从这样一种明确结果反推行为,并因此完全排斥个人的权利、意愿与自主性。
新民主主义时期,“逻各斯”或理智行动的过程性规则还是主导性的行动原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对结果的强调开始支配行动过程。教育活动的新纲领,主要出于阶级斗争的考虑,而不是基于个人自由发展的需要,或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立场。自此,正常的学校教育秩序开始受到冲击,田间地头或工厂车间开始变成教育教学的“主战场”。
“拨乱反正”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被废止。“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6],开始成为主导性的教育纲领。由于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某种意义上的心智本位论,开始重新成为学校教育的主导立场。1992年邓小平(1904-1997)“南巡讲话”之后,“对最终目标及相关任务分解与分配过程的强调”,最终“让位于对一系列过程中的基本行动原则的推崇”。[7]但社会本位论的遗迹还在,而且经常反复。

杜威曾经说:“凡是一种冲突,不是社会与个人、国家与制度(的冲突),实在是人群(Group)与人群的冲突。”[8]意思是说,不要把社会与个人对立起来,不要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冲突,说成个人与社会乃至国家的冲突。更确切地说,不要以国家、社会或人民的名义,对自己的政治对手进行道德绑架。
但社会本位论者显然不愿放弃对社会本身及其他相关观念的道德化或人格化解释,因为他们不愿失去“社会”这一便利的道德武器,也害怕自己笼罩在各种政治行动之上的正义光环破灭。
这样建构起来的社会,当然不是个人能够自主参与的公共领域,只能是一种高踞于个人之上的政治化的“总体”人格。马克思所想往的那种作为“个人”而不是“阶级的成员”的自由人的联合体[9],在这里完全看不到踪影。受到排斥或压制的,不但有人的天性,人的权利与意愿,还有各种公民团体,以及各种民间自发教育行动。
社会本位论中的“社会”概念是非常奇特的。
在涂尔干那里,现代社会基于“有机团结”,这种有机团结是以个性化、行业自主和分工协作为基础的。
但在社会本位论者那里,所有的机械生产、分工协作、个人独立、行业自治、市场运作,都被说成是机械的。现代社会好像失去了灵魂,冷冰冰的机械生产取代了一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市场交换破坏了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人们似乎再也回不到温情脉脉的岁月,再也产生不了同心同德的感觉,再也体验不到集体欢腾的激情。
社会本位论想重新唤起集体意识,形成一种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天下一家的感觉,而且是在现代社会重新形成这种意识和感觉。而对涂尔干来说,所有这些都属于那已经远去的机械团结的社会,现代社会在根本上以个人为基础。[10]
由此看来,涂尔干虽然到处强调,“不管表面上如何,无论何处,教育首先都会满足社会的需求”[11],但他不但不是社会本位论者,而且刚好站在社会本位论的对立面。

推行这种社会本位论,人们会坚持向学生输入什么知识?
首先,这种知识肯定不会让学生自己选择,只能由“社会”或官方来组织选择。
其次,除了那些意识形态学科,科学知识也能忝列其间。不过,基于对各种自发性根深蒂固的顾忌,肯定不会鼓励对知识的自由探索。因此,理工科中的那些基础学科和专业,也有可能被放弃。教育中盛行的,主要将是技术学科。像我们教育学,“文革”中就只能成为各种方针政策和领袖语录的汇编。而心理学和社会学,干脆直接被宣布成“伪科学”。
最后,所有这些知识必定需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因而最终盛行的只能是一些政治知识。这倒不是说,在这样一种倡导社会本位的教育体系中,物理学这门学科本身就是政治学科。或者说,物理学的原理本身会直接因此蜕变为意识形态。而是说,它怎么进入课程、在课程中居于什么地位、服务于什么样的教育目的、以何种方式影响我们的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都必须满足“政治正确”的要求。

这种教育经常鼓励创新,因为它觉得自己已经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理所当然能够焕发全新活力。它也经常自认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创新实践,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种教育氛围中,科学家、军人、好人好事也都经常受到推崇,也经常在创新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但社会本位论体系的最大问题是将社会本身预设为最高的神,要求一切都服从那个统一的社会,把它的要求或“启示”看成一切的根源。在这里,具有最高的价值的是社会本身的需要,而不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声音,不是基于这种声音的日常伦理实践,不是这种实践之中的明智,也不是这种明智所依赖的那套不太明确、零零碎碎的规则,以及建立在这一系列基础之上的自由探索。
这样将个人从对逻各斯的追求中抽离出来,要求他们按照正义,按照最高善,按照一整套系统的设计行动,使“戏子”也完全服从于集体意志,导致整个社会迅速滑向一个封闭体系,从根基上破坏创新行动必需的个人自由。自此,不但没了思想自由,也没了自由的市场。首先是基础研究失势,很快,技术创新也蜕变成一种群众性的技术竞赛。

在这种氛围中,甚至大学生谈恋爱,也必定变得不合法。
因为谈恋爱就意味着政治上不积极,相当于上甲课干乙事,端着公家的碗干着私人的活。就是不响应国家的号召,把精力和时间花在个人感情上,追求低级趣味。不是一心一意干革命,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偷偷地种自己的自留地。
当然还是有一些人会顶风作案,结果就是各种处分,失去评优评先的机会。
为什么要这样把两性爱恋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因为一旦爱成为生活的常态,我们那种内在的本源性的东西就会释放,就会要求展开一场无穷无尽的探险。
这样,就像费孝通所说,“非但毫无成就,而且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使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12]
事实上,在全国一盘棋的条件下,高校都不准谈恋爱。毕业分配的时候,也是发现一对拆一对。最后导致两地分居,有的调动十几年都调不到一处。为什么这么不通人情?就因为它挑战各种既定秩序,破坏国家整体布局,导致各种自发势力蔓延。

“社会”概念本来有多重含义。它可能是外在于个人的物质生产条件,可能是压迫性的政治经济制度,可能是与其他个人广泛对立的统治阶级或集团。但它也可能是涂尔干视野中个人对之心悦诚服的道德领域或精神实体,还可能是与个人相辅相成的公民社会。
如果这样宽泛地使用“社会”概念,社会本位论不可能是一种单一的理论,必定是许多可能相互冲突的理论的集合。其中既可能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这样一种排他性的社会本位论,也可能包括我们后面要说的杜威的主张,甚至包括前面说的心智本位论。
但社会本位论中的“社会”概念,尽管在政治光谱上有不同表现,显然还是有基本的定位。这样的社会充满爹味,一切都要基于政治道义,而不是基于逻各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人如果没有进行任何物质生产,还试图激发自主活动,把各种政策实践作为研究与反思的对象,差不多就像苏格拉底,亵渎神灵或蛊惑青年了。
只要最终的目标已经预定,任何思想火花就都会带来动荡,人文社会学科就只能沦为宣传机器。对它的蔑视,最终都会顺理成章。

[1] [英]哈耶克:《什么是“社会的”?——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见[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3页。
[3]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37、41~42、167~169、172~179、186~190页。
[4] [英]哈耶克:《什么是“社会的”?——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见[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166页。
[5] [英]哈耶克:《什么是“社会的”?——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见[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174页。
[6]这是1983年国庆邓小平为景山学校的题词。
[7]康永久:《新时代教育学研究的根本方向与立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2019年10月15日08:04;“铿铿金声读书会”公众号,2020年9月18日。
[8] [美]约翰·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见[美]约翰·杜威著,胡适口译:《杜威五大讲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9]参见[德]卡·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202页。
[10] [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3~186页。
[11] [法]爱弥尔·涂尔干著,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12]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图片源自网络,仅供学术交流
看完请点击右下角“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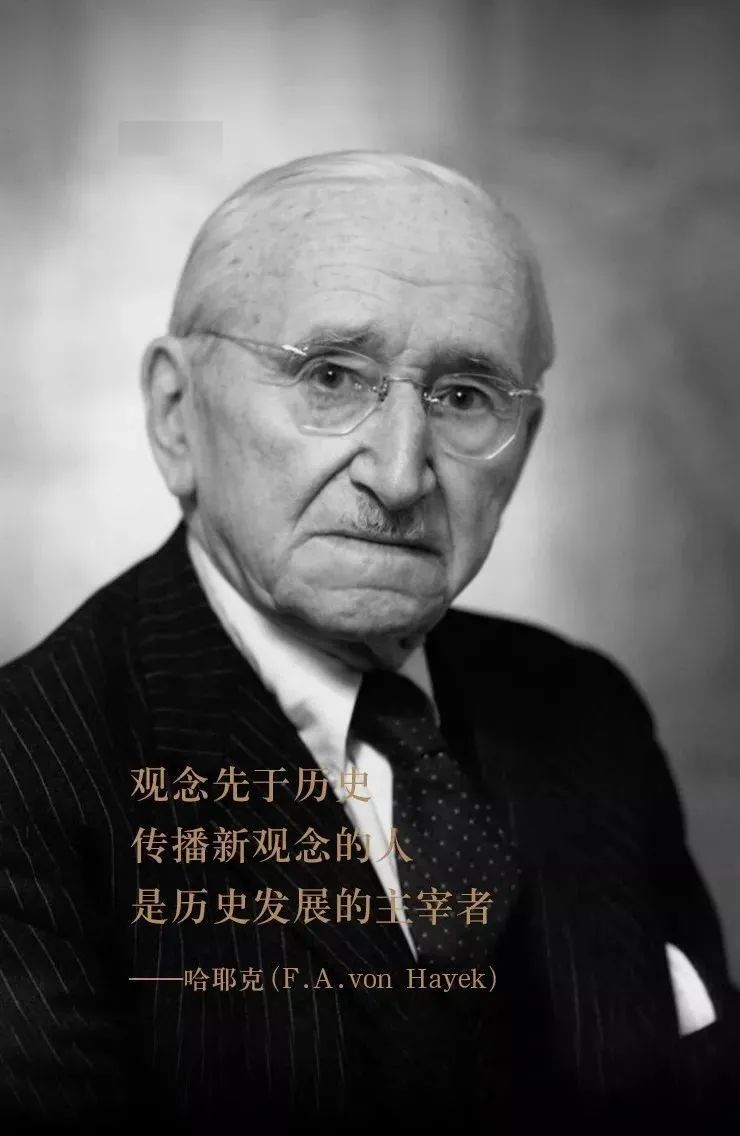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