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人际关系织成了一张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或血缘、或地缘、或姻亲,人与人多多少少会有蛛丝马迹的关联,要么沾亲带故,要么非亲即故,因彼此熟悉,就彼此关照,大家可以通过“熟人”织就的网络,沟通关系、打通关节、解困排忧,同时也可以寻找捷径、超越规则、营私舞弊,甚至徇情枉法。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难办的事,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亲朋好友可以打通“关系”,这样的思维“惯性”几乎贯穿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子女入托入学、求职就业,甚至到求医看病等等,有“熟人”不仅可以优先,还可以优惠。有人把“熟人社会”也称为“关系社会”、“后门社会”,很多习而不察的“潜规则”,便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人们一方面痛恨各种关系带来的权力寻租,一方面又渴求,甚至“窃喜”自己也拥有各种各样的“熟人”脉络。究其根源,“熟人社会”的运行规则是“人治”超越“法治”,人们办事多凭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的深浅程度,因“熟悉”而模糊了责、权、利的界线,在公共事务中公权私用、任人唯亲、特权寻租、徇私舞弊也就见怪不怪。在现实生活中,越封闭的区域“熟人社会”的特征越为明显。比如在一个县城,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互“认识”,遇到“麻烦”,总能拐弯抹角地找到“关系”,同乡、同学、同事、战友、邻居、姻亲,或者是一起开过会、吃过饭、散过步,抬头不见低头见,于是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超越规则、办成事情也就顺理成章。
“熟人社会”的运行规则大大弱化了“法治”的功能,它以“关系”代替“规则”,以“熟人”的情面代替了法律的威严,使得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在“人情”的左右中常常倾斜。特别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将亲情、交情、友情这些温情脉脉的手段移植到公共权力的行使中来,淡化了竞争激励,引发了腐败泛滥,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败坏。因此,“熟人社会”的过分发育,是对社会秩序的瓦解、市场竞争的摧残、法制社会的腐蚀。
正因为传统的“熟人社会”存在种种弊端,在当下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很多专家学者呼吁,要尽快实现“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何谓“陌生人社会”?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运行规则之上,人们相互间的很多关系被“货币化”,淡漠了“熟人”间关系的作用,强化了社会分工的职能作用,我们在慢慢地进入“陌生人社会”。
随着“熟人社会”的消褪,我们常常会有几分怅惘,回忆与怀念“熟人社会”的那种邻里温情,焦虑“陌生人社会”的互不信任。诸如家长会叮嘱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大街上陌生人倒下不要扶”;幼儿园的老师会教育孩子:“千万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银行会提示:“不要给陌生人汇款”;社区会提醒:“陌生人搭讪轻易别理睬”等等。“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冷落了人间真情,遗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大家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另一方面又不断抱怨人性的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人人自危,提醒亲朋好友少管闲事。这样一种纠结的社会心态提示我们,当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候,我们必须全方位地构建“法治社会”。
一个国家的法制,是这个国家道德风尚发展方向的强制性保障,也是规范和引导这个国家公民的社会道德基础,要瓦解盘根错节的“熟人社会”,最重要的措施是在整个社会营造浓厚的法制文化,培育全社会的规则意识,为“法治”开辟越来越多的空间,让人们适应“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制化生存,让有效运行的社会规则排斥人情纠葛、人情垄断、徇私舞弊,摒弃拉关系、走后门等繁琐环节,给整个社会提供法治保障,让人们都在法治的环境下工作与生活,消除人们羡慕、寻求、构建“熟人社会“的惯性心理。
当然,“法治社会”不是简单的“陌生人社会”,它并不必然伴随冷漠无情,更不排斥人间真情。如果说“熟人社会”人们更多地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通过关系互帮互助,而“法治社会”则凭借“法制”的中立、公正、权威承载社会成员之间最广泛的信任,让人人生活的幸福、安全而有尊严。我们要既发挥传统文化中德性自律的优势,又要积极推进依法行事的自觉,真正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科学文明的发展。
作者单位: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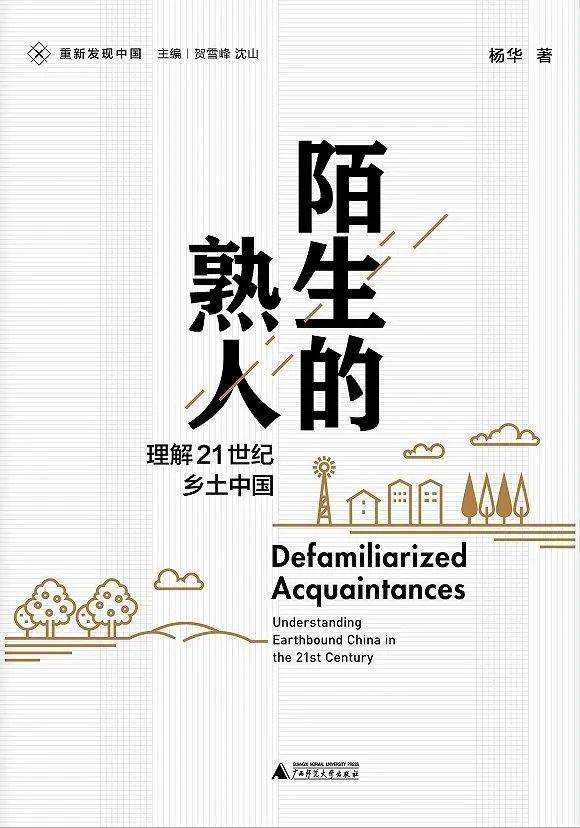
![[翟学伟]乡土中国的变迁——也说“无主体熟人社会” [翟学伟]乡土中国的变迁——也说“无主体熟人社会”](https://miehuo119.cn/uploadfile/thumb/20240626/1719338726946_0.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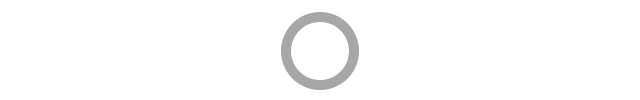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