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和柳宗元有着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他们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情无不令人赞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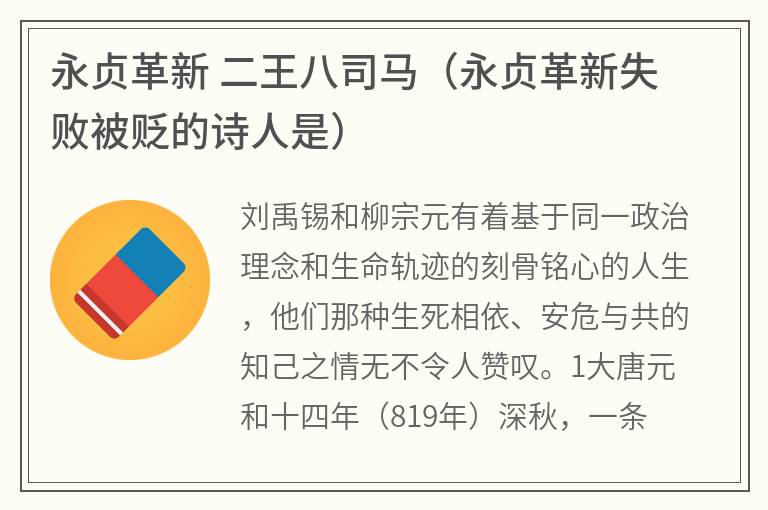
永贞革新二王八司马(永贞革新失败被贬的诗人是)
1
大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深秋,一条北归的小船停泊在衡阳城外湘江边的码头,船头,前连州刺史刘禹锡正伫立沉思,脑海里不断闪出二十年来的种种。其时,月光被乌云淹没,江水冲击着木桩,远处的城楼上传来几点鼓声,清寒,凄冷。
四年前,也在这个码头,他曾与良友在另一条船上,彻夜畅谈。次日,他和良友拱手告别。刘禹锡舍舟登岸,水路转陆路,前往连州。而良友,将继续溯江而上,前往陌生的柳州。尽管前途迷茫,但道别时,他们仍然互相鼓励,尽量不向对方倾诉内心悲苦,向其传递过多的负能量,只盼日后能把欢聚畅饮。
可湘江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如果不是命运地捉弄,他们或许可以在帝都长安干着各自未竟的事业,他们是那么的志同道合,安危与共,可这一切都像一场梦,永远留在了昨天。
刘禹锡的良友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至交——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
就在刘禹锡神伤之际,一封来自柳州的书信让他惊恐而难以自制。他接到了柳宗元去世的讣告。原来,柳宗元已在十余天前病逝。
刘禹锡本来此行是扶母亲灵柩回乡安葬,不曾想又得此噩耗,刘禹锡凄极悲痛。事后,他为柳宗元写了祭文,深沉的哀思溢于言表。
忽承讣书,惊号大哭,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泪并落,魂魄震越。伸纸穷竟,得君遗书。绝弦之音,凄疮彻骨……
进入生命最后时光的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已四年有余,由于不适应南方潮湿暑热,柳宗元疾病缠身。弥留之际,柳宗元强撑着身体写了一生最沉重的文字——遗书,他把身后事托付给一生挚友刘禹锡。
十余天后,刘禹锡收到了柳宗元来信。刘禹锡捧信大哭,失此良友的心情绝不亚于丧母之痛。然而地球不会因谁的离去而停止自转,万物仍会不断新陈交替。平复好心情,刘禹锡继续北上,他要回乡安葬老母。
就在北归的途中,刘禹锡写了第一首纪念柳宗元的悼亡诗: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
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循故道,帆灭如流电。
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刘禹锡《重至衡阳伤柳仪曹》
当年两人分别的情景清晰地在刘禹锡脑海中重映,而如今却只剩他一人,不知有多少哀痛,多少感伤。
2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初次相识是在科举场上。二人同在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是年,刘禹锡22岁,柳宗元21岁,怀着同样的抱负让两颗闪耀的新星相逢。
改变二人命运的是一次力图振兴大唐的改革——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如黑夜里的火柴,短暂地照亮了大唐的夜空。刘禹锡和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之初便被擢升,成为实际掌权派,一时风光无限。但这场历时仅百余天的改革注定二人的春风得意是短暂的。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刘禹锡和柳宗元人生的高光时刻灿烂如流星,衰落更似流星。以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推翻了改革,唐顺宗被逼逊位,宪宗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永贞革新的实力派——二王八司马或被杀或遭贬谪。
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州)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
人生就是这么变幻无常,数月前还是权倾一时的改革重臣,短短数月就成了罪人,二人在政治上也再无出头之日。
唐宪宗曾下诏说,即使有大赦,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也永不在量移之限。不像韩愈(点击阅读)那样,被贬潮州,只要上表认错服软,皇帝还是会心软,政治上不至于走入死路。可宪宗对刘柳等人却是永不量移,至少在宪宗这朝,他们再无翻身可能。
后来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二人如何请朝中大臣向当权者求情,也无济于事,并不能改变左迁的事实。
刘、柳性格迥异,柳宗元深沉内敛,刘禹锡狂放外向,因此面对贬谪,二人心境天差地别。二人这一时期的诗句便能很好说明这一点。面对贬谪,刘禹锡的心态是: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秋词》
刘禹锡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赞颂了秋天的美好,其奋发进取的豪情和乐观通达的情怀显而易见。
而柳宗元的状态是: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柳宗元全然无刘禹锡那般豪情万丈,其孤寂的心态是不言而喻的。
即便如此,这并不影响二人将对方视为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知音。
江湖路远,道阻且长,这一贬,就是十年!
3
十年后,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接到朝廷诏令,让他们立即返回长安。二人相约结伴而行,这次回京走的是十年前贬谪南下的旧路,十年前的南行是一步沉似一步,十年后的北归则是一步轻似一步。山川依旧,故人今在,这是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
刘柳经过十年漫长的贬滴生涯后,终于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可这光明却像闪电一般,转眼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二人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味,便又重新坠入暗夜之中,希望破灭了!
更为确切地说,刘禹锡和柳宗元回到长安不满两月,又被逐出京城,这次是更加遥远的南方。
说起来,这都是刘禹锡的一首小诗惹的祸。
话说刘禹锡回到长安后,朝廷并没有安排职位,十分清闲,于是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便趁此机会重游京都。
在长安朱雀大街旁有一座玄都观,这是长安的热门景点,以清幽雅致著称。道士在观内种植了许多桃树,每值初春花开时节,宛若一片红霞,蔚为壮观,刘禹锡等人相约同游了玄都观,之后他就写了这首诗:
紫阳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花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玄都观桃花》
这首诗在长安城不胫而走,确有讥讽权贵之意。很快此诗呈送到宪宗御前,宪宗本就对“二王八司马”不满,加之又被人添油加醋地解读一番,宪宗大怒。
再贬!刘禹锡被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柳宗元被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
柳宗元很懵,他什么也没干,就被贬了。患难见真情,柳宗元并没有与刘禹锡划清界线,撇清关系,他反而向世人展现了什么叫好朋友。
圣旨下达后,柳宗元连夜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折。
他不是为自己喊冤,他是为一个老人担忧,那个老人便是刘禹锡年老体弱的母亲。
这时刘禹锡的母亲已八十多岁,在唐朝,播州是极其荒凉的穷苦之地,让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跋山涉水数千里去往此地,无异于要她老命。若将其留在京城,一则无人奉养,二则实同死别!
这时的柳宗元毅然表现出与刘禹锡亲兄弟般的深厚情谊!他上奏章向宪宗求情:
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执友,何忍见其若是?
柳宗元还提出,他希望唐宪宗同意他和刘禹锡对调,他去播州,刘禹锡去条件相对较好的柳州。
唐宪宗读罢奏折,大为生气,认为柳宗元在讨价还价。幸好大臣裴度站出来求情。于是,刘禹锡改任连州刺史。连州在今天的广东,路程虽远,但水路较多,条件比播州好。
几天后,柳宗元与刘禹锡一同离开了长安。而从这以后,柳宗元再也没有回来过。
4
在连州的刘禹锡除了和柳宗元常通书信外,还自学医术,得知好兄弟柳宗元病了,要给他治病,他给了柳宗元几个药方,效果竟还不错。
是故,刘禹锡对柳宗元走得如此迅速,既悲痛又意外。
柳宗元去世的时候才47岁,英年早逝的他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儿女幼小,无人照顾;二是他的诗文未曾刊印,担心散佚。在他心中,能帮助他的只有刘禹锡。
好友的遗嘱,刘禹锡义不容辞。他把柳宗元的儿子视若己出,抚养成人。此外,刘禹锡又费时五年,收集、整理、编辑柳宗元留下的诗文,亲自作序并刊行于世。
如果说柳宗元因英年早逝而没能迎来人生春天的话,那么,比他多活了23年的刘禹锡在多年贬谪后终于苦尽甘来。
晚年刘禹锡闲居洛阳,过着优雅自在的诗酒生活。他对化作尘土的亡友一直铭记在心。去世前夕,他仍深情地回忆起与柳宗元共事的情景。对他和柳宗元来说,那都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