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步还是反动:历史进步观背后的曹操评价
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曹操进行重新评价的学术风潮中,是非善恶的评价虽占主流,但不能说就没有新史料和新观念的引入。史料的更新往往源于偶然的发现,外来观念的影响则往往是潜移默化的。从曹操研究论著中可以清晰窥视到的外来观念,最重要的是历史进步观。这一观念被引入并逐渐主导了主流话语,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传统史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变化特别是朝代兴替,多以循环往复的论点加以概括,或可称之为历史循环观。这种观念主要是以阴阳五行的循环为理论基础,解释治乱兴衰、分合不常的历史现象。决定治乱兴衰的力量,则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出”的天命。按照这种逻辑,年代最早的三皇五帝时代反而是最理想的大同社会,而王朝更替的现象,则不过是“天命”从一家到另一家的转换。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史家往往只能对历史表象进行简单概括,朝代更替背后政治演进的基本逻辑、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都是缺位的,其观照的历史变化也不断重复着循环的旧途。历史进步观与此有着鲜明的区别。根据何平的总结,历史进步观的理论体系包含三个主要论点:(一)社会演化受规律支配;(二)理性和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三)世界历史是一个统一和有目的的过程。他同时还指出,历史进步观由18世纪的理性主义历史学家把自然科学观念引入历史学而“发现”,影响了18世纪的人文主义史学,引发19世纪西方史学的巨大变革,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以后才受到挑战。
张世保进一步指出,这三个论点分别指向历史进步论、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并重塑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无论是民国时期的“主导性史观”进化史观,还是后来成为指导思想的唯物史观,实际上各自都秉持历史进步观,只是具体的内涵有所不同。在清末以来民族危机的影响之下,“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论思想逐渐在学界蔓延开来,对人物的评价往往是从是否顺应国家统一、民族强盛之潮流的角度来认识的。依据这种观念,曹操击败各路军阀实现北方地区的统一,击破北方的乌桓等部族,都被认为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因而是进步的。而对于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赤壁之战,对参与战争的孙刘双方则可能持批评态度。吕思勉就认为,赤壁之战前“孙权假使迎降,就能使天下及早统一,免于分裂之祸。”马克思主义开始影响学术研究以后,社会史论战渐次展开,讨论的问题大为扩充,与曹操所处的时代有所关联的包括历史分期、农民战争问题、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等。涉及曹操评价的部分则围绕着魏晋封建论、黄巾起义、屯田制度、北征乌桓等议题展开,主要特点是以社会经济史为取向,以是否代表人民特别是农民阶级的愿望为判断标准。郭沫若《为曹操翻案》郑重指出,评价历史人物“特别要看他对当时的人民有无贡献,对于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
随后在答《新建设》杂志提问时,他进一步阐释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 “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观念,他对曹操的评价分为几个部分:(1)曹操镇压了黄巾起义,但建立的屯田制度没有违背起义的目的;(2)曹操平定乌桓是反侵略战争,得到了人民的支持;(3)对于曹操杀人的记载需要重新评价,应该看到他的优点;(4)曹操对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在郭沫若的研究中,界定曹操是进步还是反动的考察项更为多元,历史进步观念则是一以贯之的。随着议题的不断转换,曹操的进步倾向也越来越凸显。随着讨论的深入,对曹操的道德评价也成为了批判对象,“忠臣”还是“奸臣”的评判就成了不需要讨论的伪命题。翦伯赞就指出:“到了现在,我们不但消灭了封建皇帝,也消灭了封建皇帝依以建立的封建制社会,我们就不应该再保存以帝王为中心的正统主义历史观,而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站在人民的立场,曹操有没有‘不逊之志'就不关重要,更不应因此就说曹操是一个奸臣。”这里所包含的历史观是,人民的立场和封建皇帝是对立的,封建皇帝是反动落后的代表,因而曹操也没有必要忠于封建皇帝。
以人民的立场判断历史人物是否进步,其立足点是阶级矛盾学说,史家对皇帝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关系定位不同,其评价也会走向相反的方向。周一良也从反封建的角度对曹操进行评价,但角度就颇有不同:“曹操所以有特识,就因为他朦胧地看到这种封建化趋势是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国家的障碍,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只是反封建的态度不够坚决,“一方面企图阻止,一方面又向它妥协,甚至于自己也按照它办事”。周一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皇帝的积极作用,但显然认为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国家是有利于反封建的,因而也是进步的。历史进步观对传统道德评价的扬弃,也可算作是现代史学“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案例。尽管历史进步观本身的科学性不容置疑,但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具体到曹操的评价与研究这样的论题中,仍难以避免简单粗暴的缺陷。从学理逻辑上说,今天我们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概念,很多实际上并不是曹操时代所可能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可能以进步史观来评价曹操,但若要求曹操行事都能符合历史发展进步的趋势,则可能要以后出现的观念强求古人了。因为东汉末年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价值标准中,本没有“进步”这样的观念存在,曹操也绝无可能以历史进步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当时所流行的观念,其实也还是被进步史观所批判的儒家忠君观念和道德标准。曹操本人试图摆脱而又无法摆脱的,也是这些观念和思想。从现实影响来说,以历史进步观代替道德评价,还可能造成某些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王学典就曾尖锐地指出,“为曹操翻案所造成的影响,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是难以估量的”,因为在这里“抽象的‘社会进步'标准的实质是‘政治标准',相对于特定的‘政治',伦理道德是无足轻重乃至可有可无的”,“只要有利于某种‘政治',于是曹操滥杀无辜就变得可以原谅,可以忽略不计”。
三、政治集团中的曹操: 历史人物研究的“英雄人物与社会结构”模式
历史进步观在时间的纵轴上设置了若干标准作为是否进步的参照物,从而得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曹操加以审视。在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横切面,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科学的引入也为人物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其具体做法是,在横向的社会结构层面,将特定人物归入某种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侧重分析以这个集团的利益为导向的行为。在研究的实践中,政治集团名目不定,判断依据有别,但多以两个政治集团的对立与斗争为主线。如果说历史进步观主要影响到人物评价的话,政治集团说则主要运用于对具体史事的分析与解释。以政治集团的视角聚焦王朝易代,认为历史人物选择何种行为与策略,可能受到当时特殊社会结构的影响,最紧要者便是主导那个时代的社会阶层的利益。陈寅恪对魏晋之际的兴亡递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认为东汉中晚期“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而“魏为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则外廷士大夫阶级之代表,故魏、晋之兴亡递嬗乃东汉晚年两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陈寅恪从思想文化倾向出发,以政治集团代表人物的社会阶层为分析工具,讨论汉晋之际的政治变迁,具体到曹操个人的作为来说,就是“寒族出身的曹氏”与“儒家豪族人物如袁绍之辈相竞争”。
这种观点被学界多次援引和强调,即使后来“为曹操翻案”的大讨论中被扬弃,受其影响的痕迹也仍旧非常明显。学者在讨论中放弃了是否尊崇儒家思想的标准,改而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进行重新论述,但不少论述中其实仍有陈寅恪论点的影子。如谭其骧认为袁绍和曹操二人虽同属于官僚地主家庭,但因其出身背景不同,分别“代表名门豪族的地主”和“代表后门寒士、中小地主的地主”,曹操“锄豪强,抑兼并,这种举措,又不仅符合于中小地主的利益,也符合于农民的利益”。吴泽也将汉末的地主分为世族地主和寒族地主两类,而曹操出身宦官,是寒族地主,因此曹操的作为是建立寒族地主政权,进行反世族军阀割据的斗争。万绳楠循着其师陈寅恪的思路,自1956年发表《关于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 以来,发表了系列有关曹操和曹魏政权的研究,集大成者是他于1964年发表的《曹魏政治派别的分野及其升降》一文,使得政治集团的研究更为精细化。他在文中提出“汝颍集团”“谯沛集团”的概念,并指出曹魏政权中有的两个核心政治集团,其一是以汝颍人物为首的世族地主集团,其二是谯沛人物为首的庶族地主集团。前者主要掌握政治,后者主要掌握军事,是曹操政权的两根支柱。万绳楠系列研究的学术路径,基本的发展趋向是由人物评价走向结构分析。
他的研究对政治集团研究范式的学术推进,至少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将区分政治集团的标准从文化倾向、阶层划分引向了地域特征,开启了地域集团研究新的可能;其二是在观照对立和斗争之外,还看到了两个政治集团文武分途,合作维持权力平衡的结构型模式。这样就不仅看到了历史人物背后的政治结构,还看到了维持这种结构相对稳定的功能,也就为从长时段解释社会政治变迁提供了可能。当然,无论是地域集团还是文武分途,陈寅恪在提出关陇集团说时都曾经强调过,但万绳楠将其系统化、合理化的功劳,仍是不可埋没的。李凭在评价万绳楠对曹操研究的贡献时说,“他一直远离学术研究的中心,却独立地作出过大量的深 入的研究,是值得我们纪念的”,诚哉斯言。与万绳楠相似而稍后,田余庆的研究也从人物评价进入了地域集团的分析,其代表作分别是《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与《袁曹之争与世家大族》。他的研究后来转向了蜀汉和东吴,最后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集其大成,其政治集团分析的研究路径一脉相承。田余庆的学术思想对学界的影响力,则似乎要大于万绳楠。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五朵金花”的讨论逐渐淡出,在田余庆等学者的研究推动下,陈寅恪、万绳楠等开始倡导的地域集团研究范式逐步走向魏晋史研究的舞台中心。
地域集团以及后来出现的其他包涵某种结构与功能互动的研究模式,极大地推动了魏晋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在这种研究范式下,魏晋时代的社会与政治成为由地域集团组成的系统,英雄人物则成为维持系统运行整合的结构性功能因素。比如,学界对曹操与荀彧的关系,主要讨论的不再是辅主和谋士的个人关系,而是谯沛集团和汝颍集团的合作,是由地域背景组成的文臣和武将分途的政治结构;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也不仅仅是君臣关系而是制度体系,学者由霸府政治的组织系统和运作机制进入讨论,逐渐引发幕府、军府研究的热潮。结构化研究范式的流行,以曹操为代表的历史人物逐渐概念化,越来越深地进入政治的、社会的结构网络中被分析,其个人性格与作为也慢慢地消失在史家的视野中。
四、反思与实践:历史人物研究的新取向
作为一个被学界讨论了百年之久的研究议题,目前的曹操研究已经成果丰富而史料有限,若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还需要在新史料和新观念上下功夫。我们大概都会承认,历史研究成果的出现,会受到史料和史观的双重影响,相对于早已定型的史料,不同的史观更有可能重构史家的研究取向。在传统观念与西方史学模式互动中成长的现代中国史学,很多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其实都有来自西方的知识背景,有的学术浪潮又可能受到各种时局背景的深刻影响乃至干扰。史家的史观一直都在被重塑,深刻影响了特定时代的学术研究,曹操研究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这种重塑的影响。目前学界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已经对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不仅仅着力于归纳以往研究的成果,还开始提炼其研究范式中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并从学术与社会的脉络中观照其理论认识的知识背景。近年曹操研究重新成为热门话题,其学术生长点主要基于两个层面的进展,即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使用。新材料主要来源于2009年发掘的曹操高陵,其中挖掘出土和从盗墓者手中追缴的文物包括多枚刻字铭牌、礼器、画像石、兵器、用具等250余件文物和墓主人头骨、肢骨等残块。新方法主要在于引入自然科学的新技术,最主要的研究是复旦大学历史学 和人类学联合课题对曹操家族DNA进行的研究。
相关研究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也在学界引起了不少争议。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曹操研究出现的新材料与新方法,其实都属于史料层面的进展。曹操墓的发现属于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自不必说,对曹操家族的DNA进行研究,其实也是利用生命科学的技术手段,让原来未被归入史料范畴的DNA成为史学研究的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让遗传基因成为历史研究的证据,与20世纪初学者从被作为中药材的“龙骨”中发现甲骨文并将其用于历史研究的逻辑,并无根本性的差异,只是利用的技术手段更为先进而已。研究材料得到新的拓展,研究观念也可以有新的发展空间。近年来,中古历史研究中的评价标准和分析工具,包括与曹操研究相关的进步历史观和地域集团学说,还包括这两种史观的衍生取向,正在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反思。如侯旭东对线性历史观的批判,认为这种史观与传统史学异曲同工,因为其“以曲折的方式论证历史结局乃至现存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更深层次上使史学成为一种认可、巩固现存秩序的工具”;仇鹿鸣则通过对历史文本的构造过程的反思和大量实证性研究的展开,反思政治集团学说的不足之处。实际上,近年出现的反思性论著还不仅仅是批判和反思,他们很多还写出了颇有深度的论著,试图在“破”的基础上能有所“立”。
不过相对于“破”,“立”的难度实际上更大。我们的历史观念,很多时候其实是人类思维模式和现实世界互动的结果。就像现实世界的存在并非是以问题的形式呈现的,但人类总是以问题切入来追寻答案,最后构成了认识世界的图景。实际上,无论是线性历史观还是政治集团的二元对立模型,都不是现实世界中真正存在过的,但人类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只能利用某种简化的逻辑去理解它。人类思维模式的缺陷是无法从根本上避免的,只能对此稍加修正而很难真正走出这些陷阱。尽管如此,学界近年的研究已经在观念上开创了诸多新的可能,颇可为历史人物研究借鉴参考。如果说之前历史人物的研究范式,已经有效熔铸时间、地域与结构等分析因素的话,近年的研究则已经具体到英雄形象的塑造(话语权力)、权力运用方式(治理技术)、权威结构(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规训与教化)等层面来着手分析。大体而言,其学术背景仍旧是来自于西方。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米歇尔·福柯、海登·怀特等学者的观点逐渐走进了学者的视野。“历史书写”“知识考古”“谱系学”“权力技术”“规训”“身体政治”“隐喻”等分析概念,越来越成地为学者手中的工具。新文化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勃兴以来,以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为代表的研究,开创了权力与知识的互动关系研究著名历史人物的新路径,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出版的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通过考察纪传体王朝史的诸多意识形态装置,剖析“历史书写”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间的复杂关系,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福柯理论的影响。吕博则以武则天时代为中心,从政治景观、服饰变迁等入手,利用各种构建文化身份、表达权力、缔结新的君臣关系和政治秩序的象征符号,来考察政治局势的变化,颇有新文化史的风格。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但徐冲关注的纪传体史书,其核心内容正是史书中被权力重新 建构过的人物传记,而首个问题“起元”之争正是由曹操的本纪开始的;吕博研究符号化的武则天,其原型正是一位和曹操相似的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当然,学者在尝试进行视角转换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些研究路径是否能够形成有效的范式,还需要等待时间的沉淀。在尝试以新的理论对研究问题进行视角转换以外,另一种研究取向是研究范围的扩展与研究深度的挖掘。具体到历史人物研究来说,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大方向以外,人物所处时代的精神世界与社会观念,人物政治活动的区域与空间,人物传记文本的形成与重构,人物形象的生成与变化,都可以纳入到历史人物研究的范畴。学界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受到现代观念影响的学者所持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框架,距离历史人物生活的现实状况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注重对不为今人所注意的问题加以研究。
以古人的精神世界为例,很多现有研究跳出了传统以思想家论思想的范式,转而通过史料的细密分析勾勒某个时代的人们所共有的思维模式,尽管这些思维模式在今天看来已经全无价值。比如姜生对曹操与原始道教关系的研究,就着重关注“更加微妙的精神的或曰心智的历史沉积层”,试图探索历史背后“内在地制约着历史进程的或许神秘甚至看似荒诞而晦涩的内在逻辑”;又比如对人物传记文本的形成与重构的问题,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用严格的史源学方法和层层递进的史事考证,论证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逻辑,并对今人研究的逻辑进行系统反思,可谓用看似传统的方法开辟了历史人物研究的新境界。无可否认,在现有条件下追求研究范围的扩展和对问题的深度发掘,有些时候也会受到既有史料和知识储备的限制,可能难以深入或是存在逻辑缺环。无论如何,在学界的努力探索之下,历史人物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已经在逐渐形成。
五、简短的小结
现代史学方法影响下的历史人物研究,已历经百年之久的发展过程。虽然历史上的曹操只有一位,但学界的研究却是千人千面,研究的问题和路径也是各不相同。面对百年来数量庞大、旨趣各异的研究成果,最需要的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学术史的梳理与反思。如果我们用最简洁的语句总结曹操研究的问题与方向,那么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人物及其行为的评价与叙述,二是以历史人物为素材对其影响的时代进行分析。这两个层面其实都是一个赋予历史人物意义的过程,第一种是在某种观念体系中赋予个体行为以意义,第二种是将个人行为纳入某种时间或结构体系中赋予意义。现代史学的发展趋向是群众的作用被凸显,历史人物身上的神秘性正被逐渐揭去,成为群众创造历史的标识物。直到最近的研究中,以政治符号制造英雄光环的逻辑结构也要被解构了。从这个层面来说,历史人物研究从研究事实到研究结构,再到研究意义的路向,正是凸显群众作用的史学观念的产物。历史人物研究或许还没有到告别的时候,毕竟这个世界的发展是由人来推动的。百年曹操研究在操作和实践的层面真正取得的进展,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一是新史料的发现与解读,二是新史学观念的引入和运用。毋庸置疑,新史料和新史观有效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空间,更新了学者的研究视角。百年来的曹操研究可谓大师云集、交锋激烈,正是各种史料和史观激流碰撞,才形成了丰富而极具标志意义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曹操研究直到今天远远没有发展到“题无剩义”的程度。究其原因,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文化的碰撞、观念的更新并无止境。今天的历史人物研究,在坚守文化本位、积极挖掘史料价值的同时,也需要积极地与西方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史学观念展开交锋与对话,促成研究范式的更新换代。新的研究取向的形成,同时也需要以温故知新的态度,对百年学术积累中形成的研究范式进行批判与反思,才能真正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如此,历史人物研究才可能在研究观念与操作技术、史料利用与理论解读、事实诠释与结构分析、个体行为与整体格局之间找到合乎学理逻辑的学术生长点,在看似陈旧的史料和论题中发育出新的理论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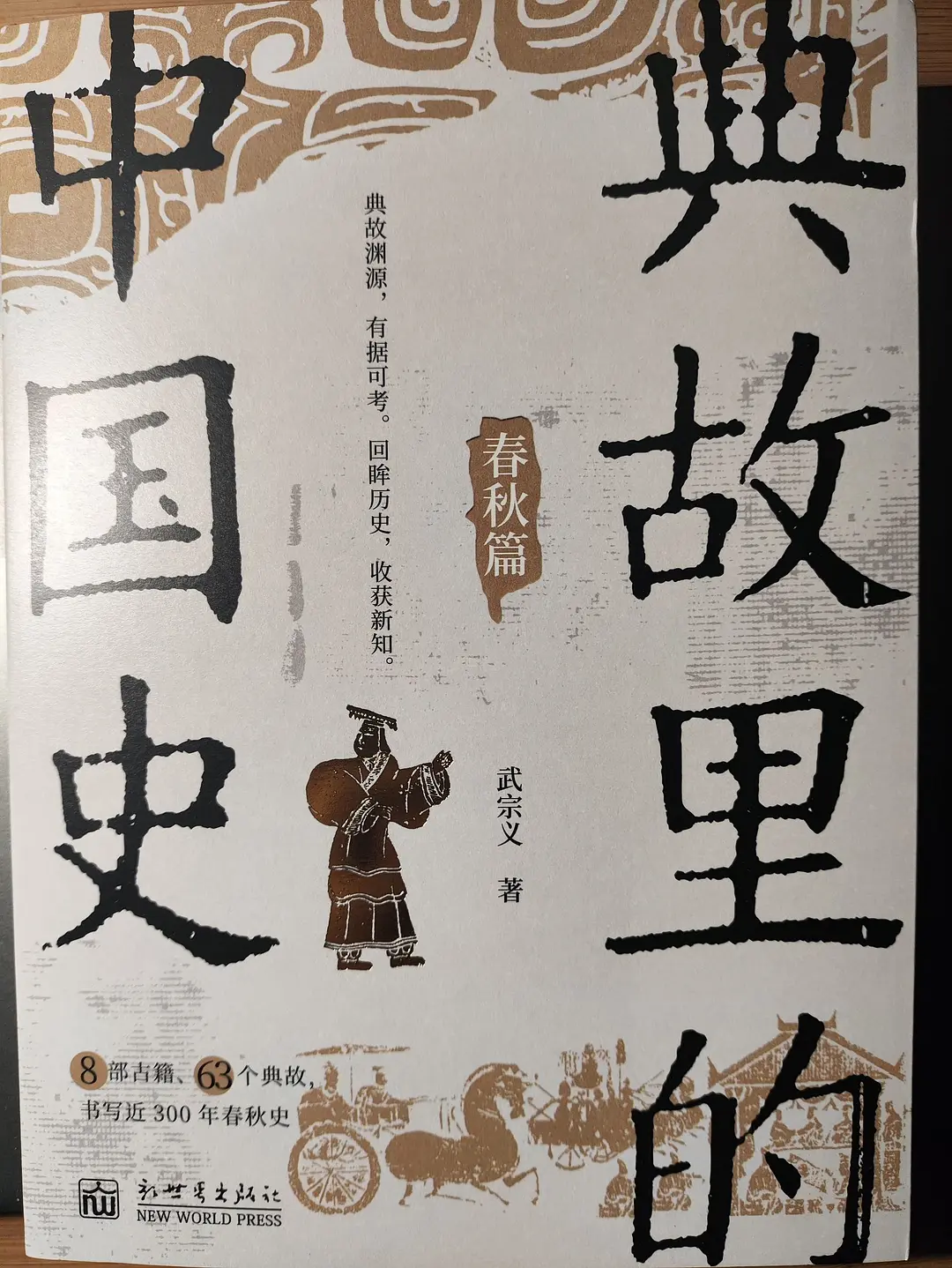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