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张冰博士《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第四章(经典互释中的多元文化视野)中的第二部分。

作者简介:张冰,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外语部主任,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俄语教学》副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副主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汉学、俄罗斯文学等。
类型学观及其情节单元结构说
文/张冰
亚•维谢洛夫斯基创立的俄国历史诗学理论中的类型学理念,日尔蒙斯基主张的以历史发生学与历史类型学为内涵的比较文学研究,以及梅列金斯基的神话诗学等诸种俄国理论思潮,可能都促使“类型学观”成为李福清原典文本阐释中重要的视点。类型学“有时用来界定文学发展的不同道路”,有时则“是对语言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相似现象的研究”,“在文本中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一个时代所特有的相似文学类型的确定”。[1]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相同题材、形象、譬喻和艺术手法的运用,是当时文本的审美范畴中重要的诗学特征之一。在李福清看来,正如克罗尔的研究,中国古代“类”的思维模式的认识论本质是“古代的中国人构成了世界模式——‘统一的连续性’,世界可以最简单地分为两个‘类’——阴和阳”,儒家认为“它们是彼此相连的,而且和谐地相互作用着”。[2]因此,“中国人用‘类’这个术语不仅表达类别,事物的种类,而且还传达‘类似’、‘相同’,甚至‘比较’的意思”。[3]而作为特殊的因果关系的“因果报应”观正是中国文化分类的基础,其对经典文本的情节结构作用显然因为外传佛教的定数观念等的影响得以强化。由此,李福清指出,《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中诸多人物转世而来,说明“古代人物以新面貌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再生,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前提的,而是较晚时期事件和人物行为同较早时期事件和人物行为有共同的规定性。类比就产生在这个基础上”[4]。

【李福清与作者张冰的合影】
“中国古代逻辑学中,正是用‘类’这个术语表示‘设计客体彼此行为模式’的范畴。”[5]李福清认为罗贯中叙事行为构建中使用的类比引入类型可以分为:1.“直接类比,即作为叙述人的作者或者某一位主人公说,从前有过这样一回事”,表现出中国儒家的劝谏传统;2.“将当今活着的人物同往昔的人物起先比较或者比拟”,突显人物特征;3.“隐蔽的类比”,历史上类似事件的套用,如,《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曹操“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于内教练水军,准备南征”[6],可类比于汉武帝的开凿昆明池,以习水战,南征。罗贯中意在以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比塑曹操的反面人物形象;4.与成语有关的类比,增强了文本的艺术表现力。李福清通过发掘类比思维的艺术意义,完成了其对经典文本中形象结构、人物形象诸要素成因中的多元文化的逻辑连接。
哈佛大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集》(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2004)将具有共同主题特征的文本呈现出来以建构世界各文学间的关系作为着眼点,其实也是“或因为文本与其他传统有直接关系,或某种文化的特性只有在差异的集合中才能充分理解”[7]的世界文学为一个整合领域观的体现。由此,李福清阅读视野中的文本,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特定的文学事实,而是一个总体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与其他各个环节横纵上下,丝丝相关、相扣、相连。通过这样的跨民族横向的多元文化视野比较研究,李福清发掘出诸多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独有的审美特征、发展规律。譬如:他研究《西游记》,阐述其与中国民间文学独有的密切关系,孙悟空不是历史人物,而是典型的叙事诗人物,“孙悟空形象中有不少较原始的(archaic)民间叙事诗人物的特征。原始叙事诗与后期叙事诗根本的区别是人物的敌人,在原始的叙事诗中,敌人一般都是各种妖怪,而后期的则是真实的历史敌人,如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雅库特族较原始的叙事诗中英雄与地府妖怪争斗,而在后期的中世纪法国、西班牙或俄罗斯勇士歌的敌人是历史上侵略这些国家的敌人,孙悟空的敌人也是各种妖怪、各种精,他多用法术战胜敌人,并不是靠自己的体力,这也是原始叙事诗的人物特征之一”。[8]他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形象与民间传说的关系,指出,中国传统的民间传说中形成了有许多传说只围绕着一个人物的独特的传说群,如关公传说群,诸葛亮传说群、孙悟空传说群等等;他研究冯梦龙,总结出中国中世纪晚期话本小说的典型样式特征,如,对口头说唱文学典型“开场诗”结构形式的保留等等。他研究小说经典《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人物描写特点,提出杨志与林冲外貌描写的原则有本质不同的论见。“一个主要是新的文学原则(对杨志的描写),可以相对地称作现实性的,而另一个是传统的、综合性的原则,——可以称作是神话史诗式的,是建立在人物外貌特点与动物外貌特点比拟基础上的(对林冲的描写)。”[9]而《金瓶梅》中报应往往同梦寐幻影相连,披散头发象征感情和情欲放纵等等都是中世纪文学的共同特点。
李福清“运用俄罗斯文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在原典互释中的另一独特表现,在于他解析经典文本时,运用普罗普的功能叙事理论,创立的“情节单元结构说”。如《水浒传》中“杨志卖刀”被分解为13个情节单元后,见出的平民生活综合情节具体化的“生动性”;而在《三国志平话》中,李福清从“情节的最小单位是人和物个别的一次行动和一个举止”[10]的认知出发,将其中诸多的动态描写分为一个个间隔,每个间隔由视为一组的动作举止完成。这些举止构成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统一的结构,过渡到另一间隔。从此可见出“在走向情节化叙事的道路上,平话显然是前进了一步”[11]。论及到《三国志平话》“微小的结构(自然是与未来的演义比较而言),同时又必须拉长巨叙事线索使之与巨大的时间距离相适应,这就迫使作者不得不运用这种‘记录式’的叙事”[12],李福清显然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迪尼亚诺夫“结构的大小决定结构的法则……”获得了理论支撑。
注释:
[1]李福清:《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301页。
[2]李福清:《汉文古小说论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3]同上书,第79页。
[4]同上书,第80页。
[5]同上书,第83页。
[6]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318页。
[7]马·罗·汤姆森:“国际经典中的焦点转换”,《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大卫•达姆罗什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6页。
[8]李福清:《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108页。
[9]李福清:《汉文古小说论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10]李福清:《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65页。
[11]同上书,第67页。
[12]同上书,第69页。
本文原载于张冰《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本期编辑
李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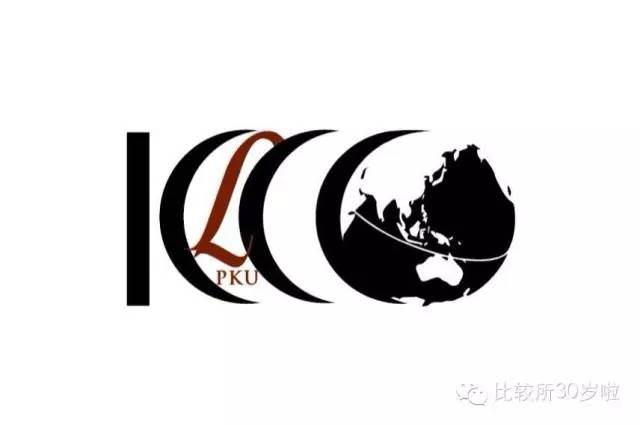
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公众号
比较所30岁啦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