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状态下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文明社会出现之前,人类的自然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未解之谜。英国人霍布斯根据当时航海所发现的美洲食人部落的情况,推测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野蛮而彪悍的:他们奉行丛林法则,以大欺小、以多欺少,经常互相残害。为了避免这种“苦难的自然状态”,人们才需要一只更为强大的巨兽来压服一切个人的力量,为弱者主持公道——于是,人们通过签订契约,把权利转让给一个强大的主权者,以便得到他的保护。
这种思想与唐朝人柳宗元相似,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初民之时,人们为了生存就得互相斗争、互相杀戮,为此争而不已,最终“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人们需要一个能明断是非的“君长”来主持公道。在“君长”的指挥下,才出现礼乐刑政等文明社会的政治制度。
霍布斯与柳宗元其实都是君权主义者,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君主是不可或缺的,他是政治活动的核心。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有力推动者,并且君主的权力是人民心甘情愿转让给他的——君主是所有人的保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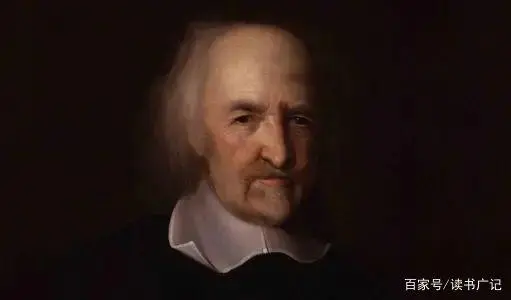
霍布斯(1588-1679)
为了推翻这种思想,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对自然状态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伟大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胆怯、懦弱而又无助的;他们畏惧大自然,不敢招惹丛林中的飞禽走兽,只有群居而活才能得到一丝安全感。因此,自然状态下的人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并非相互攻击与杀戮。
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卢梭则进一步发挥,他说人们之所以要走到一起,组成社会,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而需要制约。相反,正因为自然状态下的人太过于弱小了,所以才需要聚集起来,以便对抗其他物种,获得安全感。
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强壮有力,只要他离开人类的群落,选择独自一人在丛林里过活,他最终必然会变成猛兽们的晚餐。人们之所以要过上社会生活,是出于集体生存的需要,而不是苦于个人间的争斗。社会才是所有人的保护人,而不是一个“君长”。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人并不是丛林中的猛虎,也不是草原上的群羊,而是有着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动物。
当人们决定放弃离群索居、与同类们一起过上群居的社会生活时,就脱离了自然属性而获得了社会性。群居中的人并不像羊群那样各啃各的草皮,相反他们有着分工与合作,男子外出狩猎,女子四处采集;一群男子共有一群女子,而氏族里的儿童也是所有人的孩子。这是最初实行群婚制时人类的社会组织。之后,这种氏族扩展成胞族,胞族推广成部落,部落联合成城邦,城邦又组成为国家。而群婚制也变成了对偶制,对偶制形成专偶制,专偶制组成现代家庭。
在文明社会中,每个婴儿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获得了社会属性。他不是深山里的狼孩,而是某国某省某家某户的孩子;他与父母、兄弟、亲戚、邻居、伙伴等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
因此,可以说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动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为了规范这种社会关系,就需要签订社会契约——每个人都与这个社会达成一项协议,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以便获得社会赋予的新权利。
卢梭的社会契约的理论
社会契约是每个人与整个社会签订的契约,是一种权利交易。人承诺放弃天赋的自然权利,作为报答,社会赋予他新的权利,并加以保障。
例如,每个人都拥有着绝对的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这是一种自然权利。但是这种权利是抽象的,不能实现。
首先,它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例如人不能想摘就能摘得到月亮,也不能想吃就吃得到珍馐;其次,这种权利还会受到主观条件的限制,我所拥有的自由未必能被我想得到。例如我可以通过破窗而出,挣脱牢狱,获得行动自由,但我思维受限,没想到还有这个办法,只能甘于受缚。最后,这种权利在实行起来会处处受限,无法落实。因为我想做的事经常也是别人想做的——大家都想走同一条路,结果反而互相妨碍、互相侵犯,谁都没有得到想要的自由。
对此,社会说:“请你与我签订契约,放弃这种抽象的自然权利,我将赋予你真正能够实现的社会权利。”
当每个人都把抽象的自然自由放弃掉之后,社会便赋予大家平等的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它利用规则来限制每个人的自然自由,以便整个社会都实现真正的自由。例如,在十字路口安装红绿灯,并要求所有人都要遵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因服从于社会规则而放弃了横冲直撞的自由,却获得了顺畅通行的自由。
社会契约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规范每个成员,通过限制自然权利来实现社会权利。而人们之所以愿意参与社会契约,乃是出于生存的需要。社会是每个人的保护者,每个人又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说只有人民才是主权者
所谓的社会是由一个又一个签订契约的人组成的,这些人转让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形成了社会的公权力。社会又通过公权力来保障每个成员的社会权利,从这种角度来说,社会就是主权者。
社会统治着每一个人,要求他们服从法律、遵守规则,并且能够通过公权力来惩办一切破幻规则的个人与集体。所以社会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但人们又无法直接统治自己,所以他们经常需要通过推选公职人员的办法,把公权力委托给一些人,让他们来代理执行“社会”的职能。担任公职,拥有权力的人在古希腊被称为“公民”,而所有签订社会契约的人则被称为“人民”。
“公民”本身也是“人民”,只是他们被委托担任公共职务,代理“人民”来实行统治。但在一些情况下,“公民”经常会窃取“人民”的权力,他们赖在公职上不肯走、也不肯交权,俨然以“君长”自居,自称自己就是“主权者”,是全体人民的保护者。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约遭到了破坏,社会权力变成服务于一己之私的工具,导致许多人对社会产生厌恶,更渴望离群索居,恢复自然状态。
无论在何种请情况下,社会公权力都不可能转让到一个人的身上,君主不过是一个窃权者而已。主权者不可能是一个人,也不可能是一小撮人,而永远是全体参与社会契约的人,主权只能在民,而不会在君。
人民既是国家的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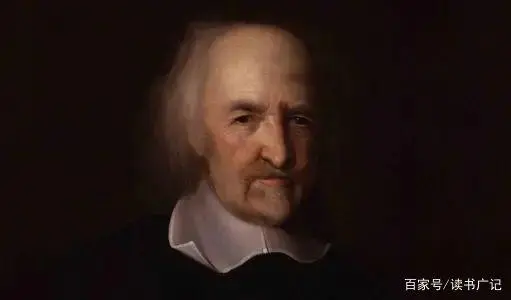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