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间,杨月楼在上海租界的著名戏园金桂园演出,令沪上男女为之倾倒。他们不看一般的京调,只看杨月楼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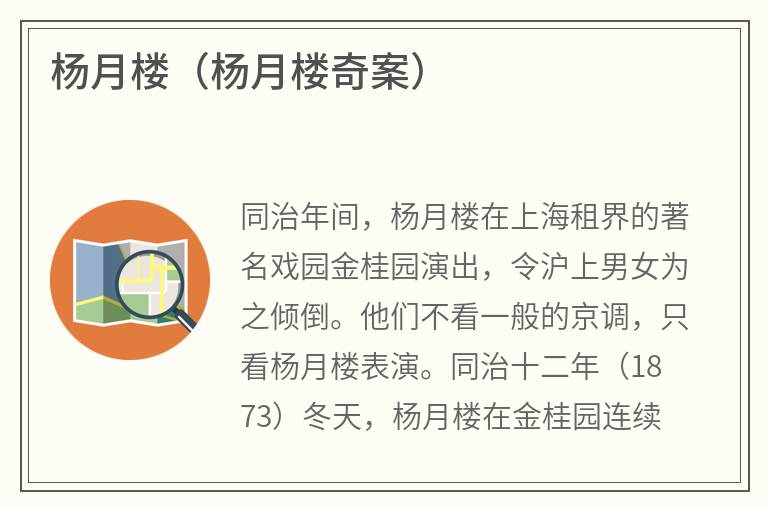
杨月楼(杨月楼奇案)
同治十二年(1873)冬天,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一对广东来的韦姓母女连着看了三天他的演出。这位17岁的韦姓少女名叫阿宝,对杨月楼由痴迷产生了爱慕。当她回到广东后,就写了一封信,向杨月楼表达了思慕之情,并打算与他订立婚约。她将这封信连同年庚帖一并派人交给了杨月楼,约他相见。杨月楼对这件事有些疑惑,也有些害怕,不敢赴约。这名少女倍受相思之苦,竟一病不起。由于少女的父亲长期在外地经商,所以母亲便顺从女儿的意愿,将此事告知杨月楼。杨月楼这才相信,并前往与少女相见。双方请了媒人,订下婚书。杨月楼还送去聘礼,开始准备婚事。
可是,偏偏在这时,韦女的叔父得知了此事,他以良贱不能通婚的礼法对这件婚事强加阻挠。无奈之下,韦女的母亲找到杨月楼,他们秘密商议仿照上海民间的旧俗,进行“抢亲”。韦女的叔父认为抢亲就是拐卖、盗窃,于是把杨月楼告上了衙门。
就在杨月楼在上海的新房里举行婚礼的当天,上海县衙的差役和巡捕突然闯到,把杨月楼、韦女以及陪嫁的七箱衣物、首饰押解公堂。这一事件引来了成千上万的民众沿途观看。凑巧的是,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也是广东人,因此他更加痛恶杨月楼,在公堂之上对杨月楼施以敲打胫骨150下的重刑。而韦女则更显得坚决,她不仅没有反悔之意,还自称“嫁鸡随鸡”,对杨月楼绝没有异心,也遭到了掌嘴200下的重罚。随后,杨、韦二人被关押起来,等待韦女的父亲回来之后再行判决。
一位如此有名的优伶竟然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这场良贱通婚的案件很快就被传遍了街巷,舆论轰动,杨月楼也红极一时。那么,当时的人们究竟怎样看待杨月楼的婚姻呢?
韦女的父亲是一位茶商,他通过捐钱买官得了功名,是上层社会有身份的人。而杨月楼被称为戏子、优伶,操持的是一份贱业。他娶良家之女,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越份之举。韦女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家族的名誉,私下向优伶请婚,也是违礼之事。总之都是违背了通行的“良贱有别”的道德礼法。“良贱不婚”这一封建社会正统礼法准则,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了。所以,此案一经发生,一般的议论都是对杨月楼和韦女采取否定的态度,甚至有许多人通过公开的途径进行辱骂性的议论。上海的《申报》报道当时人们议论用的是“不堪入耳”这个词。该报的主笔,在事发之初关于此案的报道中,也是习惯性地从道德礼义观念出发,附和传闻,顺乎成说,对杨月楼和韦女多有贬斥之词。在案件审理的初期,《申报》所刊登的关于此案的报道用了“杨月楼诱拐逃案发”、“拐犯杨月楼送县”的标题,正文中也多有“拐盗”、“诱人闺阃”、“恶贯满盈”等带有污蔑色彩的词句。无论是出自自身利益考虑的韦氏乡党,还是以维持风化自任的上层社会名流,都是顺着这一思路,以“良贱之别”的传统身份观念和道德礼法为最高准则,对杨月楼和韦女的行为给予完全否定和道德谴责。为了维护道德礼法,他们主张对杨月楼从重惩罚。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采取敌视的态度。同情派认为杨月楼和韦女是受了母亲之命,请了媒人,具备婚书和聘礼的,一切程序符合明媒正娶,因此是合法的。而至于违反“良贱不婚”的责任,则应由主持婚姻的家长——韦母承担。此外,同情派还强调了人情天性,来辩驳重惩派所讲的道德礼法,因为肯定人性也属于传统的观念。孟子说:“食色,性也。”一名优伶,忽然有人将美人许配给自己,如果不愿意,难道不有反人情吗?他们对于韦女不顾身份而执意嫁给杨月楼,并在公堂上喊出“嫁鸡随鸡”、“誓不再嫁”的行为给予了赞赏,称赞她能不嫌弃所爱之人的微贱身份,愿同生共死,气节很高。 围绕杨月楼一案,重惩派与同情派在《申报》上展开了近一个月的争论。双方各执一词,愈争愈烈。《申报》主笔一改初期反对杨月楼的姿态,转为同情派的代表。他们写的文章锋芒直指官府,且言辞越来越激烈。由于《申报》发行广,影响大,造成了很大声势。上海地方官恼怒,对《申报》发出威胁。为避免事态扩大,《申报》不得不在十二月七日宣布拒绝所有来稿,就此结束了这场笔战。关于杨月楼最后的结局,传说最后出来为他们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此案后经淞江府复讯,仍维持上海知县所定的“拐盗”之罪,杨月楼被判充军,韦女则被遣送善堂,重新择偶许配。多年以后,杨月楼忧愤地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显然,此案最终还是以重惩派和官方的胜利而告终,表明他们所代表的正统观念仍然在社会上居于优势。但是,《申报》上各类人士围绕此案的这一番大争论,反映出在近代化社会转型初期,中国社会伦理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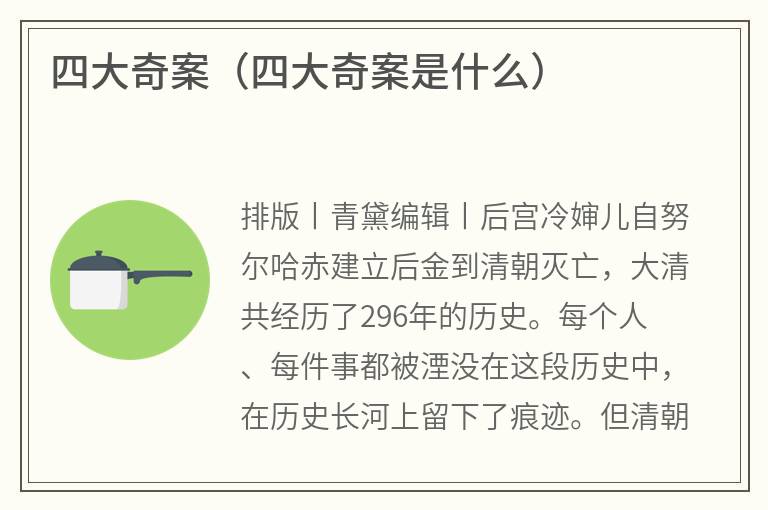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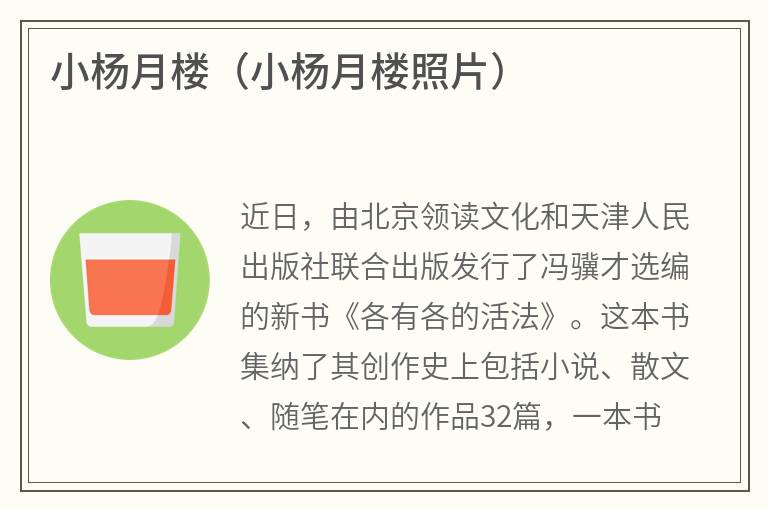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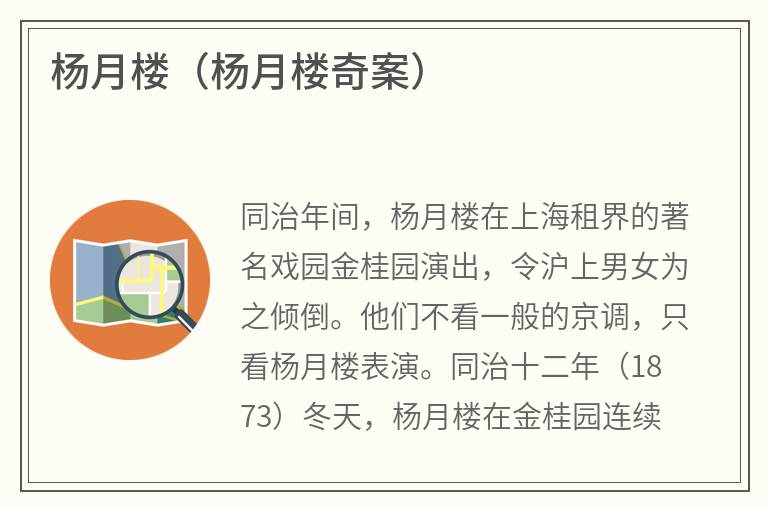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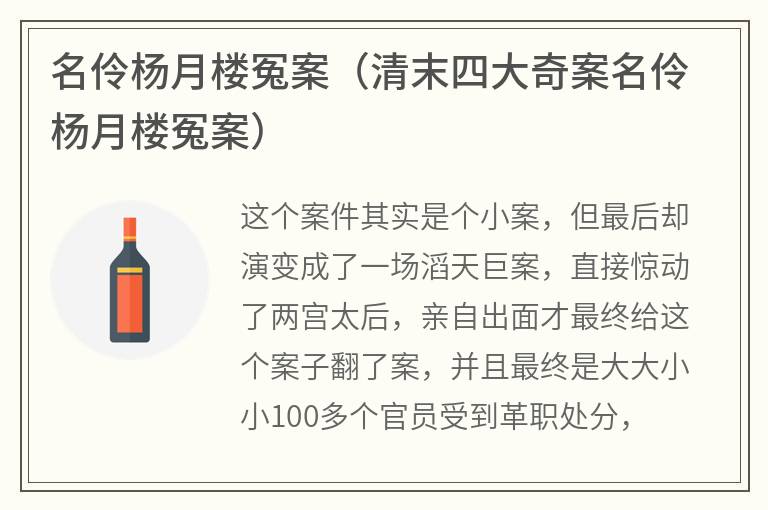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