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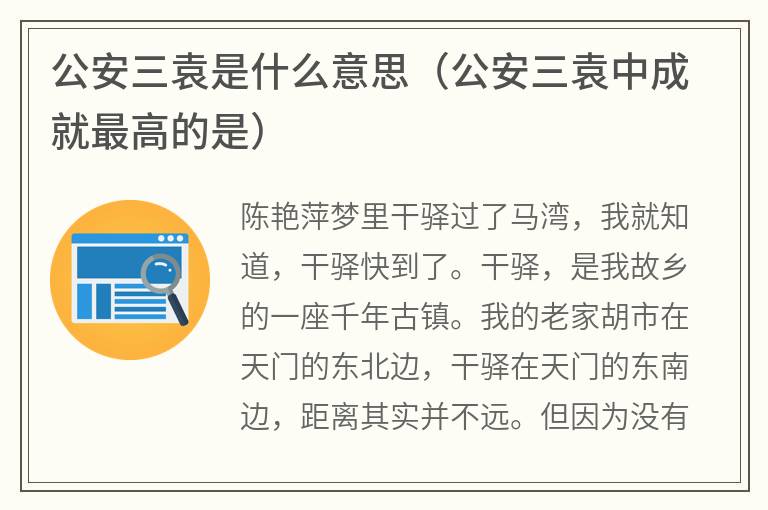
公安三袁是什么意思(公安三袁中成就最高的是)
梦里干驿
过了马湾,我就知道,干驿快到了。
干驿,是我故乡的一座千年古镇。我的老家胡市在天门的东北边,干驿在天门的东南边,距离其实并不远。但因为没有什么交集,就一直未曾来过。
古云梦泽中,干驿这地方,地势稍高,有一块滩地。人们划着木船讨生活,在此地停留,买卖和交换物质,很热闹,形成集市,取名晴滩。后来又叫古晴滩。后随着古云梦泽水系的不断变化,泥沙淤积,晴滩越来越高,成了干滩,也就改名为干滩。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设驿站,名干滩驿。清雍正四年(1726年),更名为干镇驿。“驿”这个字,很好理解,那就是明朝时,此地设过驿站,供官家使用。
顺着这个思路一想,眼前就会出现一些画面:得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驿站的店小二一听,好像不是一匹马,而是好几匹马,并赶紧出门迎接。着官服的人一个个下得马后,店小二接过缰绳,牵马来到拴马石边,拴好马,快速进堂去服侍官人。
吃什么,是不用问的,那一定是天门的蒸笼格子。喝什么,是不用问的,那一定是古镇最好的酒坊酿出的粮食酒。对,肯定会有一盘油盐豌豆。最后,到吃米饭时,店小二还会给他们端上一碟鲊辣粑,一叠洋生姜。酒足饭饱后,枕着牛蹄支河,几位外地人酣然入梦。第二天早上,吃几个干驿锅盔后,他们上马,绝尘而去。
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干驿曾经的繁华是不言而喻的。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干驿曾经的名气是不言而喻的。
往干驿东走十里,有一个镇,叫田二河,属于汉川,是汉川名镇。自古以来,干驿古镇这样繁华,也与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强强相连,美美与共。当然,还和干驿人有关。明朝时,有好些个干驿人在朝廷里当大官。
我走进干驿之前,就知道,它和很多古镇一样,失却了古味,失却了古韵,失却了古建。所以,我之此行,并不求能看到些什么。只希望,能听些什么,感受些什么。
去前,跟周老师说,周老师联系了他的发小魏老师陪我游古镇。还有朋友洪峰的堂哥奉林,趁暑假在老家照顾父母。对于古镇风物,他极有兴趣。就这样,也就有了古镇三人行。
说起干驿古镇的消失,真令人唏嘘。相比于其它古镇,干驿古镇的古早味道消失得更早,更彻底。
这,来自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接连两场大火。
火烧老街
历史绵延而来,有文字留存,有口口相传,使得我们知道,那场火灾的始作俑者是谁。
古鼎新,这个陕西人,是我家乡江汉平原上的知名人物。不是因为他善,而是因为他恶。有顺口溜可证:天见古,日月不明。地见古,草木不生。人见古,有死无生。物见古,化为灰烬。儿时,我总是听爹爹和其他爹爹聊天时,说起“日古打劲”这个词。这个词,就来源于古鼎新和王劲哉两个人。
王劲哉,也是陕西人,当时统领128师。据守江汉平原一带,是侵华日军的心腹之患。书里说,他的队伍经常打胜仗,助长了军阀作风和半独立意识,所到之处,从不爱惜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
古鼎新,只有一只眼,人们也叫他“独眼龙”。魏老师给我看了他的照片,有一说一,抛开眼睛部位不看,此人还是很英俊潇洒的。他原本是王的部下,驻扎干驿。在干驿刘洲村建了步枪厂,在干驿的皇殿小学举办过两期军官培训班。武器得以充实,人员得以补充,使得他的势力迅猛发展,使得此人更嚣张更残暴。民谣为证,人们恨他之深。
王发现古为人诡谲,桀骜不驯,就想除掉他。古知道后,密谋投靠日军。他离开干驿,逃到汉川脉旺的侵华日军处。
王一路追来,见古部已投敌,王命令部队暂住干驿待命。怕古鼎新日后再返干驿,王命令他的部下李德新率兵对干驿古镇实施“焦土政策”,除祠堂、庙宇、公房以外的建筑,全部烧毁。也得以这一命令,皇殿保护下来了。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的深夜十一时,李德新率领一个营的士兵荷枪实弹,手持火把,挨家挨户地敲门砸户,让大家交出金银财宝后,再将所有人驱赶到牛蹄河堤上,从下街一家弹棉花的铺子开始点火。那晚,起着呼呼的北风,使得火势迅速蔓延成一条几里的长龙。见烧得不彻底,隔一天后的十三日,又来烧了一场。
千年古镇被毁,当年的损失无法估算,后来的损失更无法估算。一夜之间,明清两代积累的千户重镇成废墟。两天之内,万余居民无家可归宿在干涸的河床。后来的古镇,再也没有恢复过原貌。
魏老师的家,当年就在古街上。他听他的父亲说起过,富户人家的房子,有七个天井,八个天井,十几个天井,可以想象,那房子得有多长,多壮观。
我在老街上转悠,一道围墙围住的里面,有一栋老式建筑。残垣断壁,依稀可见当年的精致,当年的风情。魏老师说,这应该是小户人家,太简陋,他们看不上,也就放过了。
这么多间华美的房子,被人点火焚烧,火光冲天,哭声漫地,那骇人怕煞的凄惨场景,仿佛就在眼前。毕竟,只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情。
太惨了,太惨了。无论以什么理由,都不能洗刷这样深重的罪孽。
古鼎新,后来被活埋。
文风流响
我没有来干驿之前,读过胡德盛先生写的《天门县东乡史考》,周庆璋先生原著胡德盛先生补注的《干镇驿乡土志补注》,大致了解过一些干驿镇的古人,古事,古景。
虽说是第一次来,但也还是有备而来。
干驿的人文底蕴,如高天厚土,是不好写的。但我既然来了,也还是略略写几句。要向大家说明的是,这些内容,我也是道听途说,也或查书所得,如果错了,漏了,请大家原谅。
牛蹄支河,是干驿人的母亲河。我在一些文章里读到,说是河流所经之处,如牛蹄形,所以叫牛蹄支河。
这次,我听魏老师说,他听老人们讲,清朝时期,河道疏浚改流,从这家的田产前通过也不行,从那家的田产前通过也不行,后来达成共识,把牛的眼睛蒙住,让它在前面走。它走到那里,水流就通向那里,所以叫牛蹄支河。
干驿这地方,仿佛是文曲星下凡。历史上,文人名士辈出。古镇人传唱的一首歌谣,做了生动的诠释:一巷两尚书,五里三状元,前面一天官,座后一祭酒,挂角有都堂,镇中出巡抚。
其中,以“座后一祭酒”的鲁铎老人,最为显赫。人们说,是鲁铎开启了天门干驿的文风。鲁铎之后,干驿镇走出了很多读书人,大人物。
鲁铎(1461年--1527年),字振之,号东冈居士,又号莲北居士,学者称“莲北先生”,晚年称“止林老人”。明祭酒,国子监最高官员。他去世后,由嘉靖皇帝派遣官员来主持葬礼。
干驿古镇,有一栋建筑,叫皇殿,初听说时,我大吃一惊。一座乡村古镇,怎么能有这样的“地名”。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有个猜测:离这里不远的钟祥,有皇亲皇眷,后又有皇陵。皇帝从京城回故园省亲,一路上总要休息停顿,这座皇殿,只怕是皇家的行宫。后来读胡德盛先生编写的书,里面也是这样说的。
但干驿镇的老人们却说,皇殿和鲁铎老人有关。
正德元年,也就是1506年,新继位的明武宗朱厚照赐给鲁铎一品朝服,派他率团出访附属国安南去和番。安南,就是今日之越南。并许诺,和番成功,可让他做三天皇帝。鲁铎和番成功后,回到朝堂,大臣们纷纷劝说皇帝,让鲁铎做三天皇帝的事情,万万不可行。万一他想永远做皇帝,闹出事端,那就不好收拾了。后来,折中了一下,在鲁铎的家乡干驿盖一座皇殿,以示嘉奖,也或弥补。
当然,现在的皇殿,早已片瓦不存。
但有一点值得欣慰,文昌阁摧毁,砖瓦和木料运到皇殿,把皇殿改造成了一所小学。虽是荒唐的行径,但也善莫大焉。是为教书育人,是在薪火相传。
一巷两尚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明朝官员,名字叫周家谟(1547年--1630年),字明卿,号敬松,大家喊他周天官。天官,天官,名字多么宏阔,足见此人的卓越之卓越。
在朝为官期间,周家谟鞠躬尽瘁,不顾个人安危,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他曾经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职位,后遭人陷害,被剥夺官籍。返回故乡,他仍然心忧天下,后新皇帝登基,他被重新启用,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是长寿之人,活到八十四岁。
周天官去世后,葬礼由皇帝下诏举行,很引人注目。他的家人眼见如此,怕被盗墓,又给他建了十几处坟墓,让人辨不清真正的“天官之墓”。
也是这样,墓葬得以完好保存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因为一些原因,占地七十亩的周家谟之墓被摧毁。听说,开棺那一刻,周家谟老先生的肉身尚存。
另一位,则是陈所学(1559年--1641年),字正甫,号正寰,晚号松石山人。他万历七年乡试中举,1583年参加癸未科殿试,名列二甲第三十八名成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当他预感到朝政昏庸,无力回天时,主动请辞回到家乡。朝廷挽留他,下的诏书达十二次之多。
他不动心,专心在老家著书立说,和同乡进士周家谟,李维祯交情深厚,和“公安三袁”情同兄弟。袁宏道在《叙陈正甫会心集》中赞叹所学的文采: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孰谓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壮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我读到这里,特别会心,文章重在趣。趣,难得。有趣,即是好文。
陈所学老先生非常谦卑,所著诗文一直深藏不露。1943年正月初六,臭名昭著的古鼎新在干驿学人陈先源家放了一把火,松石园故址旁前后九进的陈氏故居化为灰烬。所学老人毕生著作,就收藏在这所老宅里。
湖北人常常说“九头鸟”这三个字,说是明朝张居正时期,他向朝廷推荐了九个年轻人担任监察御史。这九个人,个个刚正不阿,大公无私,学养深厚,朝廷特赐予“九头鸟”之名,以示嘉奖。这九个人里,就有周家谟和陈所学。
这是传说,不知真假,大家姑且一听。
古镇文昌阁,就是明朝所修建,它矗立在牛蹄支河畔的一处高台上。蜿蜒的街道如一条青龙,文昌阁在这里,就像青龙含着宝珠。三进院落。一进是前殿,以迎客,雕梁画栋,斗拱飞檐。二进是中殿,以教学,学童满座,书声琅琅。三进是后殿,以供奉,文圣孔子坐像,名人字画满壁。整栋建筑蔚为壮观,雄踞本镇名胜之首。
童谣里唱的,镇中出巡抚,就是周树模老人(1860年--1925年),字少朴,号沈观,又号孝甄,晚年自号“泊园老人”。
这位老人,曾任黑龙江巡抚,在此职位上功绩卓越。小镇上的老人们,经常会谈起他的事迹。
他15岁中秀才,19岁进湖北经心书院读书,25岁中举人,29岁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常,32岁任翰林院编修。
他家的老宅叫“周汇东”,一连365天,除几个重大节日外,大门常年关闭,人员进出均经过由家丁看守的耳屋差房。即使是耳屋差房,也还是花砖亮脊,飞檐翘壁,门前有石鼓和上马石。只有朝廷重臣前来拜访,才开中门迎客。
晚年的老人,闲居北京,著书自遣。常与恩施樊增祥,应山左绍佐三人诗酒酬唱,时称“楚中三老”。
歌谣里唱的“五里三状元”,那是我家乡家喻户晓的蒋氏家族蒋立墉家,嘉庆状元,也因此,天门被称为“状元之乡”。当年,蒋氏家族有好几个青年人参加考试,分别出了探花,状元,翰林各一名,说“五里三状元”,是采取类比的艺术手法,其实也可以念“五里一状元”。
“挂角有都堂”,说的就是蒋氏家族的蒋详墀,曾任左副都御史,称之为都堂。
我还想说的是,周树模老人这个家族,近代出了一位大才子,名字叫周庆璋。如今的干驿人,有很完整的乡土志可阅读,得益于这位老前辈的著作。
他生于1899年,去世于1964年。
那是1918年的初夏,年仅19岁的周庆璋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优等师范学校。临放暑假时,学校给他们布置了一篇暑假作业——写一篇关于自己家乡地方志一类的文章。
一放假,周庆璋立即从武汉回到了故乡小镇,经过多方走访、打听、考察,并查阅相关资料,最后完成了一本小册子《湖北省天门县乾镇驿乡土志》。
这份作业完成得非常优秀,不仅文笔相当优美,而且完全符合乡土志的规范与要求,“对一乡之疆域、山川、古迹、人物、风俗、出产、农田水利、教育、寺观等史料广泛收罗”。可以说,这样一本小册子全方位把干驿的情况反映了出来,弥补了很大一个空白。
作业交上去以后,学校认为非常有价值,也是天门人的校长沈肇年先生更是喜出望外,欣赏有加,就将这本乾镇驿乡土志作为范本保留下来。后来历经数十年,几经辗转,这部作品的原件竟然由湖北省博物馆转移到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最后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其抄件更是广为流传。
寻访青石板
“镇街依堤,长三里许,宽六尺。长堤一眺,则屋宇栉比,工商鳞集。村落依高阜而局,或百余家,或数十家,鸡犬相闻,守望相助,犹有古之遗风焉。
这是周庆璋老人在(《乾镇驿乡土志》里写的。
现在的小街,当然无法找到当年描述的场景。我来寻访古镇,最想看到的就是青石板。
我问魏老师,青石板还有没有。魏老师说,还有点幸存,不长。当时,已是夜幕降临,我们当即决定,去见青石板。
干驿古镇的青石板,是五条石。
明朝,干驿出了周天官,鲁祭酒,陈尚书,魏按察,李将军等高官显宦,朝廷重臣。清康熙年间,依循惯例,将干驿镇主街道改成五条石官道。西起“古晴滩”镇门处,东至“文明关”关门处的这段正街街心。整齐铺设长过三米,宽约一尺,厚过五寸的白麻石条五排,两旁铺设大小不等的青石板。其它集镇的青石板街道,一般是中间横铺,两旁各竖一排白麻石条,如梯子状。走五条石官道,有讲究,凡是五品以下官员,文官需下轿,武官需下马,步行而过。
现仅存的一段,石板斑驳破败,若不是有五条石官道的简介,很难相信这青石板昔日曾经有过的辉煌礼遇。
两边是民居,几个人坐在门口乘凉,其中一位大姐说,这青石板,如今可香喷了,很多人前来拍摄。
它是古镇唯一的象征。也或,是古镇的灵魂。
夜色里的青石板,没有看好,第二天早晨,我们又过去看。
经过菜市场,路边有人卖鸡头苞,一边剥皮一边卖,很俏销。我已多年没有见这情景了,忙凑过去看。大姐很热情,另给我剥了两个鸡头苞。才从水里捞上来,鸡头苞的头上顶着紫色花。
乡村集镇,菜市是最生动的场所。进进出出的,大多是老人。他们热情,有时间,喜欢交谈,声音洪亮,使得菜市场更鲜活。
揣着鸡头苞,提着香瓜,走向青石板老街。可惜,没有下雨。可惜,天气太热。走在这青石板路上,很难联想起戴望舒的《雨巷》,那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很难联想起郑愁予的《错误》,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只能稍稍想起的是,这青石板路上,曾经走过很多双脚,曾经承载过很多副身板,曾经踏过很多只马蹄,曾经印过很多道车辙,曾经飘荡过很多声音,曾经消散过很多话语。
魏老师说,他小时候看见的青石板街道,有三里七分长。下雨天,木屐踩在上面,发出的”嗒嗒“声,连绵而有生气。奉林说,他如今还能回想起自己走在青石板上时的跫音,回想起那抹光亮,那份寂寥。
还是昨天那位大姐,正坐在门口喝汤,她说,未来修路,青石板肯定会被拿掉。我知道大姐的意思,她的门口不平,她其实很有想法。但我觉得不会,如何改造,这段青石板路都会保存下来。
悠悠岁月,绵绵时光,这青石板,在人们的心中,已不再是路,而是印迹。已不再实用,而是典藏。
有米醋的味道飘荡,一看,街边有牌,介绍干驿李长茂醋业的历史沿革。走进去,醋香更浓。米醋,不同于陈醋,它由米酒转化而来,仿佛是为家乡蒸菜而量身定做,朴素而经典。
老板家的院子大,摆着很多口大缸。缸口戴着斗笠,在大太阳下晒着,是一道景观。院子的最深处,有一口缸,其貌不扬,但又与众不同。老板介绍,这是祖传留下之物,不敢用,怕它破。用手摩挲了一下,看起来粗糙的缸身却华润柔和。我想,这是时间之下工艺和使用之间自行转换和成就的魔力。
古镇,大的标志物,是不会有的。细细寻,犄角旮旯,细枝末节,总还有些古镇气息在悠悠回响。
民居情思
寻访干驿的一栋民居,是我的念想。
朋友洪峰,有一次发朋友圈,写他回去参加姑父的葬礼,一并发出的民居图,吸引到我了。
这次去干驿,联系到洪峰的表哥志勇两口子,得以去参观了这栋老宅。
这是我很多年前在家乡时,经常看见的民居样式。后来,再后来,这样的民居越来越少。即使有,也是斑驳沧桑,潦倒不堪。但这栋民居不同,它还是新的。但确确实实,它其实是旧的。
这是典型的江汉平原上的丈八八民居式样。什么是丈八八?就是房子的主梁高度是一丈八尺八寸。此屋三间,十根柱头落地,稳如泰山。漆得光亮的鼓皮,能当镜子用。整齐结实的梁板搭成的楼,浑然如新。
那时候的建筑,基本是这样的格局。只是柱子的多少和粗细有别,有的人家好一点,有的人家差一点。鼓皮,那确实要看条件。有的人家有鼓皮,有的人家没有鼓皮,只能用芦席隔墙。
整座瓦屋,像一幅水墨画。屋顶上,黑色的瓦片依循着自身的弧度一层层一排排扣着,颇像故乡的蒸肉。风来时,回旋的风声在屋顶穿梭袅绕。雨来时,雨水顺着瓦楞给瓦屋装上一道雨帘,下面接着木桶。一夜大雪,早晨,一截截冰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孩子们拿着竹篙敲打嬉戏。屋顶的形状像一本翻开后仰面朝天的大书,中间那道横线两侧,往天空的方向造一弯飞扬的弧线,极像人嘴角的笑意,顿使脸部表情生动起来。猫们在屋顶“飕飕”穿梭,踏出一片清脆。
清晨,木门次第吱吱呀呀,扭扭捏捏。梁上的老燕子等不及,冲出去为儿女们寻食。乳燕们张着黄色小口,伸出头候着妈妈回来。打开鸡笼,鸡们扑腾扑腾翅膀,踏着碎步,小眼睛滴溜转,找吃的。一侧的偏房,猪听到声响,大声嘟囔叫饿。主妇们手忙脚乱,吆喝着忙一阵。一会儿,各家各户的炊烟花朵般开放,和自家青瓦缠绵悱恻一番后,拉伴结伙,高空寻云去了。孩子从床上爬下来,坐在青石门槛上,等着卖锅盔油条包子的生意人快快到来。
那个年代,做一栋瓦房,动用的往往是毕生之财富。地势低洼的地方,十年九淹。涨水的时候,人们把柱头用铁丝绑起来,怕它被冲走。也有人家,怕屋倒,就在墙上打洞,让水呈流动的态势。
志勇家的这间瓦屋,坐位很高。旁边是稻田,前面是菜园,格格空空种花草。大门高敞,上书“钟灵毓秀”四个黑色大字。两边有两幅画,是自然风光。志勇妈妈说,当年,请来的工匠画不出来了,她说,她去画。结果,三下两下就画好了。
我说志勇妈妈是才情女子,志勇妈妈就笑,然后说,那个年代,绣门帘,绣帐帘,绣枕头,绣鞋垫,绣孩子的布兜等等,她是一把好手。
现在,七十几岁了,穿针引线,说眼睛一点儿不迷蒙。
老人家一辈子好强,一辈子惜物。一辈子能干,一辈子智慧。“钟灵毓秀”,不是这个词好,才用在这里。而是这个女主人就是这么好,所以用在这里。
老伴儿去世不久,老人还沉浸在悲痛中,但她很会想。老伴儿病得的不好,生活质量差,这样快快地走了,是福气。活着的时候,她尽力照应。走了,心里也没有愧疚。
老屋旁边,老俩口建了一栋新屋,儿子们并不会回来住,二老却非要做。他们是这样想的,大家都做楼房,他们家也要做一栋,享受住新房的滋味。儿子孙子们回来,也可以住新屋。
老伴儿去世后,老人一个人住着两间屋子。老屋,收检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让所有的老物件保持着原样,让老屋的风貌保持着原样。她只是晚间在新屋睡,白天里,她还是在老屋活动。
这其实是一种陪伴,某种意义上,老屋就是老伴儿,老伴儿就是老屋。
房间里的桌子上,有一对瓷坛,完好无损。是老人当年的嫁妆。梳妆盒,在岁月里自行陈旧斑驳,老人一直保存着。房间里有三台老衣柜,其中一台,老人说,是娘家的母亲用过的,后来翻新旧屋,大家准备劈了它。老人不许,抬到自己家。
衣柜上的一对铜制扣件,小鱼造型,做工很精致。这么多年了,还泛着光泽。原想把玩片刻,竟有些爱不释手。
过去,物质没有现在这样的充裕,时间没有现在这样的紧张,发展没有现在这样的现代。人们的生活很简单,很慢缓,很古拙。单纯,往往是更高级的美感。这对小金鱼扣件,可表达那个年代的很多东西。
对这种瓦屋,我的念想很深。我出生时,家里的房子是小两间,只前面是灰砖,其它三面均为土墙,摇摇欲坠。后来,它真的倒了。婆婆爹爹没有能力建房,用积攒了一辈子的一千八百元买了别人的一间房,也是摇摇欲坠,仿佛一推就倒。
后来,我离开家乡。后来,婆婆爹爹去世,那买下的三间屋倒塌。在我的生命里,一直没有盼到那样的三间大瓦房,我有遗憾。遗憾自己没有住过那样的房子,也遗憾婆婆爹爹操劳一生,晚景那么凄凉。我曾经想着,等有能力了,为婆婆爹爹盖一间崭新的瓦屋,买一台电视机。没等我做到,他们就相继离世。
人生长恨水长东。
房子,是遮风避雨,也是温暖和热闹的承载。祖孙之家,是没有的。但我还是想,渴望,也就把这种想和渴望寄托在这瓦屋之上,随时间流逝,这情结蔓延至所有的瓦屋。看起来,我是在怀旧。其实,我是在怀想,怀想当年那些缺憾,那些向往。
坐在志勇家这三间瓦屋的青石板门槛上,我有点恍惚,它成了我的家。
干驿锅盔
回到天门,锅盔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不能不品尝的美食。
没来到干驿前,我就听说过干驿的锅盔,比其它地方大,比其它地方贵,比其它地方好吃。
听说,天门举行的锅盔比赛,干驿的鲁荣初师傅得了第一名。
其实没来之前,我听说干驿有个四香锅盔,一直坚持用脱皮的芝麻,坚持熬制糖稀,坚持老面发酵等。不巧的是,天气太热,他的锅盔店歇热了。然而也是巧,干驿有十几家锅盔店,我们随便走,就走到了鲁师傅的锅盔摊子前。大马路边,他正在贴锅盔,旁边有几个人等着。
我伸进炉火里望了望,锅盔确实大,还鼓。夹出来时,丢在炉台上,“邦”的一声响。赶紧拍了一张照后,准备把锅盔装起来。魏老师说,不能装,要用纸包。只一装进塑料袋,锅盔的味道就变了。
说着,魏老师拿起一张裁好的报纸,让我托着锅盔。他说,你看,“狮子头罗汉肚起层有酥口”,这就是干驿锅盔的特点。
锅盔的两头,造型是不一样的,有一头,师傅一捏一扯,就成了狮子头样,这是师傅的造型艺术。罗汉肚的意思是说,锅盔的中间部位是鼓的,这是师傅驾驭火功的能力。酥口,是刷过糖稀的麻面,这是锅盔师傅传承的匠心。
干驿锅盔,也叫酥麻锅盔。
现在,很多师傅做锅盔,省了刷糖稀的这个环节。糖稀,要正宗的麦芽糖熬成。不然,味道也不会好。
干驿锅盔,宽大,但并不是很厚。一口咬下去,酥劲比较足。刷过糖稀,有淡淡的甜味。除此之外,再不好描述。
天门人喜欢天门锅盔,喜欢得有些痴,永远的心心念念,永远的不离不弃。那个味道,已刻在大家的肚子里。描述,其实是多余的。
吃锅盔,要趁热。再好的锅盔,冷了就不好吃了。干驿锅盔在这方面尤盛,不知道是不是配料的原因,凉了后,很筋道。
鲁师傅说,自从他得奖之后,天门一家单位请他去食堂专事做锅盔,他干了几个月后,辞职回来了。
他说,不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而是受不了限制,觉得不好玩。
在这小街上卖锅盔,每个顾客都是他的熟人。一边贴锅盔,一边还有人陪他说话。一边贴锅盔,一边还可以看着小街上的风景。仿佛,不是营生,而是在好玩。
遇到节假日,人们返乡,那锅盔,俏销得不得了。必要时,还要预定。贴不赢,卖不赢,最后,还有人买不到。人们站在炉子旁边,吃着锅盔,夸奖着手艺。
鲁师傅说,这感觉,单位食堂里是没有的。
在外的家乡人,可以找鲁师傅快递锅盔。锅盔多少钱一个,就是多少钱。快递费,由买锅盔的人承担。
吃着美味的锅盔,总担心,未来的某天,锅盔会从家乡的土地上消失。
怅然若失
写完锅盔,就此打住,前面我说,干驿古镇写不好。而其实,还写不完。
名人太多了。除我略略写了几笔的那几个人之外,还有很多。
古迹太多了。除文昌阁、皇殿外,还有书院,有庵,有庙,有寺,有道观,有各种楼阁,有观音堂,还有过天主堂。遗憾的是,所有的建筑都没有留存。幸运的是,有人做了记录。
总是痴痴地想,假若皇殿还在,老街上一长溜的房子还在,各种亭台楼阁还在,寺庙香火还在,那干驿古镇,将是多么美好。生活,恰恰是不能讲如果的。当下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能作丝毫联想。唯一可问询的,就是脚下的土地。而土地,是永恒的寂静。
对于家乡,了解得越多,越知道家乡的好。我接纳她的过程,也是她接纳我的过程。这种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好美妙。而同时,也万分心痛。
它是古镇,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名,但我在了解书写的途中,把它看成了一位老人,一位祖辈。
它包容了太多的伤害,承受了太大的磨折。它如此辉煌,如此努力。它如此隐忍,如此沉默......
陈艳萍,湖北天门人,现居武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自由写作者,出版了散文集《故乡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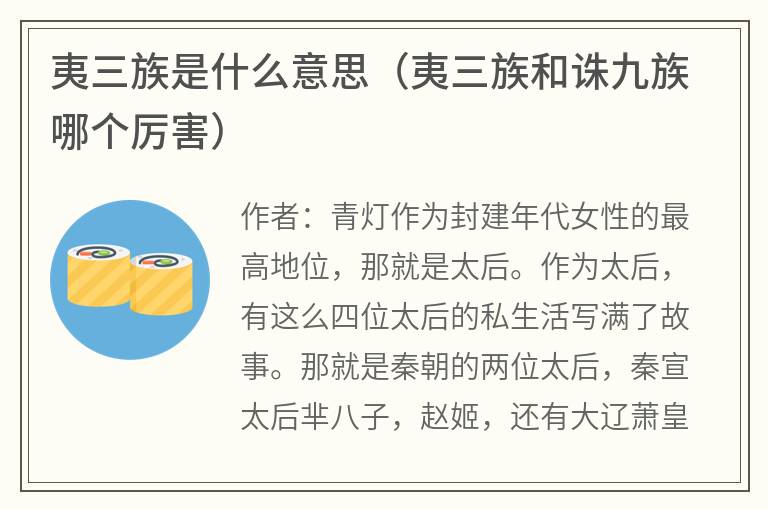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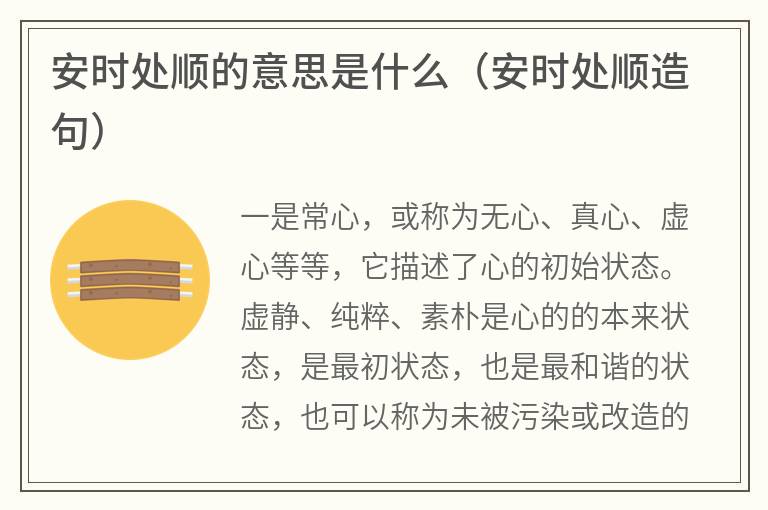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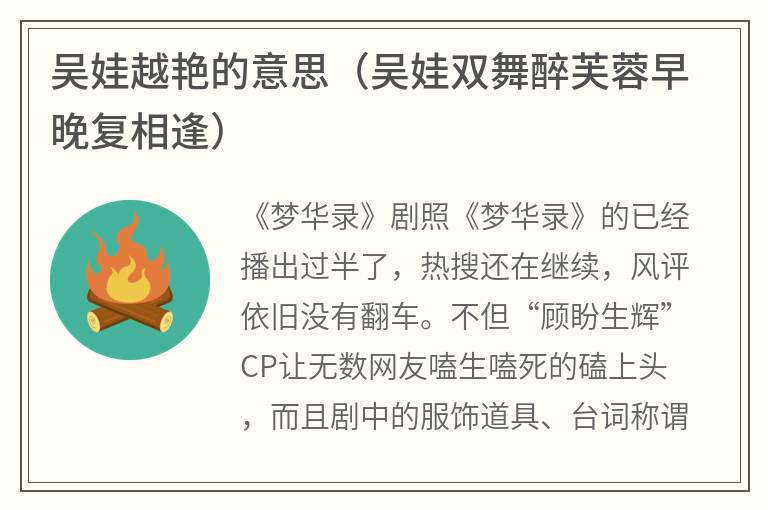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