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在《〈雷雨序〉》中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我念其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智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间,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戏剧《雷雨》就是这样的一首人性悲歌,其主人公都避免不了情感和理智的选择,都逃脱不了机遇和环境的捉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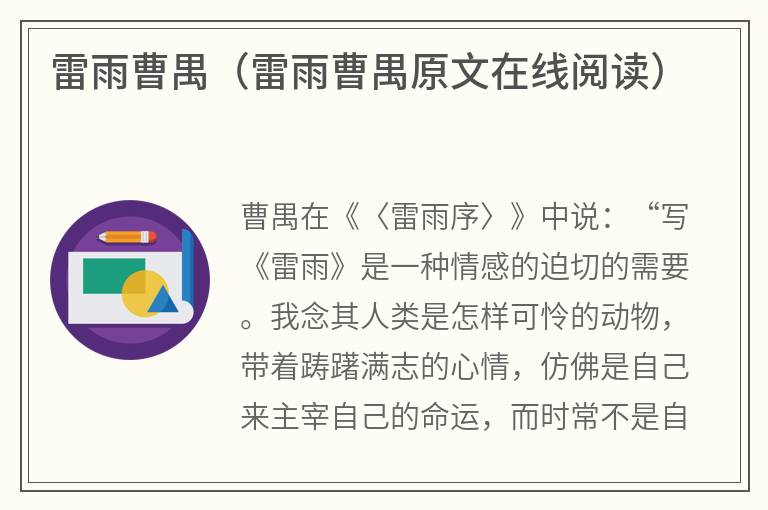
雷雨曹禺(雷雨曹禺原文在线阅读)
从课文的内容来看,周朴园对鲁侍萍不能说全无感情。他多次向人打听鲁侍萍的下落,还特地派人到无锡去打听,并一直保存着侍萍喜欢的家具,一直保持着总是关着窗户的习惯,一直记得侍萍的生日,一直保留着侍萍绣了花的衬衣。周朴园怀念过去年轻的侍萍,怀念侍萍给他带来的美好回忆。从情感上,以前周朴园对鲁侍萍是爱恋的,现在周朴园对鲁侍萍是怀念的。三十年前,周朴园在情感和理智中作出了选择,选择了富家小姐,抛弃了爱恋的鲁侍萍。他总认为富家小姐总会给自己的事业发展带来帮助,他认为这就是他的人生机遇,同时这也是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给他的共识。在事业和家庭中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也就为几十年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而现在当周朴园千思万想的真正的鲁侍萍出现的时候,曾经的情感又是显得如此的脆弱。当他听到侍萍还活着,先是感到惊愕,后是避而不见。当得知侍萍就是眼前的鲁妈时,马上就是声色俱变的责问,接着企图稳住侍萍,希望用金钱平息侍萍的旧恨新仇,最后凶相毕露,辞退四凤和鲁贵,开除鲁大海。这时的周朴园就已经完完全全成了利益的代言人,他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只想着眼前的鲁侍萍会不会破坏他的并不美好的生活及他的事业。他就在受着不可知的力量——利益的捉弄,作出了违背自己几十年情感的选择。在情感和理智之间,他又作出了理智的选择。他的环境他的生活告诉他这样的选择是合理的。
鲁侍萍在年三十晚上被周朴园抛弃,先是投河自杀未果,后来又嫁过两个男人,个中的苦痛可想而知。而这一切,都与周朴园那次理性的选择有关,她对周朴园恨之入骨是理所当然。但在她记忆深处,曾经与周朴园的爱恋,曾经的美好生活也是永存心底的。爱之深才恨之彻,恨之彻才越爱之深。我们的人生往往经历这样的爱恨交加。当她与周朴园再次相遇时,爱与恨交替浮现,爱在感性中涌动,理性又将其带回恨之中。当鲁侍萍看到周朴园的时候,她没有马上走开,她还怀念三十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用洋火,看来三十年前的生活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当周说起以前的事情时,鲁又不断地提醒对方,“说不定,也许记得的。”“无锡那边我还有认识的人,虽然许久不通音信,托他们打听点事情总还是可以的。”当周叫她下去的时候,她“望着朴园,眼泪要涌出”。并提起了绣着梅花的纺绸衬衣。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作是周和鲁三十年前爱情的象征,那时他们的爱情之花就像这梅花一样傲霜绽放。当然在烧破的窟窿上绣下的梅花终究是悲剧的隐喻。这是真实的鲁侍萍,她没有什么阶级情感,她只是一个爱恋男人的平常女性。而集仇与爱于一身的鲁侍萍的人生经历毕竟是最痛苦的。我们都希望和自己心爱的人儿相处一生,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当周朴园暴露出理智的丑恶的本性的时候,鲁侍萍意识到这个曾经深爱的人已经是如此的陌生,对他最后的那一份爱也就彻底消亡了。“不是我要来的。”“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我没有找你,我以为你早死了。”“哼,你还以为我是故意来敲诈你,才来的么?”“我这些年的苦不是你拿钱算得清的。”
曹禺在给《雷雨》导演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对于人性的触及和深入,当是该戏剧最为重要的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撩拨起我们每个读者心底的本真。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基于人性来待人处事,我们每个人在情感和理智的选择中是否每一步都是正确的。我们在受着机遇和环境的影响时,是否又都能做出客观正确的评判。学习《雷雨》,让我们重新反思生活,考量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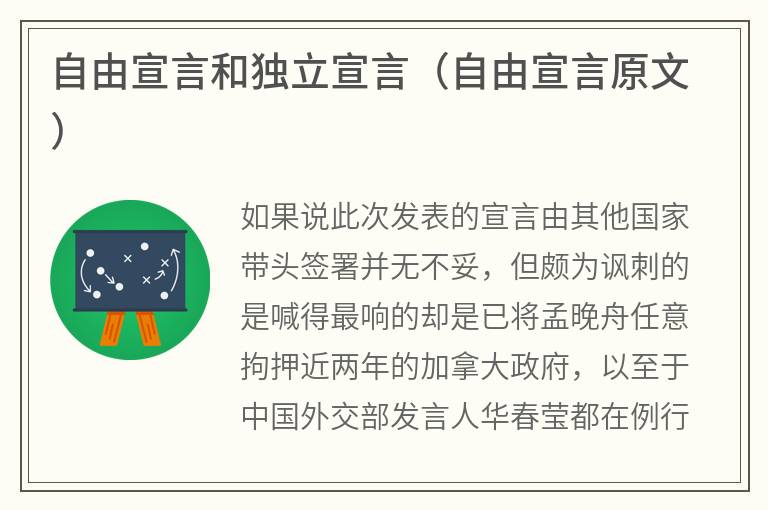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