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风景与庭园》
[日]后藤朝太郎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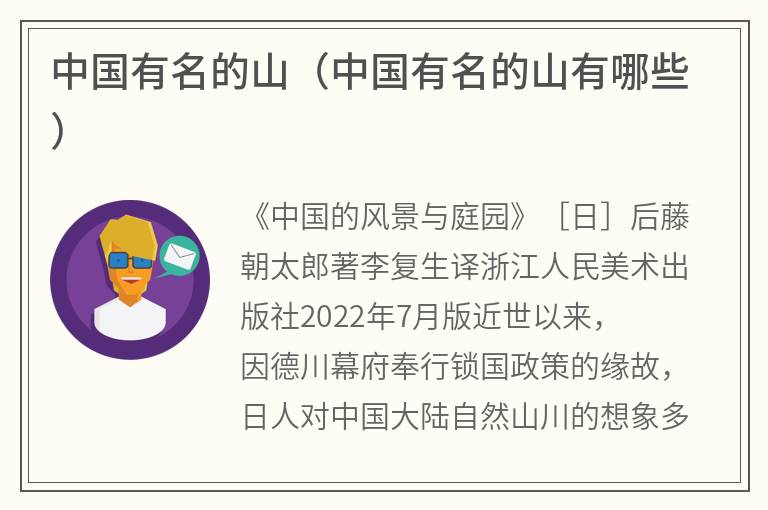
中国有名的山(中国有名的山有哪些)
李复生译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2年7月版
近世以来,因德川幕府奉行锁国政策的缘故,日人对中国大陆自然山川的想象多系于汉语的诗文,直到幕末,随着幕府派遣的商船“千岁丸”使沪,渡航者渐增,这点才被打破。从那之后至战前,日人的中国漫游记可谓灾梨祸枣,积简充栋,那些出版物的作者既有被称为“中国通”的汉学者,也有作家、记者等文化名流,也不乏“素人”。
身着长袍马褂的后藤朝太郎(1881~1945年)
这本《中国的风景与庭园》虽然出自汉学家之手,但严格说来,却不是一本汉学著作,而是一本以日本普通读者为对象的大陆观光案内书。在此书甫问世的年代(日文原版初版于1928年),可以说它涵盖了关于大陆最有价值的情报,不枉著者后藤朝太郎先后三十余次(截至此书出版的时点为三十次,作者一生访中逾五十次)南船北马的中国游历。有些旅行经验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如关于如何应对土匪绑票或“激进分子”的绑架,以及防止被轿夫敲竹杠的技巧等。当然,其核心情报仍是对大陆各地自然风景和观光名所的导览。
用轿子抬人下山甘博摄(1924~1927年)
日本人与中国人,因所处国土环境不同,在面对某些自然景观时,会有迥然不同的反应。一个被媒体用烂的例子,是对濑户内海的第一印象:这个连结本州与四国的海峡,东西狭长,南北短促,最窄处仅有5公里。在日人眼中是海,可在中国人看来,是江,是河。与之相对者,是长江。民用航空普及之前,日人闯荡大陆需靠船,一般是从门司港或神户港启程,从上海港上陆。当客轮驶到吴淞口一带水域时,面对那“水天相连,云陆相接,陆地仿佛浮在水上一般”(宫崎滔天语)的雄大风景,对看惯了濑户内海和日本内地河川的日人来说,内心受到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翻检日人的回忆录和游记,少有在那段航程不动情者,甚至动辄怆然而涕下。如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写道:
黄浦江甘博摄(1917~1919年)
而令完造惊到的“赤黄泥水”,其实是基于大陆独特地理环境的常态,所谓“百年河清”论徒有逻辑意义,这也是导致日人常识反转的心理变化之一。对此,后藤朝太郎做了一番学理分析:
如此,从河川的清浊引申到风景的色调,后藤对大陆山水园林的考察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地理,从文学到历史,到美学、心理学,是跨界的,横断式的,就知识的浓密和认识的深度而言,不仅远超那个时代的大陆风光案内书,亦非今日以“孤独星球”(LP)为代表的商业观光主义旅行指南所堪比附。惟其著者是汉学家出身的园林学者,饱读汉籍经典,才能在文学的文本与视觉的绘画、风景之间穿梭自如,而且打通了国界和符号(文字)、视觉、物理性文本的边界,像一名职业侦探似的,手握类似今天文化人类学般的道具,东敲敲、西探探,刨根问底、追根溯源,结果硬是发现了深藏不露、中日名园共通的文化DNA:
断桥残雪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摄(1911年)
说白了,正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名篇,成了中国园林的“原文本”。已故中国园林学大家陈从周先生说:“中国园林,名之为‘文人园’。它是饶有书卷气的园林艺术。”古人称造园为“构园”,正如文章的构思一样,“构”必然牵涉到美学。好的园林能看出构思,而构思得以充分呈现,便是境界。文人画常写意,中国园林亦如是,诸如“春雨江南,秋风蓟北”“小桥流水人家”“平林落日归鸦”等意象,不仅都能在大江南北的名园中找到模本,甚至可在同一座园中“一网打尽”:
不过,就像文人画也有品格之分,也会有败笔一样,基于同一种“原文本”之上的中国园林,同样有格调之高下。成也文人,败也文人,后藤朝太郎发觉,“中国风景夸大宣传的始作俑者也是文人”:
兰亭流觞亭常盘大定、关野贞摄(1918~1924年)
明文徵明《兰亭修禊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譬如,后藤经过田野调查后发现,会稽山阴兰亭曲水流觞的背景、庐山西麓虎溪桥附近的风景,“与至今流传的画卷情景相比简直天差地别,几乎突破了相关风景的根本概念”。张继的诗《枫桥夜泊》是千古名篇,“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寄托了一代又一代日人对苏州的想象,“凡到中国的日本观光客大都会去看寒山寺,但看过现状之后,基本上没有不对其表示失望的……总之大致的说法都是庙宇一般,所谓枫桥也无甚趣味,作为名胜实在是名不副实”。
桃山时代日本著名画师狩野山乐的六曲屏风画《虎溪三笑图》(部分)
凡此种种,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以笔者的浅见,不外乎两点:一是作为毕业于东京帝大的汉学家、语言学家,后藤受过西方实证主义的学术训练,这使他在面对那种大写意式的艺术表现和诸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式的文学夸张时,也会保持警惕,以至于有种把文本客观化的倾向,导致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始终隔层,殊难与文本共情入境,遑论融为一体。感觉这里既有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也有职业(学者)使然的一面。
日本的箱庭艺术
二是日人的箱庭趣味。所谓“箱庭”,是源于江户时代的日本特有的园艺工艺,类似中国的盆景,即在一只箱状容器中,铺沙土,再在沙土上布置木或陶制的人形、房子、桥、舟、水车等模型,再现日本各地的庭园、山水、名胜,实际上是按一定比例尺缩小的袖珍庭园。这种趣味的关键,是对实景的摹写,务求逼真,有些类似今天的3D打印,但并不要求“构园”。
当然,我并不是说后藤朝太郎其人一定是箱庭趣味的嗜好者,事实上也并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和证据。但这种趣味会影响思维,使人动辄从箱庭出发,再按比例放大,务求与实景关系的一一对应,在有些日本人身上,仍能看出这种思维模式的遗留。对此,其实后藤本人也有一定的自觉。他在本书的序中预言,再过25年,日本人口将达1亿左右,“到那时再看,估计这箱庭会愈加显得狭窄……我们将迎来一个不得不直面这重叠式的箱庭一隅来满足自身趣味的时代”。
昭和6年再版的《中国的风景与庭园》
这话给我们一种年代感的提醒:这本《中国的风景与庭园》已是近百年前的著作;而今天的日本,则历经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人口膨胀到1.26亿,却驶入了“老龄少子”化的慢车线。后藤希望通过这本书,引导日本人把目光投向中国,然后“面对这日趋狭窄化的日本现状和未来,再看中国大陆的庭园和风景并试加思考和比较”,从而获得一种“幅员辽阔”的思考的尺度。这也体现了作者非同一般的社会人文关怀,其学术视界远超通常意义上一介园林学者的畛域。
文:刘柠,作家,译者。北京人。大学时代放浪东瀛,后服务日企有年。独立后,码字疗饥,卖文买书。日本博物馆、美术馆、文豪故居,栏杆拍遍。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著译十余种。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陈蕴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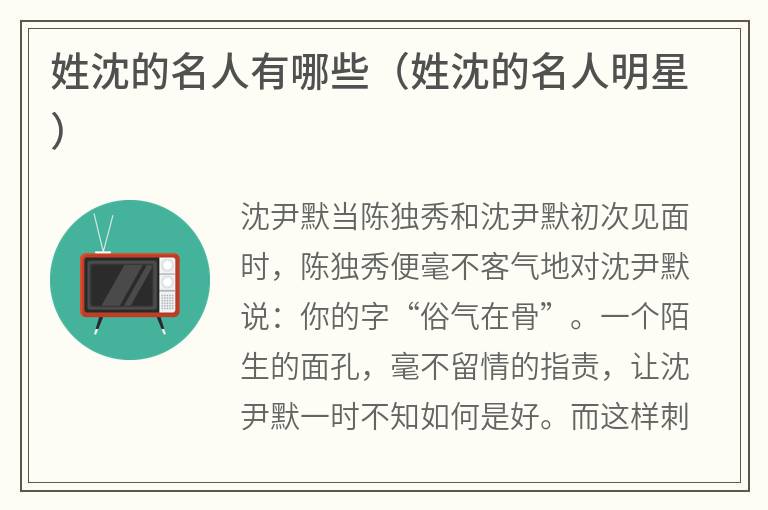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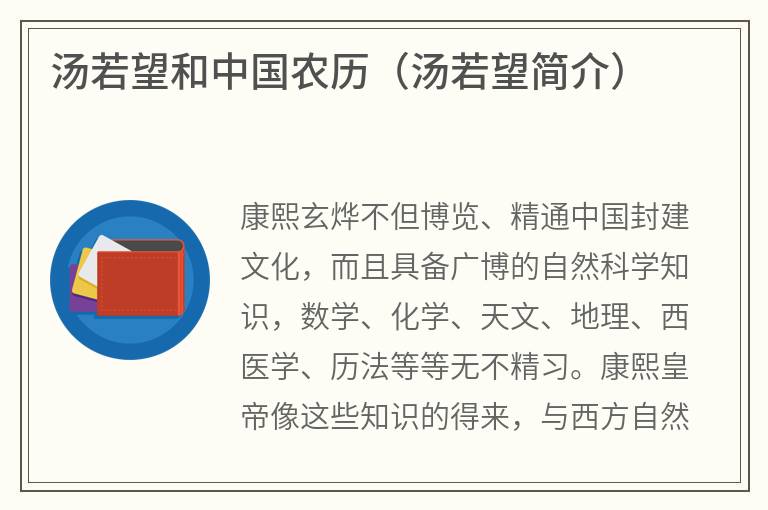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