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匠
是历史上传承最长最久的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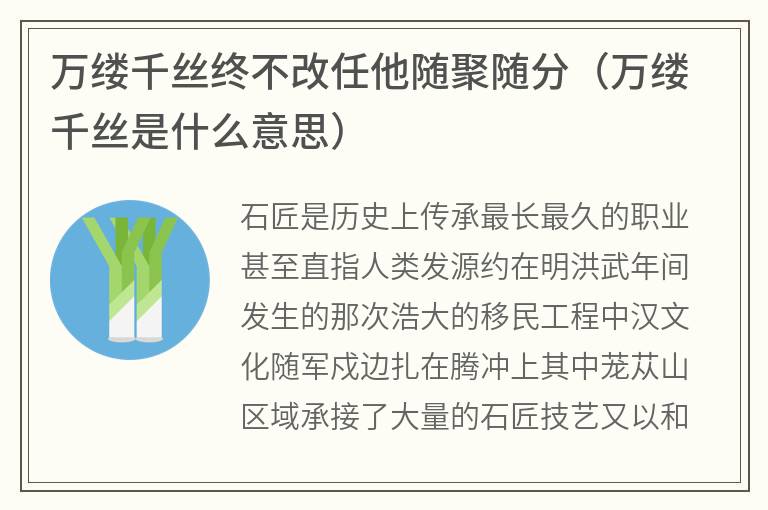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万缕千丝是什么意思)
甚至直指人类发源
约在明洪武年间发生的那次
浩大的移民工程中
汉文化随军戍边扎在腾冲上
其中茏苁山区域承接了大量的石匠技艺
又以和睦最为典型
每年初秋的清晨,稻子刚收完,几乎每家的老母亲都会祭奠祖先,祈求即将外出的游子平平安安。因为接下来的6个月,是和睦人口中的“干天”,石匠们会结队外出打工,往往是父携子,兄携弟。在无数个劳累过后的无眠夜晚,大概会有人思念贤惠的妻子,尚穿着开裆裤的孩子,母亲所做的荷包蛋。石匠们有时会遇到结不到工钱或是丢失工钱的情况,且不说几月的辛苦白费,家中老小还会面临窘境。然而,家总会包容,勉励。
这似曾相识的一幕竟延续几百年之久,因为和睦人血液里流淌着改善生活的斗志,不被生活所打败。
一个个普通而淳朴的和睦石匠,在整个腾冲甚至保山都小有名气,因为他们实在技艺高超。修的拱桥,粗犷美观,百年不倒;绵延的弹石路,经牛走马踏,未曾变样;砌墙,采本地独有的火山石,巍巍然给人以安全感;刻碑,入石三分,书法传神…一根准绳,量得下山河分野,锤子凿钎,挥舞间便是巧夺天工。然而,和睦人总是和气的,工钱要的不高,若是雇主家境不好,取个伙食路费罢了。
当地人赶集路上的一座石拱桥名“小花桥”,历史久远且不说,上面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传说,在晚清时候,发生过一次百年未有的大雨,连降半月有余,山洪肆虐,屋舍农田具毁。有见识的人说,是有蛟化小花龙,但缺少化龙的龙门,没有灵智,才会有大水。于是便募集众石匠,修下这座拱桥,上刻龙凤,此后,再也没有听说有发大水的情况了。
但当地人坚信,有龙过的地方是宝地,于是每当男女结婚,会携手过桥,希望生出的孩子成龙成凤。
石匠们闲居家中时,凿个水缸,换块台阶,亦是不舍得歇下来。领居家不可少的老灶、石磨、猪槽,保你打磨精致。你说价钱,您看着给,拿不出,也没事,几升米也是可以的。
石匠们不拘于古,大胆创新,随时代而进步。有啥新的材料工具引进来,老的新的水乳交融,不见生硬痕迹。也许,工艺品和老一辈做的不一样,但是,那颗工匠之心却是一如往日,炙热,“板扎”。和睦的石匠不吝啬,教会许多慕名而来的求学者,将技艺传承得更广,更久。
一绳一锤,量的是情怀,凿的是匠心。自这门手艺诞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未断。他们用一根绳丈量着历史的温度,用一柄锤凿刻着民族的脊梁。从雕栏玉砌到阡陌纵横,从布艺桑麻到王侯将相,无一不感受着属于石匠的馈赠。
而行至如今,风吹雨晒过后,留下的,是独属于和睦石匠的浪漫。在那经得起考验的无数个瞬间,他们早已幻化作和睦精神的象征。
那是一群怎样至善的人?
他们或刚成家立业,或已到天命之年。他们没有华衣丽裳,被晒得黝黑的皮肤,常年劳作已习惯的老茧,只有那双眼睛永远那么干净,澄澈而坚定,而那一身刻进骨子里的技艺,生生不息。
他们拿着最简单的工具,走在和睦的千家万户里,走在风雨里,走在烈日里,走在每一个春秋冬夏里,走在每一朵山茶花的岁月里。累了,便拿出随身携带的草烟,一抓一裹,虽呛头却也是苦累里的慰藉。汗滴在土里,那是前人走过的足迹。
名和利,于和睦石匠而言,虽谈不上身外之物,却也不足挂在心上。老一辈的和睦石匠,更多的是一份责任和坚守,有时一筐蛋一袋米,便无需工钱。或是困于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更多的,是一份匠人的初心不改。
直至发展到今天,这依旧成了很多和睦人吃饭的家伙什,成了他们心中最割舍不断的那一缕情怀。
传统与创新似乎是一个永远避不开的矛盾话题,一方面技术与时代的进步,带来更精确的机器取代人工,另一方面,传统手艺已深深镌刻在每一个和睦人的心中,必须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而这二者该怎样融合与发展,便成了每一个和睦石匠无法避开的时代答卷。
之前去和睦看山茶花,恰逢一位石匠坐在路边,悠然地抽着水烟筒,走上前打听两句,忽然看到那精美的石刻,又抬头望见他粗糙的脸庞,阳光下他花白的胡子微微颤着,不觉间,竟红了眼眶。
“人呐,能把一件热爱的事做到老,这辈子,值了。”他转过身,朝着我说道。
对啊,不就是,热爱吗?
他又开始了忙活,清脆的声音回荡在大片的山茶花里。红艳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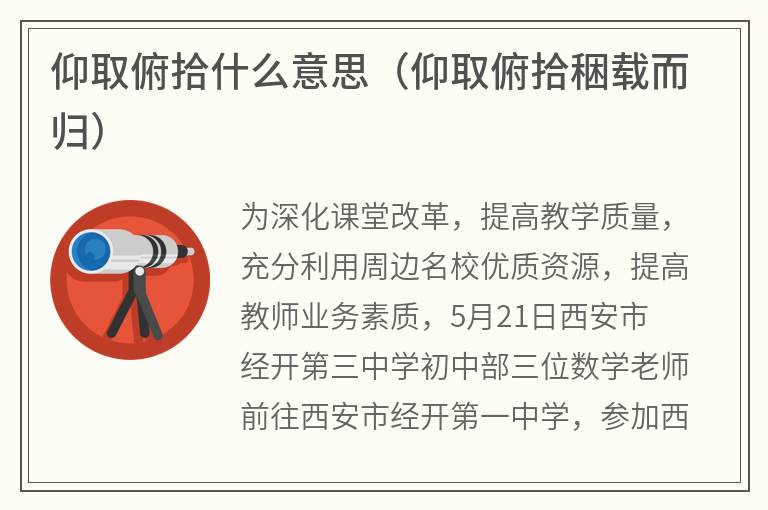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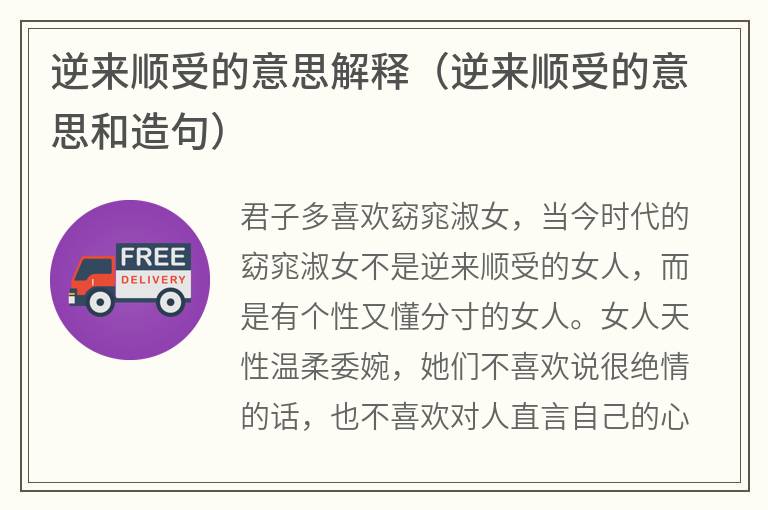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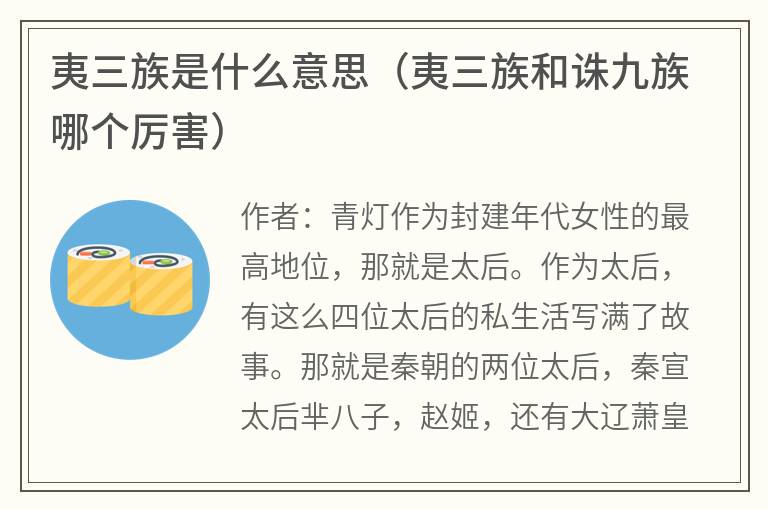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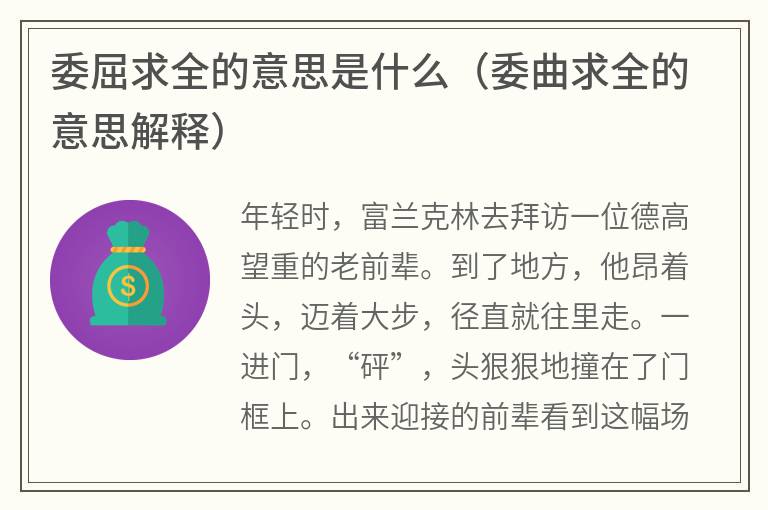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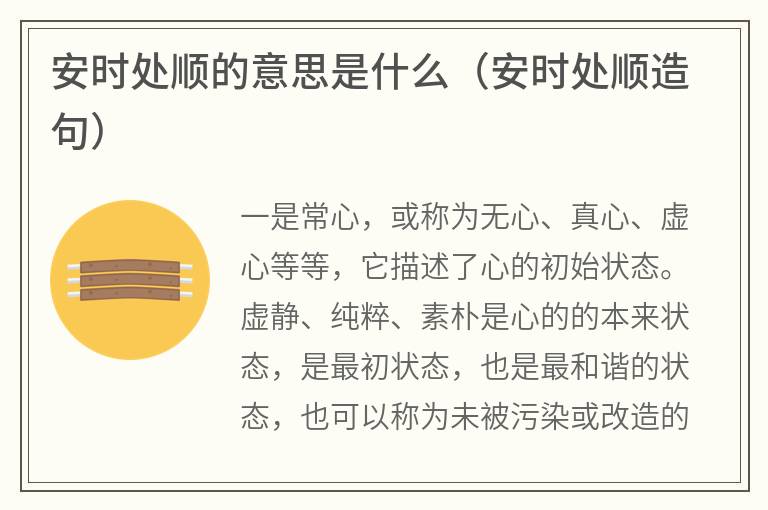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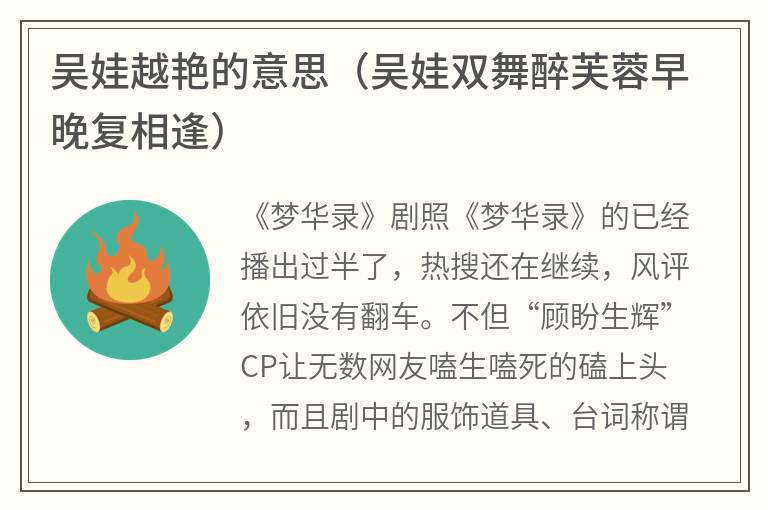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