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16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梅开二度”,进入17世纪,蒙古文坛诞生了以《蒙古源流》等为代表的大批历史著作。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专家学者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历史典籍的?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关于消极影响,学界普遍认为有两大方面。
1)虚构的历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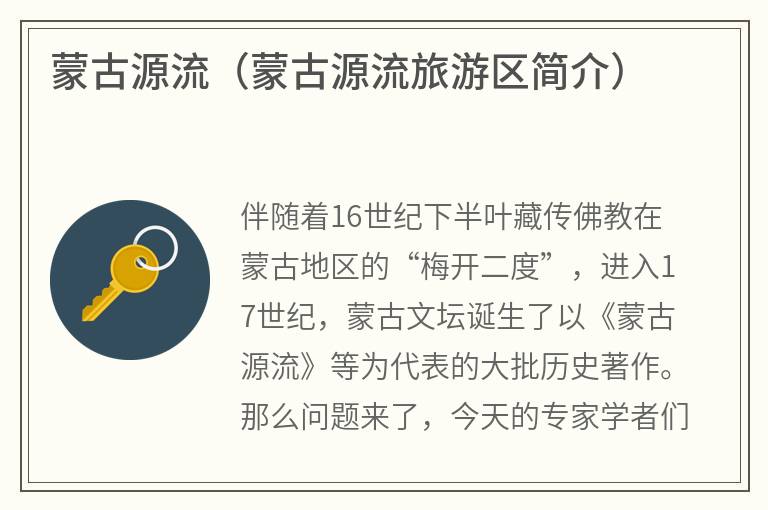
蒙古源流(蒙古源流旅游区简介)
说到“虚构”,最具代表的无疑是所谓“印度一西藏一蒙古”同源说。至于搭建这一“虚拟理论”框架的缘由,无疑是为了论证“黄金家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就拿《蒙古源流(全书共8卷)》来说,该书用相当长的篇幅(2卷),介绍了印度和西藏王统的历史。在第三卷中,作者将蒙古先祖孛儿帖赤那安置了进来,最终达成了“印度一西藏一蒙古”体系的构建。
《蒙古源流》所记载的“印度一西藏一蒙古”同源说,其脉络大致是:
藏王尼雅特赞博合罕的七世孙色尔持赞博合罕即位后,臣下隆纳木谋叛并夺取了汗位,色尔持赞博合罕的三个儿子不得不各自出逃。“季子布尔特奇诺(即孛儿帖赤那)往恭博地方矣。因彼恭博国人不信,娶名郭娃玛喇勒之女为妻,渡腾吉斯海(可能是贝加尔湖),趋之东方,至拜噶勒江界之布尔罕·哈勒都纳山(靠近克鲁伦河的源头),而逢必塔国(疑似‘北狄’)之众焉”….
实际上,成书于这一阶段的蒙古史料,写作框架大多大同小异。以佛教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开篇,接下来依次讲述印度、西藏和蒙古诸汗极其佛教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四段式”写法,成为了蒙古史学界约定俗成的创作模式。不过,这种“刻意为之”的“套路”,无疑让其真实性打了一定的折扣。
《蒙古源流》汉语版封面
因为藏传佛教思想的深度影响,在这些蒙古文历史典籍中,时不时就能看到“佛教影响政局”的描述。
譬如在《蒙古源流》中,忽必烈一开始并不信任藏传佛教,他在与高僧玛迪·都瓦咱(从信史看,应该是“帝师”八思巴)的辩论失利后才皈依了藏传佛教,最终“以行十善福事之政,平定四海,致天下以康乐之境矣”。也就是说,忽必烈之所以能“平定四海”,使天下成为“安乐之境”,就是信仰藏传佛教的结果。
拓展阅读:一文纵览:西藏是如何加入中华大家庭的?
八思巴与忽必烈
关于元朝的覆灭,《蒙古源流》的描述更为“猎奇”。原本是布衣出身的朱元璋,在书中摇身一变,成了元顺帝麾下的大臣“朱葛诺延”。“朱葛诺延”把持朝政、祸乱朝纲、为所欲为,他排挤贤臣,并煽动汉人造反,最终颠覆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一言概之,“朱葛诺延”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面“奸臣”。
明军大军压境,元顺帝不得不退居漠北。临别之际,他借助“哀歌”,复盘了败亡的原因,即“偏信叛亡之朱葛诺延乃我之愚也,误杀我聪睿之托克托噶太师(即脱脱),驱逐我尊上神喇嘛者乃我之孽也”。值得注意的是,在元顺帝的复盘中,除了“远贤臣、亲小人”外,还有“驱逐我尊上神喇嘛者”一条,即没有按照藏传佛教的理论治理国家。
在今天看来,这一理由实在是让人摸不到头脑。但现实情况是,当时主流的蒙古族史学家,几乎都认同这一观点。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明太祖朱元璋和元顺帝
2)损害了历史客观性
坦诚说,蒙古族史学家撰写史料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充分传递藏传佛教思想以及谋求政治上的利益。因此,他们并不十分在意史实的真伪,也并未把史实的考证放在首要位置。毫不客气地说,蒙古历史成为了他们“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于是,蒙古历史长河中的一些重要史实,要么被刻意忽略,要么被肆意篡改,严重损害了史籍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如《黄金史》中“拖雷为成吉思汗而死”的记载,与信史《蒙古秘史》完全不符。
拓展阅读:「蒙古大乱斗」拖雷“意外”之死:蒙古帝国分裂的伏笔
拖雷与妻子唆儿忽黑塔尼别吉
因为藏传佛教思想的“深入人心”,在这些蒙古文史料中,凡是与藏传佛教理论有关的史实,史学家们可以添油加醋、大书特书;至于与之不相关或关系稍远的史实,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干脆完全无视。
亦邻真在梳理《黄金史》对撒儿讨温远征(西征花剌子模)以及南征中原仅仅用一句话就简单带过后,便深入分析道:“在黄教史家看来,变蛇化鹏才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奇迹。在他们眼中,超现实的历史才值得一写。他们希望历史充斥幻想的现实性,因而他们也就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
为了论证藏传佛教的合理性,不少史学家们甚至刻意扭曲和捏造了一些所谓的“史实”,用来迎合自己的佛教观,从而为其现实政治目的服务。譬如关于“成吉思汗为西夏王妃所害”的记录,就是典型的例子。
拓展阅读:“成吉思汗被西夏皇妃所害”的“魔幻”记录,究竟出自何方?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历史局限性,以至于直到今天,围绕着蒙古历史(尤其是北元时期的历史),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
实事求是讲,藏传佛教与蒙古族史学的结合,是蒙古统治阶层谋求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1368年,元室退居漠北。原本大一统的元朝,“退步”成了割据北方的游牧属性政权——“北元”。纵观北元史,兄弟反目、父子成仇、不同部落之间相互讨伐攻杀的戏码,令人叹为观止。直到达延汗即位后,整个蒙古地区的生产与生活才日趋稳定。
拓展阅读:被压制百年的“黄金家族”:北元大汗们的凄凉血泪史
达延汗
进入16世纪中叶,谋求地域稳定发展的蒙古统治阶级,在寻求扩张的藏传佛教上层达成了“心有灵犀”的默契。前者通过大肆修建寺庙、礼遇高僧并给予优厚待遇等举措,“借用”藏传佛教的教义,加强社会思想的统一,巩固自己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达延中兴”的16世纪上半叶,蒙古社会各界才达成了“黄金家族”正统观的共识,即“只有拖雷系忽必烈支后裔,才有资格充任蒙古大汗”。
伴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各地的深度传播,蒙古族史学家们迅速“审时度势”,不仅在史籍中积极引入了藏传佛教的思想“改造蒙古史”,并成功构建了“印度一西藏一蒙古”这一虚构的文明传承体系。这样的“神操作”,不仅让“黄金家族”正统观更为深入人心,并进一步巩固了统治阶层的统治。
到了俺答汗时期,藏传佛教的传播达到了新高度
实际上,清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也意识到了藏传佛教在统一和团结蒙古诸部的作用。因此,清廷不仅对宗教上层进行政策性收买,并在蒙古地区大力修建寺庙,给予了喇嘛们免税、免徭役、免兵役等特权。
因此,即便在清朝时期,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有增无减。这样的现状,也给了乾隆敢于说出“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底气。
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藏传佛教之于蒙古史学,还是有一定可圈可点之处的。
1)客观上充实了蒙古族史学的内容
藏传佛教与蒙古族史学结合,使得藏族历史和古印度的历史,均成为蒙古史学必须记载的基本内容之一。蒙古族史学家在学习这些民族史的过程中,视野逐渐得以拓宽。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蒙古族为中心、兼及其他民族历史记载”的民族史学体系得以搭建完成。
得益于藏传佛教“东方黄,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青”的“五方色”理论,在成书于16世纪的《白史》中,就衍生出了“东方白色朝鲜、南方黄色回回、西方红色汉人(北方人)和南(方)人、北方黑色吐蕃(藏族)、中央四十万青色蒙古和卫拉特”的“五色四藩”观点。有学者认为,民国“五色旗”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就借鉴了这一学说。
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从上至下依次代表汉满蒙回(穆斯林)藏“五族”
2)打破了蒙古社会沉寂的文化氛围
元朝灭亡后,“回到草原和山区的蒙古人,比成吉思汗以前时代更陷于孤立状态,蒙古人迅速地丧失了帝国时代的各种文化成就”。直到“达延中兴”之后,蒙古文坛才有了些许复苏的迹象。
“捅破”这一层窗户纸的,无疑是佛教僧侣以及深受藏传佛教影响和熏陶的蒙古族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诸如《蒙古源流》、《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阿拉坦汗传》、《水晶珠》、《金轮千幅》等大批蒙古文史籍横空出世,并得到妥善保存。其中,《黄金史纲》、《黄金史册》、《金轮千幅》等史书的作者,本身就是藏传佛教的僧侣。
让康熙颇为头疼的噶尔丹,是如假包换的活佛
3)系统化史学体系的构架
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理论的系统性。对于深受藏传佛教熏陶的蒙古族史学家而言,其历史观也变得更为系统。
以宇宙和世界的构成为例。在藏传佛教传入之前,蒙古族史家们长期停留在“上天创造宇宙和世界”的认知上面。
拓展阅读:锦囊:如何写一封诚意满满的“硬核”情书?
元顺帝《大元宣谕圣旨之碑》,第一句就是“长生天气里,大福荫护助里”
藏传佛教传入后,蒙古族史学家们的传统认知被逐渐打破。譬如《蒙古源流》在开头就提出,宇宙是由风、水、土所构成的。“自定一切所依之外相世界,生成凡依存之内部生灵,此二者中,首言其定外相世界之事,则用三坛而定焉。其所谓三坛者,乃肇造之风坛,涌波之水坛,所依存之土坛是也。”可以说,他们已经初步具备了比较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
总而言之,藏传佛教对蒙古史学的影响,囊括了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对于历史事件造成的“一体两面”,我们既不要全面肯定,也不要全面否定,而是尽可能地尝试用更冷静、客观的视角,深度认知其背后的逻辑和内涵,进而实现更为深度的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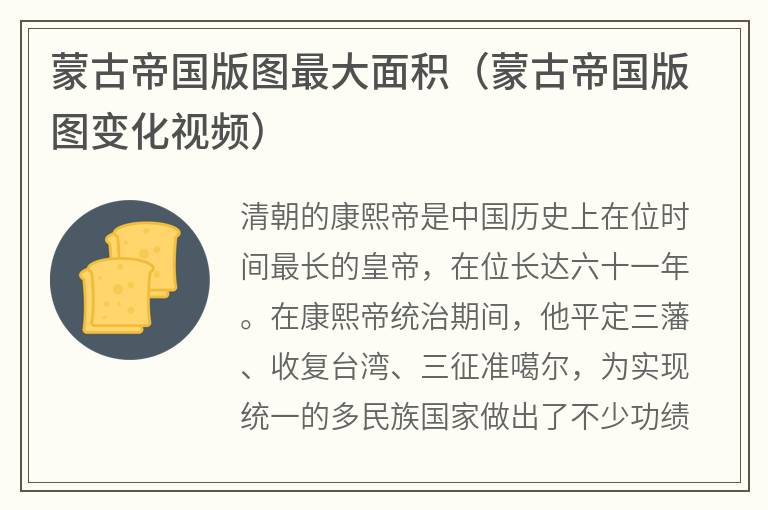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