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歇家研究》
【编者按】浙江师范大学胡铁球教授所著的《明清歇家研究》,引起明清史及社会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探讨,颇获好评。不过,高寿仙、范金民等学者,对该著一些史料的解读提出了质疑,认为有误解与过度解读史料的嫌疑,为此,在《光明日报》连续刊发了三篇商榷文章,即高寿仙《准确把握历史的细节和碎片——也以明清歇家为例》、范金民《谁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兼评〈明清歇家研究〉》、高寿仙《怎样在史料体系中理解历史的细节和碎片——仍以明清歇家为例》。胡铁球则认为自己并未过度解读,我们期待通过学者们相互论难,推进史学研究的发展。
歇家的记载极其繁多,但多为片言只语,而歇家本身的概念、功能、涉及的领域等又极其复杂和广泛,故解读起来非常艰难,若不仔细斟酌,极易误读,甚至歧义纷争。若想较为准确地把握历史的细节和特点,精深的微观研究必不可少,我相信,随着历史研究的推进,类似歇家这种研究,将会越来越多,因此如何解读好歇家,应具有较典型的意义。我私下认为,高寿仙先生之所以不厌其烦与我商榷某些歇家段落的解读,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细节解读关乎整个体系的立论,更多是基于上述原因的考虑。
如何在史料体系中解读歇家?我与高寿仙先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不得不迫使我们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正确地解读史料,以便使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高寿仙先生在《怎样在史料体系中理解历史的细节和碎片——乃以明清歇家为例》一文(《光明日报》,2017年11月6日十四版)中指出我解读史料的五处硬伤,现商榷如下。

青海来丹噶尔城的内蒙商客
一是关于“解人犯”的主语是谁?高先生认为“解人犯”主语是“外府州县”,而我认为其主语是“歇家”,谁对谁错?首先录原文如下:“禁止保歇。省会府县歇家最为作奸犯法之薮,故定例,歇家与衙蠹同罪,法至严也。其在省会府城者,外府州县解钱粮,则包揽投纳使费,更有洗批那(挪)移之弊。解人犯,则包揽打点行贿,更有主唆扛帮之弊。”假设按高先生理解,主语是“外府州县”,不是歇家,那么“包揽打点行贿,更有主唆扛帮之弊”也是“外府州县”所为,这便无法理解了。若“解人犯”主语是“歇家”,那么“包揽打点行贿,更有主唆扛帮之弊”为歇家所为,而这些舞弊行为正是歇家的一贯伎俩,如“江西歇家之害甲于诸省……如指称打点,扛帮词讼”;“主唆扛帮之人,歇家、原差居十八九”,诸如此类史料可列出百条以上。要解读好上述史料,首先要清楚“禁止保歇”是整段史料的纲目,在此纲目下,若歇家即具有押解犯人的职责,又有“包揽打点行贿,更有主唆扛帮”等弊端,那么便可断定“解人犯”的主语是歇家无疑。“打点行贿”“主唆扛帮”是歇家惯用伎俩,无需多言,至于歇家具有解犯人的职责,这我在《明清歇家研究》已经证明了,高先生也承认了歇保职责之一是押解犯人。
实际上,歇家不仅有解人犯职责,甚至有捉拿犯人的职责。如嘉靖年间,江西巡抚张时彻言:“但凡里甲应投或词讼到官,即拘歇家保领,遇有公事及问理干对,责令拘提”(张时彻:《芝园集》别集公移卷五《禁约崇仁县奸弊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八十二册,566-567页);又如崇祯十二年,张国维言:“趁(犯人)此际遁逃不远……着囚属歇家追缉”(张国维:《抚吴疏草·吴狱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三十九册,632页);再如晚清青海地区,“为此仰歇役前赴加咱等四族会同隆务寺昂锁、加咱等族千户红布人等上紧开导弹压该族番子,务须安静住坐,不许过河行抢为非滋事”,“倘有不遵者,着该歇役等即将该管千户等押令来辕听候本分府严加究办”(《循化厅为不准隆务四族渡河抢劫的谕》 ,青海省档案馆 , 档案号:7-永久-2663);而晚清台湾地区的歇家“金广福”,拥有私人武装,其捉拿、押解犯人是常事,如“擒获林李,并搜出利刀,登即锁交金广福押候……金广福将犯押解到县”(《淡新档案》,档案号:32102-001、32504-003,台湾历史数字图书馆)。
二是关于“歇家”指称的是“住所”还是“房主人”?原文如下:“传谕口令、抄誊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许增减及别添祸福之说。每传毕,差巡视旗于街上,或歇家,唤二三个军来问之,照不知条内,查治所由。”高先生认为这里的歇家是指“住所”,而我认为是“房主人”。我认为,按古代的书写方式,若“歇家”解读为“住所”,则断不会出现一个“或”字,故这里的歇家应理解为“房主人”。但高先生认为上述史料来源于戚继光的《练兵实纪》一书,而《练兵实纪》一书六次提到歇家皆是指住所,这我不敢苟同,如上引史料中的歇家就是指“房主人”,而戚继光在其它史料中明确指出歇家指称“房主人”,如《戚少保奏议·补遗》载,“各兵远来……不幸有病,地方主家当为调理……应着原歇之家,领回调理……调理不善,至伤本兵者,歇家抵罪”,又郑若曾谈“兵歇家”时,也说歇家为“房主人”,而这些史料我在《明清歇家研究》中解读“兵歇家”的职能皆已经引用,目的就是告诉读者,这里的“歇家”指“房主人”。根据解读史料一般通例,歇家概念包含了“住所”与“房主人”两个,在任何一个史料中,不能轻易排除一种“概念”的可能,这与《练兵实纪》一书所载歇家多指“住所”没有多大的关联。
三是关于“国子监歇家”是否属于“职役”的讨论。高寿仙先生关于“国子监歇家”考证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引用该史料的最初版本《明太学志》,而我当时没有看到,但歇家属于“职役”这个结论,依然成立,因为其已列入役目,并有额定的名额。
四是关于黄善述等八人是不是歇家。隆庆五年,高拱在其《参处崇明县民黄善述等保官疏》言:“看得崇明县民黄善述、施泰然、张堂、龚九衢、袁时化、郁倬、钮尧、沈大鲸奏保县丞孙世良一节。为照近年以来,黠狡成风,不惟有黠狡之民,而亦有黠狡之官,往往或因论劾,或因考语不佳,或被左谪,或被劣处,辄买求该州县无籍棍徒数人奏保,多写鬼名,称颂功德,以为公论……今崇明县县丞孙世良考语甚下,且见被告讦,本部因推王官以示劣处,而黄善述等乃踵袭敝风,连名奏保,抄出本部唤审,乃寂无一人,乃于通政司查出各歇家姓名,行兵马司拘审,又寂无一人,而歇家者,固鬼名也。即此,则不惟黄善述等诡伪可见,而孙世良之买求亦自可知。”事情的原委是:因崇明县县丞孙世良“考语不佳”,孙世良“辄买求该州县无籍棍徒数人奏保,多写鬼名,称颂功德,以为公论”,这里的“数人”暗指黄善述等八人,在明清史料中,歇家经常被称为“无籍棍徒”,而后面又谈到“歇家者,固鬼名也”,故上述八人皆是崇明县的歇家。按明代制度规定,通政司管民间奏报,故上述八人的连名奏保先是递到通政司,通政司再转交吏部,吏部核查时,找不到这八人,于是叫通政司复核落实,这便有“乃于通政司查出各歇家姓名”之语,这里“各歇家姓名”,指的就是上述八人。若是按高先生的理解,这里歇家皆是在京城的普通客店,这连名的八人怎么可能分住在“各歇家”?又京城歇家属兵马司(巡城御史)管辖,怎么又会叫通政司“查出各歇家姓名”?因此这里的“各歇家”就是指上述八人,断不会是指京城歇家。按我的理解,“黄善述等诡伪”与“歇家者,固鬼名也”完全可首尾呼应,若按高先生将“各歇家姓名”解读为“京城歇家”,那么京城歇家的“诡伪”就没有作任何处置,完全可以逍遥法外,这便不符合逻辑了。通看《参处崇明县民黄善述等保官疏》最终处理结果,只处理了黄善述等八人以及县丞孙世良,没有一个字涉及到“京城歇家”,显然这段话中的歇家指的是黄善述等八人。
五是关于“歇家”是指“京城普通客店”还是“指在地方上包揽钱谷刑名等方面的歇家”。原文如下:“布、按二司,府州县佐贰官并各正官,以事不在任者,行令巡按御史严核贤否得实,劾奏转行提问,拟罪发落奏报。仍敕吏部,将应该考察官员预先案仰该城,取具歇家结状。务听说事面纠,以昭赏罚,以示劝惩,方听其去。如此,庶几大典不为具文,足以鼔舞人心,丕变士习,慰塞民望,弼成至理矣。”高先生认为这里“歇家”是指在京城提供住宿的“一般的客店老板”,而我认为是指在地方上包揽钱谷刑名等方面的歇家。解读这段史料的关键是“该城”两字如何理解。
我认为“该城”是指各官原任所在的县城或府城或省城,而非京城,否则无法理解“将应该考察官员预先案仰该城,取具歇家结状”这句话,若歇家仅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在没有考核完就提前离京,则“预先案仰该城”是何意?何况在我所搜集数百万字歇家史料中,未见过在京城考核官员时要“取具歇家”的史料,但在地方调查时,经常要“取具歇家”或熟知情况的相关人员,以便保证身份、事委、考评内容等方面的真实性。如上述黄善述等八歇家,显然利用了自己在地方官员考核中有证明权的身份,希望通过向通政司投递奏保的方式,来推翻崇明县县丞孙世良“考语不佳”的结果;又如明政府曾规定,“饬令干差取具保家,以便传唤质讯”;再如“应立保歇之法,细查殷实之家,赴部报名,取具该管地方保结”等等。根据上述史料,我认为,这段史料中的歇家是指在地方上包揽钱谷刑名等方面的歇家,他们对官员的底细很清楚,故在官员们正式考核前,需通过“该城(各官原任所在的县城或府城或省城)”的歇家来调查取证他们的为官品行,即“取具歇家结状”,以便在考核时能做到赏罚分明。

位于山东聊城的清代山陕会馆
总之,解读史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以笔者研究歇家经验,要解读好歇家,首先要对歇家的概念、异名、经营方式、职能、作用等有一个系统了解,其次则要对商业、税关、赋役、司法、仓场、考成等制度有较深入的研究,其三要对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以及民俗民情有一个系统了解。我所说的史料系统,其内含包括了上述这些复杂信息系统。只有掌握了上述整体的史料系统,才能将记载歇家的每个细节所能展现的歇家功能以及其内含的社会特性等揭示出来。不妨再举几个我与范金民先生解读史料的差异以说明之。
其一,有关“禁革歇家”问题的解读。“禁革”这个词的含义非常复杂,在明代,所谓“禁革歇家”,多是指禁革歇家游离政府,而在政府控制内的歇家,政府不仅不革,还赋予其许多职能,故将其称为“保歇”“官保”“保户”“保家”“保识”“相识”等等,且将歇家不断地纳入税关、仓场、赋役、司法等制度体系中,广泛建立起了“保歇制度”。到了清代,由于清政府力图构建政府与纳户一一对应直接征收的理想模式,开始禁止一切中间包揽,这种禁革,属于“取消”范畴,但在实际运作中又取消不了,这便迫使歇家不断更换称呼以符合新制度的要求,如“禁歇家,则变其名曰传催、曰里书”等等,这时候的歇家才处于隐形状态,即以另一种身份出现。除此之外,政府对某事下达的“禁革”越多,恰恰说明了该事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如清初因士绅通过歇家经营包揽刑名钱谷的事,越来越普遍,因此清政府“禁生员”等告示越来越多,如“生员、衙役、宦仆不许揽充斗户”;“严禁生员出入公门”;“禁生员充当里长”;“严禁生员、监(监生)抗粮唆讼”;“禁生员摄约正务”等等。从明清文献记载来看,政府禁革士绅、胥吏衙役包揽钱粮词讼厉害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歇家,因此不能说歇家不断被禁革,就说其势力不大,这刚好恰恰相反,这也是我与范金民先生关于这一点解读的差异所在。
其二,关于“新旧经营方式”在时空存在的关系问题。新的经营方式取代旧的经营方式,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新旧经营方式同时并存,毫不奇怪,故“歇家牙行”与“会馆公所”同时并存是合理的,如青海地区的公所直到晚清民国时才兴起,而且是从歇家中发展出来,史称“歇家公所”,如“口外各番族来丹采办粮茶,向择土人之能操番语者,开设店户充当歇家……嗣经设立公所歇家,专司其事”。又如湖北都昌县,在晚清民国时,多在县城建“祠堂”作歇家,这些歇家也被看作是“会馆”,如“一个仅三千人口的县城,开设保歇的高峰时就有六十来户,五十四栋祠堂,既是各族姓氏打官司的会馆,也是保歇之家”等等。查之全国,自万历中期开始,地方政府或乡民曾尝试设立“便民公舍”“里舍”“公馆”“完米公所”之类的设施来取代歇家的职责,如“完米公所……系合邑粮户捐置建屋,以便完米人丁寄宿之处”等等,这些皆说明会馆公所与歇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便是我为何不赞同范先生所认为的“歇家牙行”与“会馆公所”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理由。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案例研究盛行,这对深入理解社会特性具有重大意义,但把典型案例的研究视作整个社会的运行样板,就有极大的风险。就诉讼等类型的案例而言,留下的,基本上是违法的案卷,而合法的则不会留下案卷,也就是说这种案例本身就排除了合法行为,而合法行为,在正常情况下占绝大多数,是社会性质的真实反映,但不会留下记载,故案例研究必须在制度框架内来理解,脱离制度框架的案例解读,其实就是一个意义不大的特例。打一个并不十分妥帖的比方,如目前我们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一般而言,没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夫妻多数不会留下案卷,而重婚、婚外情等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往往因离婚、争家产而留下大量的案卷,但就是你找到了一百万个“小三”案例,也改变不了这个时代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社会属性。
再如乡绅、宗族等问题的研究,确有许多典型案例可以说明当时社会具有乡绅、宗族社会的属性,不过,非乡绅、宗族社会结构也是广泛存在的,这些非典型区域也要额外关注和研究,且只有将二者进行对比研究,甚至要采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将典型区域与非典型区域的实际范围进行比对研究,方能清楚整个社会结构状态和属性。因此,我认为明清所有社会问题皆要放在制度框架内来讨论,游离制度框架,会与历史真实发生背离,尤其要清晰认识到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一直是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结构。总之,解读史料,即需熟知典章制度,又需尽可能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否则很容易犯一叶障目的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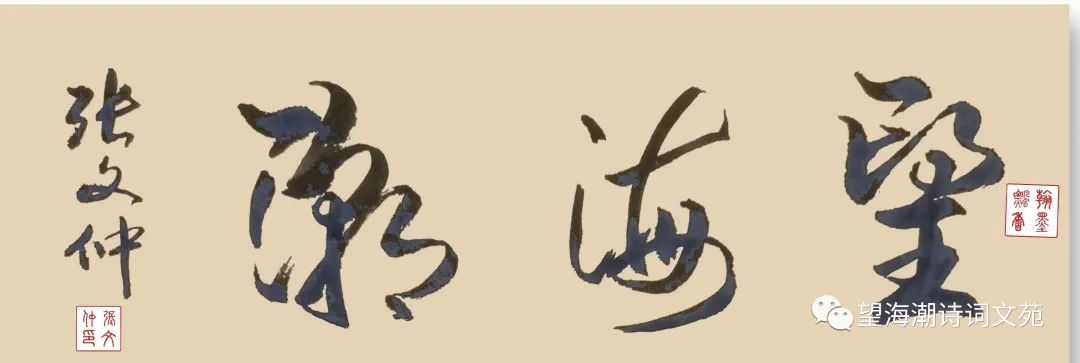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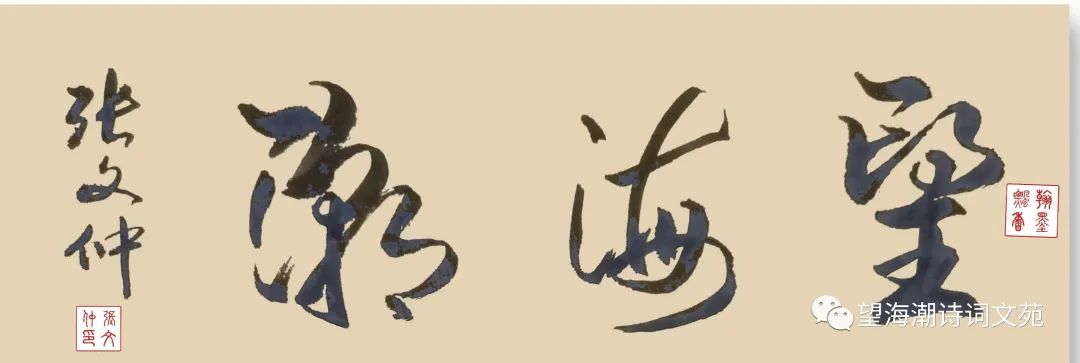
发表评论